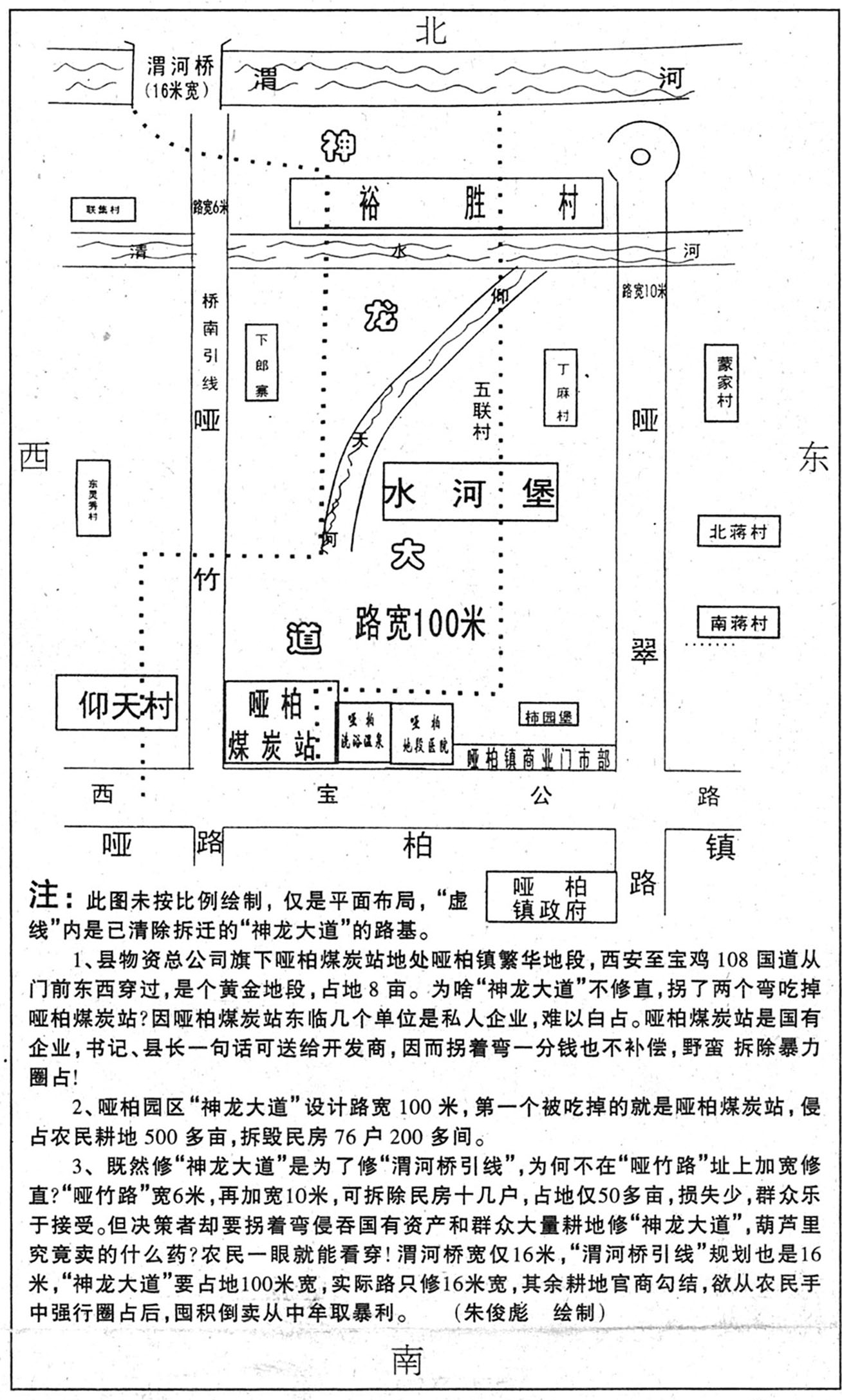□杨乾坤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尽人皆知。风俗不同,大抵受制于多种因素,也正因为如此,方形成了丰富多采的地域特色,欣然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怪么?不怪。然而有人怪之,不能不说是少见多怪了。少见多怪,致使陕西有了“八大怪”之说。有人还把它凑成十大怪,更有生拉硬拽编派出更多的“怪”,庸陋低俗,直是把无聊当有趣。
这些怪,大抵是对陕西并不了解的好事者所诌。“面条像裤带”,叫人恶心,本地人不会如此下作。“锅盔像锅盖”,那是民俗,既是“锅盔”,不大而何!“房子半边盖”,那是贫穷,盖不起前后两檐流水的上房,只能用这种厦子房凑合。“凳子不坐蹲起来”,那是农民农事劳作,相遇聊天,蹲惯了的缘故。“帕帕头上戴”,是因妇女出门时,春秋避尘夏避日的原因。“辣子一道菜”,那是因秦人好辣椒,又以面食为主,调味用以加餐之故。齐鲁人餐桌上顿顿有蒜,也未听什么人说它“怪”,川人湘人尤嗜辣,那辣椒非惟是一道菜,简直是道道菜的根本,却没有谁去说什么,为什么一到陕西,就“怪”了。还有另外的两怪,这里且多说两句。
秦腔的高亢激越豪放,被一些人外地人所垢病,又听不大懂,故有“唱戏跟吵架分不开”。殊不知作为梆子腔的鼻祖,秦腔自有完美的体系。以激昂的大净(黑头)戏概括秦腔,是以偏概全。看看拍成电影的《三滴血》和《火焰驹》,再发表高见亦不迟。至于秦人,没有绵软的苏白,没有响亮的京腔,自有其犷放大气之特点,涌动的正是先人的血脉,君不见《诗经》中《秦风》的诗句么:“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姑娘不对外”,是指出嫁姑娘不出本村,还是不出本地?若是前者,是将个别作了一般的歧见。若指后者,似乎农耕社会的外省亦是如此,通婚圈大都有几十里范围之内,唐人诗中,有“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之句,“舅姑”指公婆。在古代,因舅家姑家常通婚的原故。有通婚圈子,非秦地所独专,为何将此怪强加在陕西头上?
可见这些怪,本不是怪。何况风移俗易,这些所谓的怪,有的在消失,有的在淡化,有的在改进,继续的只有一两个。硬拼凑“八大怪”,大约也是犯了类似的“八景病”。硬凑的人有的是出于无知,有的是出于揶揄,有的纯属贬意,总之是无聊。始作俑者,是浮薄之徒,他们对陕西人文地理知之甚少,故而显露出轻浮之相。
这种轻浮,就见低俗卑劣的嚣然。“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老陕齐吼秦腔”,就是这卑劣之谬种。此谬种至今还制匾悬于西安某餐馆门首:“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老陕齐吼秦腔;来碗面条喜气洋洋,没有辣子嘟嘟囔囔。”自我辱践,反以为荣,真教人尚何言哉。前几年我去山东曲阜,见一饭馆楹联曰:“德不孤,必有邻,仁里美乡歌善政;行守道,和为贵,远来近悦乐良朋”。相形之下,高者何其高,卑者何其卑,优者何其优,而劣者何其劣也。莫非文章自古传东鲁,至今仍难度秦关?
陕西自号文化大省,因何“八大怪”能谬种流传?又因何有拿“八大怪”做了陕西民俗定格之虞?这就是媚俗。更何况还是媚错了。“八大怪”若说是在关中,尚算有因,若膨胀到陕南、陕北,便属无稽。拿“八大怪”而自傲,而张扬,以为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就惹天下人耻笑了。
何物“八大怪”!能泛而滥之,实在是一种悲哀!不说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