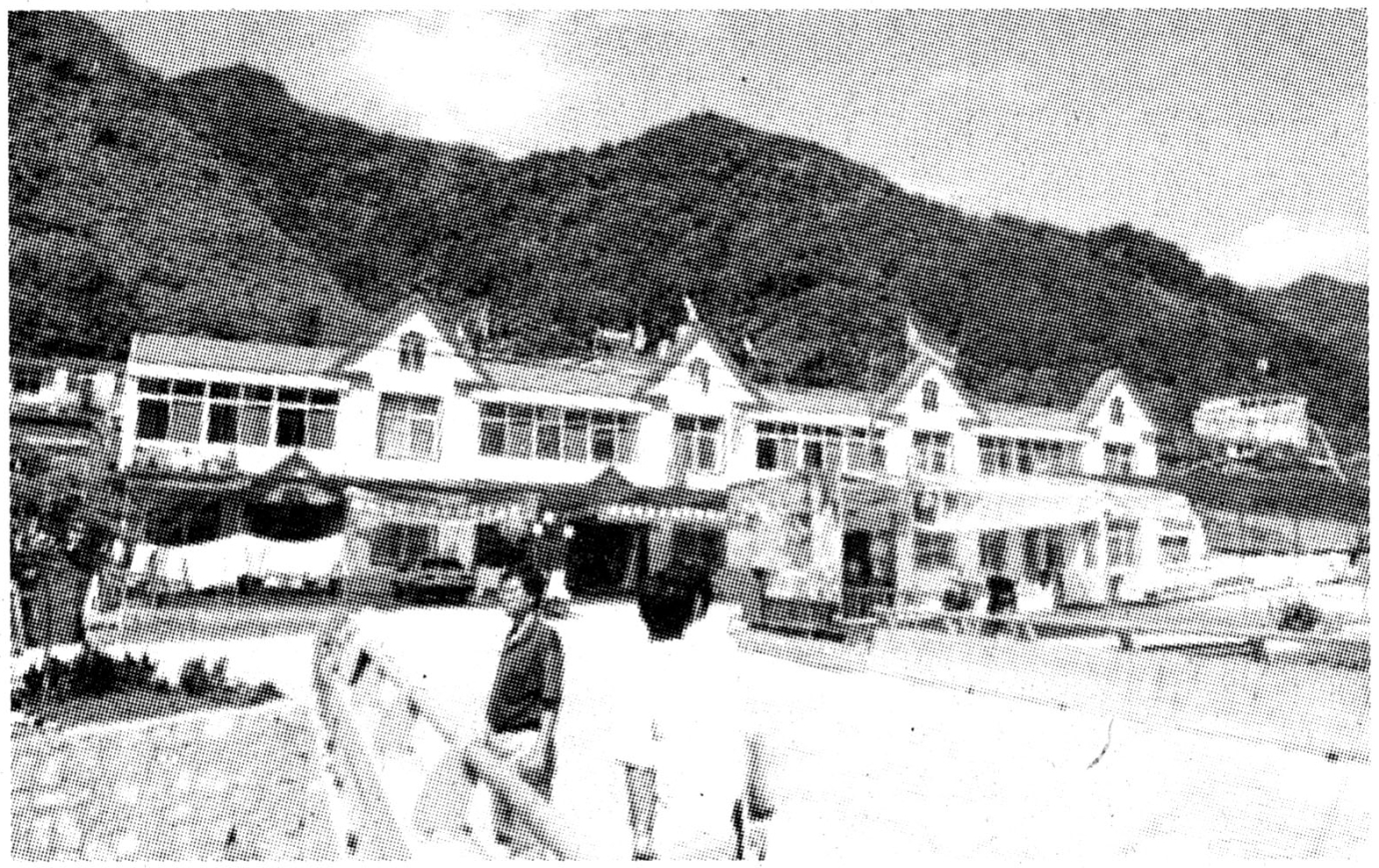□童大焕
前不久,河南省濮阳市对人民路进行改造,把原有的非机动车道改没了。为了让人们“适应”新路况,有关方面派出一批“交警协管”,把三轮车、自行车、电动车往人行道上赶。原来路面上的通畅与和谐不见了,路人因此怨声载道。一位濮阳市民在“濮阳信息港”上留言:“我昨天接儿子下学,协管员厉声呵斥我要遵守交通规则,我很想遵守一下,可为了提醒提醒儿子,我违章了。我告诉儿子,当坐小车的人没有想到骑自行车人的感受时,你也大可不必顾虑坐小车者的感受,包括为他们服务的人的感受。打小我们就被教育做好孩子,可我告诉儿子,你真的不必做好孩子。”
这是一个制度化不信任的典型例子。当制度、法律、规则不公正,或者执行不公正成为常态之时,对制度的不信任就会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不成文的“制度”。此时,人们内心遵循、服从的将不再是公开的法律、制度等规则,而是自我内心的律令以及各种通行的潜规则,比如,强者践踏规则,弱者被迫服从规则;再比如,明里遵守规则,暗里破坏规则……
制度性不信任通常是导致集体无规则的渊源。当制度性不信任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时,人们往往选择忍耐,但当忍无可忍之时,一些人又会将暴力视为解脱的途径。在山西,有一个曾经得到过“社会治安模范户”荣誉称号的村民,连续四年向各级部门检举村干部的腐败行径,不仅毫无结果,而且饱尝冷漠、推诿乃至白眼。于是,这个村民最终对惩治腐败的法律救济机制产生了绝望,竟一连杀了村支书等数家14口。这种残忍的做法固然不足取,但他在法庭上的一番陈诉却令人深思:“如果我的死能够引起官老爷们的注意,能够查办了那些贪官污吏,我将死而无憾!”由此可见,没有合理的官民利益、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博弈机制,社会很可能回到无规则的原始状态。
制度性不信任所导致的集体无规则,不仅在弱者身上广泛发生,也不仅广泛发生于弱者和强者之间;而且也发生于强者和强者之间。比如,最近被媒体广为关注的“山西民警打死北京民警案”就是鲜明的一例。事件发生后,当事双方的单位都急急忙忙地站出来,声称属下的警察是“好警察”,辩解这种相互残杀是一时冲动的“激情犯罪”。这种现象不能不令人感慨万千,因为它只能证明一点,对某些部门和国家公职人员而言,对权力运行的骄纵已经成为一种惯性,正是这种惯性,植下了制度性不信任、集体无规则的种子,并成为点燃社会内耗、社会暴力的炸药包。
目前,对于社会广泛关注的“山西民警打死北京民警案”,除了行凶者本人被捕以外,负有责任的公安机关领导也被停职检查。不过客观而言,让这些领导分担案件责任,实在是勉为其难。因为说到底,体制性问题必须体制性应对,要消除因制度性不信任所产生的集体无规则、社会暴力等病症,我们更应着手于宏观层面的体制改造,比如,强化公民权利对公共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切实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财产自由和言论自由,推进司法改革,促进司法公正,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