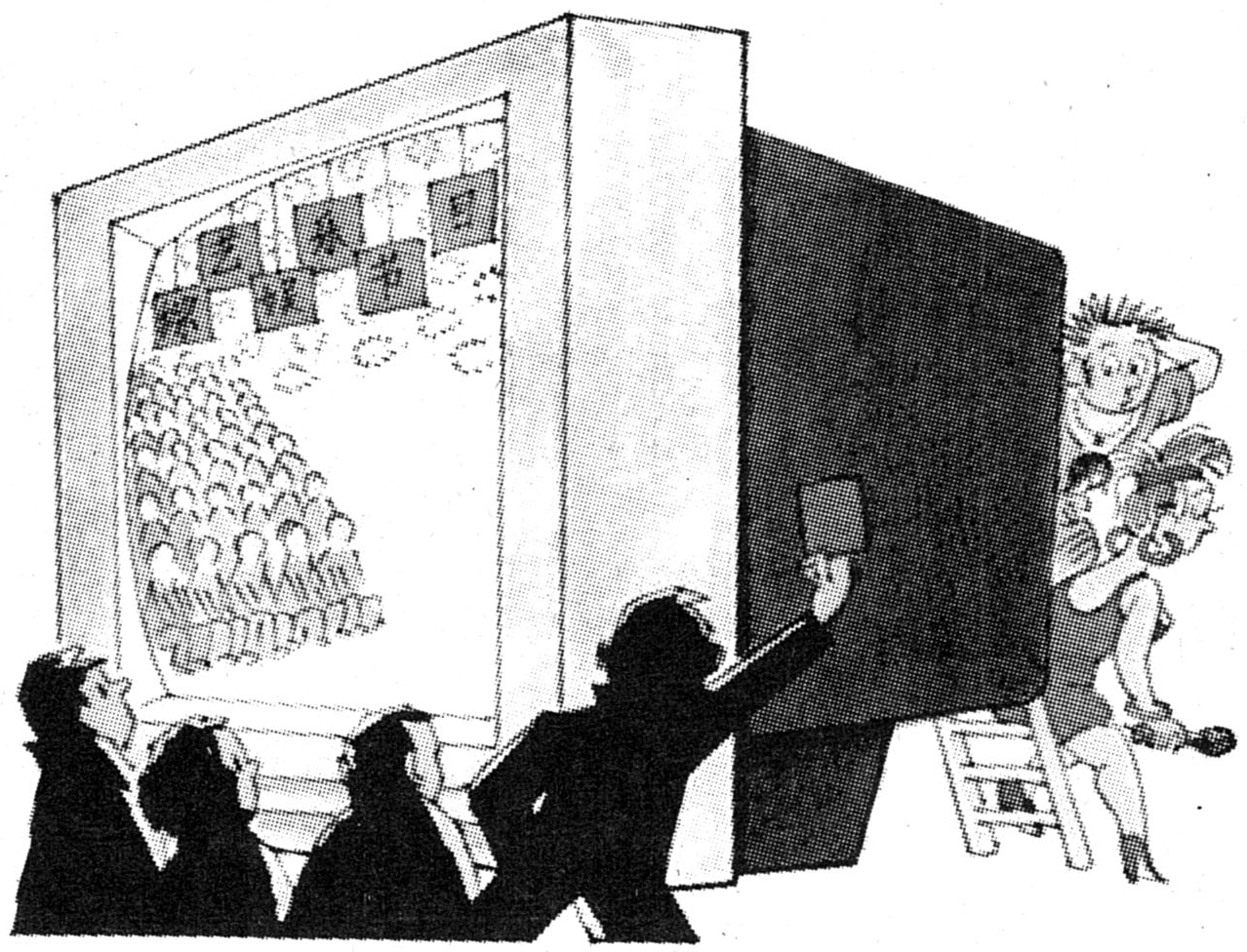·袁波·
一位大学教师为了完成学校规定的每年必须发表三篇以上学术论文的任务,不惜花费重金从社会上买回四五篇赝作,然后再用钞票打通路子,将其发表,这是我刚刚获到的消息。
其实,这等消息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早在几年前,我就从报端上获悉,现在社会上就有专门为人提供论文“服务”的“写作公司”,据说此等“公司”一面世,就显示了强劲的势头,生意做得十分的红火。个中的缘由不外乎迎合了一些人为了评定职称或评上职称后应付单位关于职称获得着每年需要产出的论文量的“新要求”。然而,对于相当一些人来说,由于囊中羞涩,为了评上职称或在有了职称后完成单位关于论文发表的硬指标,他们不得不拿起剪刀和浆糊“自力更生”地充当起了“文抄公”。对于这种在学术上弄虚作假的行为,理所当然地应当受到舆论的抨击和谴责,严重的还应该像那位剽窃他人成果的北大王姓博导受到取消其博导资格的惩处。
这当然不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初衷。我要说的是,学术的腐败,赝作的泛滥,不要单从学术良知上去找原因。而是要冷静下来好好反思一下我们评价科研成果的某些钢性的规定和标准。譬如,在职称评定上,在评了职称之后,规定不同级次所发表论文篇数。乍一看,这些规定和标准似乎是无可挑剔的。实际上这些规定和标准就存在着严重的失范效应:其一,无论是各级审评单位,还是有关的专家组均不可能对论文的真伪进行鉴别,这就使得赝作可以一路畅通无阻地以“正果”的名誉通过鉴定。其二,过于钢性的数字不仅违背了科学研究的法则,同时也种下了“逼良为娼”的因子。在这种情景下,人们为了达到某个职称层次论文数量的要求(人们总是首先考虑数量),必是要千方百计地在一定的时间里凑够那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数”。当受精力、能力或水平的限制还不足以达到凑够这个数而自己又不轻易放弃对职称的追求时,一种“冒险”的意识也就随之产生了。难道仅仅是一个学术良知问题而与有关的规定及标准的失范无涉么?
在下长期在高校工作,就有限的目睹耳闻,我以为眼下的学界,由于忽视甚至无视科学研究和科学成果产生的规律,片面追求论文发表的数量,不能不说在有意或无意地为学术腐败的滋生提供土壤。可悲的是,即使在伪学术泛滥成灾的今天,一些单位仍然乐此不疲,依然将发表论文的数量(他们也时不时讲质量)作为“科学和知识创新”的重要标志。有人说这也是一些学界官员追求“政绩”的反映,这恐怕不是空穴来风。地方官员可以通过劳民伤财、大搞“形象工程”来突出自己的“政绩”,某些学界官员完全可以照此而为之。而一些规定和标准大抵正是符合了一些学界官员的“理念”,使他们更钟情于科研上的数量标准。更何况,有些规定和标准原本就是某些官员一起制定的,要他们破除这些旧的东西,创造出新的东西来,难!
从发展生产力、繁荣我国的科学文化事业的角度看,我们任何时候都非常需要有价值的论文,这样的论文愈多,其对社会发展的推动力就愈大。但是,论文倘若不是在科学研究的正常氛围中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而是这种靠“硬指标”、靠“枪手”或剪刀“创造”的“繁荣”,绝不是一种建设,乃是一种十足的破坏。它毁掉的不只是学术的良知,而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家园。因此,以愚之见,针对时下的学术腐败,恐怕也是“要从源头上治理”。这个源头是什么?我看,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我在以上所说到的那些已经失范的规定和标准。换句话说,只有我们把“规矩”真正弄科学了,才能为遏制学术腐败打下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