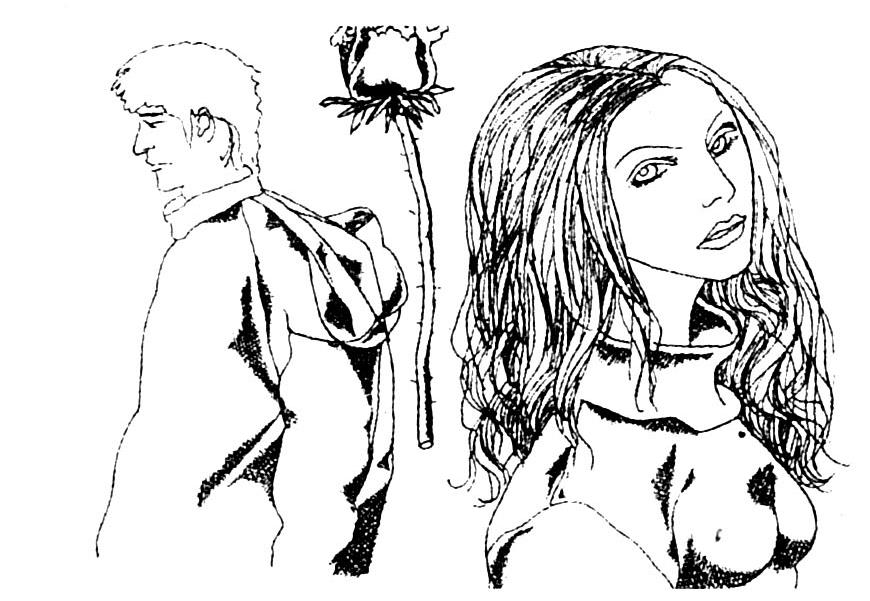〔西安〕 劲草

武钢是我的中学同学。接触不多,但印象颇深。他爱笑,又有一技之长,会拉二胡。
武钢变成了我的同乡。六八年,上山下乡到延安插队,我和武钢分在一个村里,我发现武钢人像被霜打的茄子,蔫了,笑声没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我们的关系。那天,队长派我俩卖菜。马车摇摇晃晃要走两个多小时才能到城里。一聊才知道,我们竟然同是天下沦落人。文革中,我的祖母被赶回东北老家,父母举家南迁江西五七干校,父亲隔离检查,母亲患重病在身。武钢的家更惨,父亲被赶回河北老家,精神失常,姐姐去了黑龙江建设兵团,没有工作的母亲做些针线活艰难度日。他告诉我,自从家里出了那么多事后,最大的愿望就是早点挣钱养家,可出身不好招工无望,心急如焚。我建议他不要丢弃一技之长,我们成了朋友。
武钢脸上有了笑容,话也多了起来。忽然有一天,他进城回来,拎了一只小提琴,第二天清晨,我们还没起床,就传来刺耳的琴声,不和谐的音律凄凉而悲怆。我起身推开门,看见武钢正站在硷坢上拉琴。我忽然明白他开始选择走自己的路,与命运抗争了。
我曾问他,为什么不练二胡,他说,文艺节目只有样板戏,二胡派不上用场。武钢终于盼来了这一天。那天,我们正在地里刨红薯,来了两位同志找武钢。几天后,武钢正式被录取到一个地区文工团。
离队的前夕,武钢找到我,他说了很多,感激、感谢、感慨的话,还表达了和我交女朋友的愿望。我想,武钢走出了人生低谷,我的前程未卜;武钢变成了挣工资的公家人,我还是挣工分的农民;我们毕竟还年轻,只有十八九岁,不谙世事,我没有答应他。
几年后,队里知青招工、提干,有了自己的工作和家庭,忙忙碌碌,失去了相互联系。忽然有一天,我收到一封同学来信,除叙旧外,简言告知,武钢已于三年前去世。这个消息令我震惊。利用休假回北京的机会,我和那个同学一起去了一趟武钢家。
武钢母亲的双眼在不堪回首的年月里,几乎哭瞎。她告诉我们,武钢到文工团后,工作紧张,生活单调,又没有知己诉说,心情一直很郁闷,就想千方百计调回北京,多次与中国青年报联系反映家里的情况,因为没有政策,困难极大。后来,不知谁给他出了个馊主意,他竟然将食指的筋切断,以无法拉琴为由,调回到北京。至此厄运并没有结束,他总是头疼,还不时伴有抽风,等被诊断出患脑瘤,为时已晚,不到三十岁,便英年早逝。……
斯人已去,琴声不绝,那是我们青年时代一段难忘的旋律,悠久地留在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