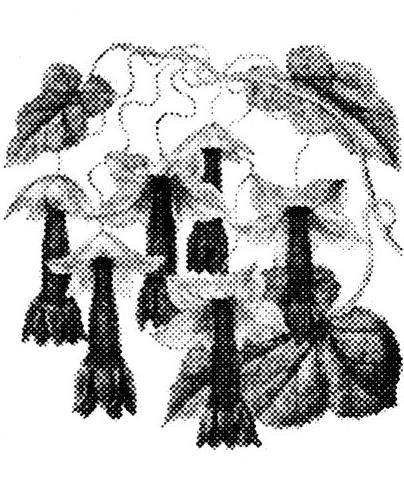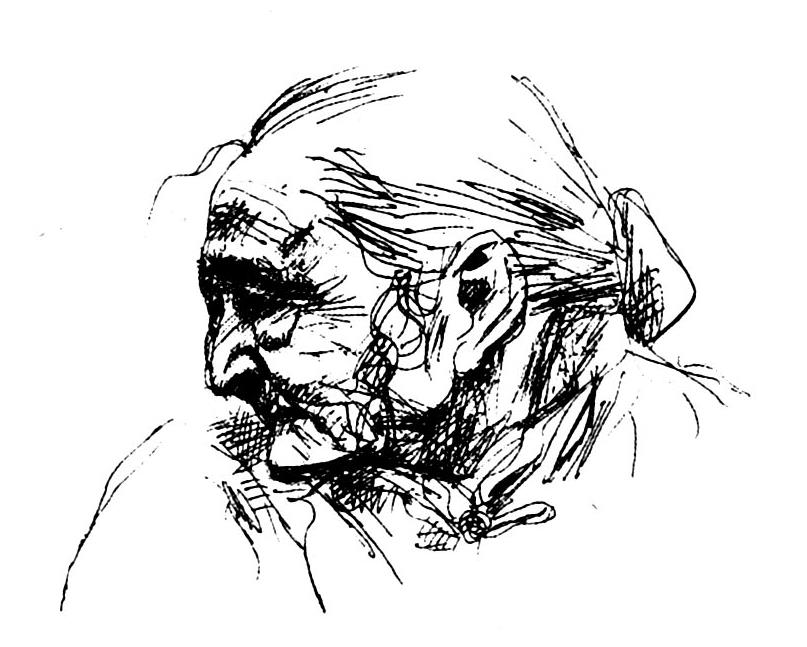〔宝鸡〕 润文
小时候,我和其他小孩子一样,到了腊月,就期盼着过年。
朦朦胧胧地还不知道啥是年。期盼的只是要换的一身新衣裳,一串红绿诱人的小鞭炮,还有几张崭新的能花、能换、能在小伙伴中攀比、炫耀的毛毛票——压岁钱。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期盼发生了变化,逐渐酷爱上了能给干枯的腊月带来绿色,能使新春佳节丰富多彩的关中窗花。
过去,老宝鸡的城里人,过年家家户户贴窗花。
吃过腊八粥,躺在炕角。看到母亲从炕柜深处翻出那包裹了里三层、外三层父亲用的大帐本。翻开来,里面全是五颜六色的彩色纸和各式各样的窗花底样。
母亲没有文化,可心灵手巧是有了名的。
她哼着很少听她唱的关中小调,脸上挂着慈祥的喜悦。将每张纸按尺寸裁好,正反两张折起来,全神贯注地挥动着剪刀。一会功夫,就剪出了十几套窗花,然后,精心收好。
腊月二十八早饭后,母亲把哥哥、姐姐叫到屋里,将两个窗扇卸下,撕去旧了的窗纸和褪了色的窗花。又将窗框洗净、擦干,按照色彩的搭配和早已比划了多次的位置,小心翼翼、端端正正地贴上窗花。
上好窗扇,关上窗。顿时,满院生辉。
10岁那年,父母已有了6个孩子,早年做的两桩生意也“合营”了。父亲每月40多元的工资已无法供养家庭。母亲进了工厂,紧张的工作,打破了原来的生活节奏。已过了祭灶,还没见母亲动剪刀。
心里着急,腊月二十六,我跑到大舅家,向在中学里教美术的大表哥要来一支水彩笔,一盒快用完的六色水彩。第二天,一个人关起门在房子里按着窗格子的大小画起窗花。画完后,神秘地将它藏了起来。腊月二十八,当母亲拖着沉重的身体回到家里,看到新换的窗子上已贴上我画的窗花时,吃惊地眼里含满了喜悦的泪水,露出了欣慰的笑。从不夸奖孩子的她,第一次那么认真地夸了我。
从那以后,每年春节的贴窗花便成了我——一个男孩子要操心、要完成的一项神圣的任务,一直持续多年。
1991年,为八个子女奔波了一生,又被多次政治运动教育、帮助了多年的父亲去世了。这年春节前,我又拿着买来的窗花准备贴时,母亲却将它收在准备烧的纸钱里。她拿出剪刀,找出两张很少用的紫色油光纸,默默地剪了两个菊花,贴在窗上。
事后,我才知道,亲朋好友家有了婚嫁喜事,得了儿子、孙子,就要贴喜鹊;有了白事,就要贴紫色的菊花……我知道了许多,也深深地感悟到了,窗花,是母亲用手、用心、用情给儿女留下的无法忘怀的情结、思念和寄托。窗花,是只有我能够理解、体会、读懂的内涵丰富的诗。窗花,已成为我每年要献给母亲最好的节日礼物和回报。
又要过年了,心里开始筹划着啥时给母亲买窗花、贴窗花。真想再看看50年前年轻、漂亮的母亲剪窗花时的笑脸。听听“二十八,贴窗花”时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