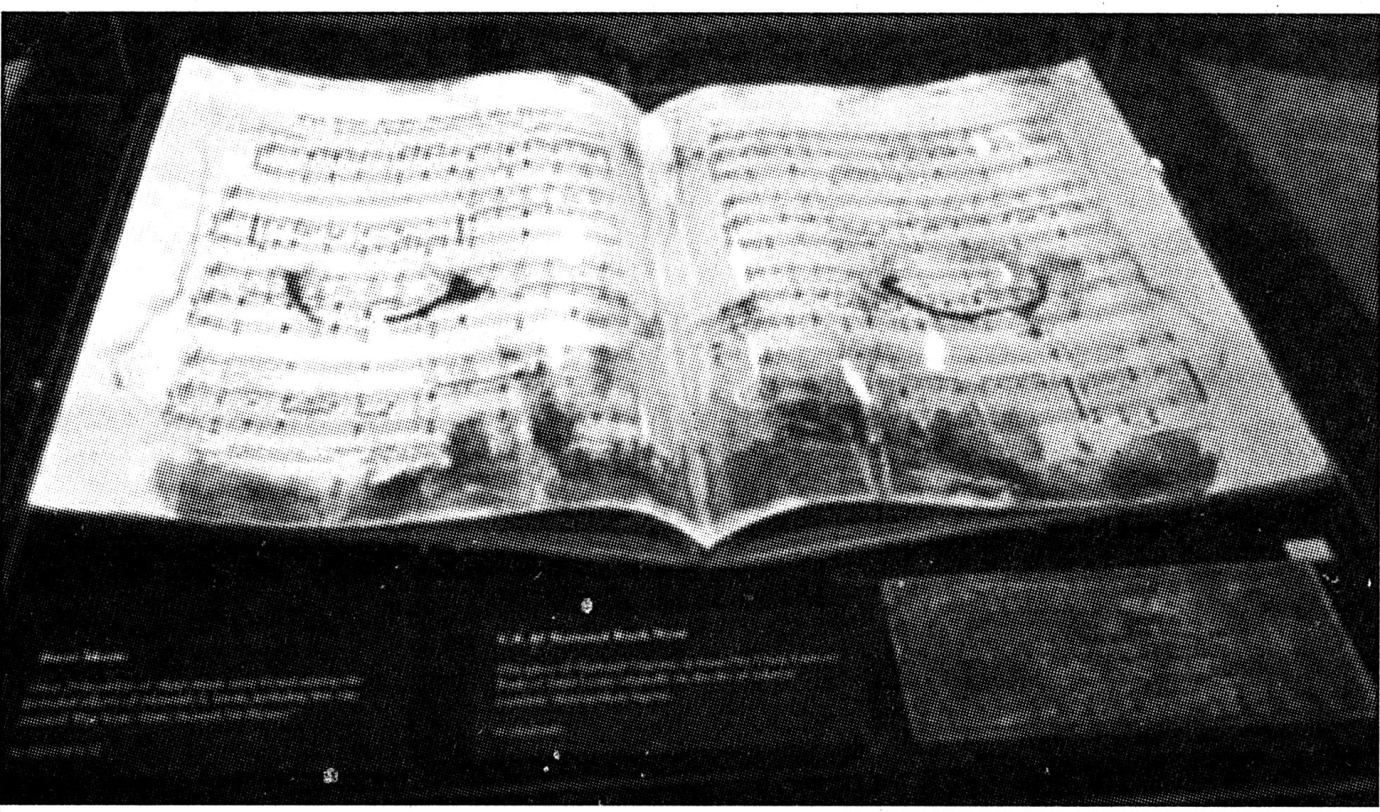·黄宗江·
命题:《我的书斋》。当答:“有!”沉吟,又拟答:“无!”怎么这样具体的事物却如此似有若无呢?
自幼开卷便悟:只有对书,才可与大人小人、今人古人、国人洋人对话、对思、对心。由于种种教养,我对书中自有黄金屋、颜如玉之类从没什么幻觉,却深悟到书中自有一切。
从幼时有第一个书架起,便想着再一个又一个,书架多了便成书斋了。没想过这世界上我会据有什么,但的确想过我应据有一书房,雅称书斋,是属于自己的。书越多越好,书架越高越好,最好是高及屋顶,有可移动的小梯子供攀登取书。岁月如流亦如凝,书籍亦流失或堆积亦如岁月。我如今已入耄耋岁晚,各方面均难再做高攀想。
书必有劫,虽历经焚书、缴书或作废纸售,老实交代存书仍不少。书架也还有若干个,难拘一格,散放各室,难以列成书斋。且因搬迁,一部分书被我家聪明的保姆安放在我双人床下的空当儿之内,内有冰心、巴金、萧乾、萧军、夏衍、曹禺……诸大师亲笔题签的赠书,倒真的成了珍藏,不至于沦落“潘家园”了。
我之未能有藏经楼阁,也和我的行业有关。我大学学业未毕,即下海从事剧影,成为一个艺人,后虽转化为文人、军人,仍从事剧影为终身职,实质上仍属艺人。我很小就憧憬做一艺人,且最向往流浪艺人,行吟一世。此生虽说不上流浪,可称浪游;倦而思归,也就是归隐书丛,仍难称斋。抗日中期,我随剧团跑码头至内江,在茶馆里写了一卷散文,自题为《卖艺人家》,自认为妥帖,颇为自得。多少年来,得到不少位师友名家的赠字赠画,苗子大兄且为我作一横匾,无奈字大屋小难高悬。乃悬于我情结万种、想象中的书斋,在此披露,以飨诸书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