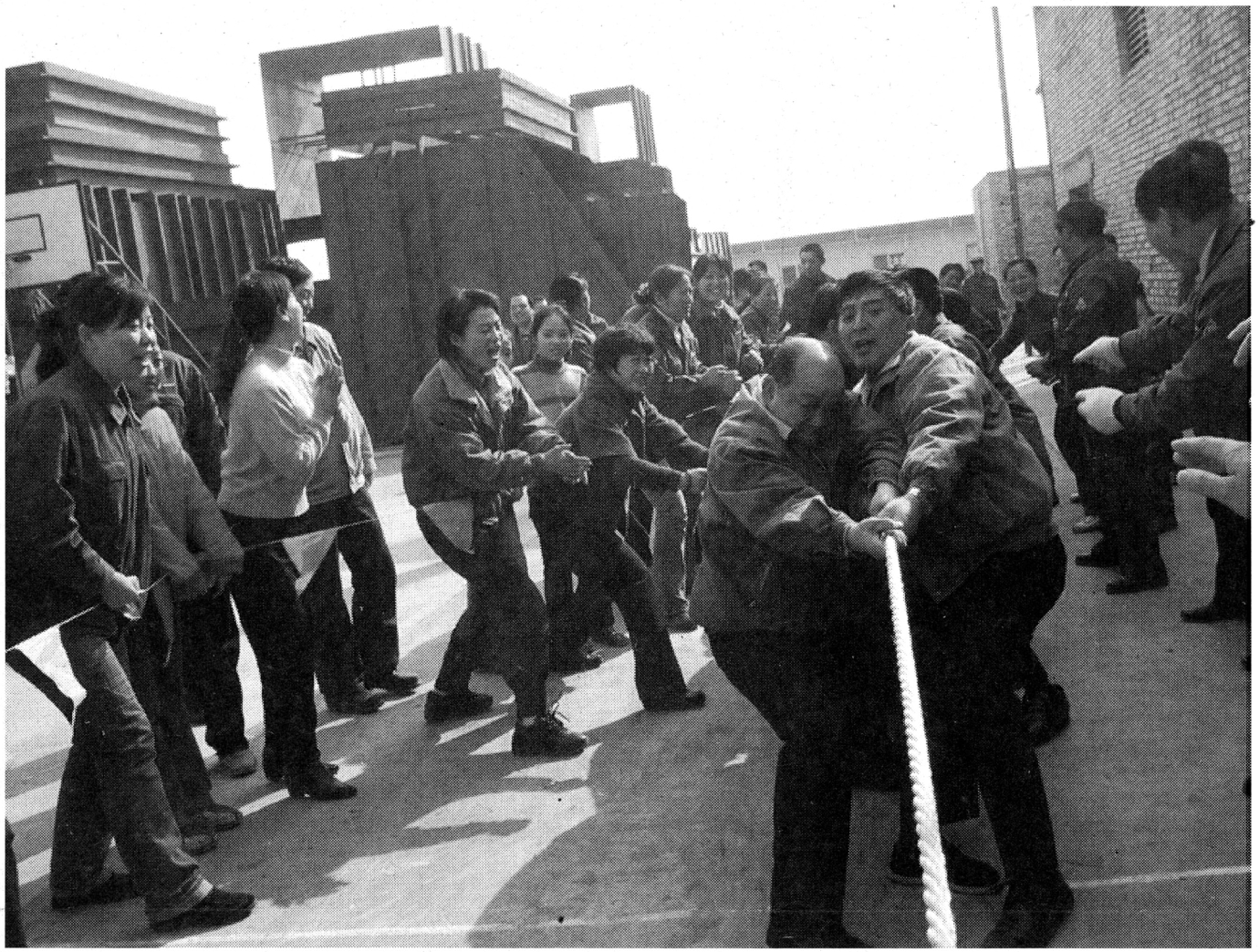[案例]
某保安公司职工韦某晚上驾驶无号牌二轮摩托车上夜班,途中与骑自行车的郑某相撞。随后,韦某驶离现场200米左右,还是在上班的必经道路上与电线杆碰撞致摩托车损坏韦某死亡。交警部门就此事故出具两份交通事故认定书:第一份为韦某和郑某相撞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其认定的事实是韦某驾驶无号牌摩托车和郑某所骑的自行车发生碰撞事故致郑某受伤,事发后韦某驾车逃离现场。另一份为韦某与电线杆相撞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其认定的事实是韦某和郑某发生碰撞事故后韦某驾车逃离现场,在驶出200米许和路边电线杆发生碰撞致摩托损坏韦某死亡。两份认定书都认定韦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但韦某已死亡,公安部门不再对其进行处罚。
韦某的亲属向当地劳动保障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要求认定韦某属于因工死亡。当地劳动保障部门调查后认为虽然韦某驾驶无号牌的机动车和肇事逃逸行为违反了有关治安管理规定,但公安机关未出具其违反治安管理的文书,而韦某确属在上班途中发生机动车事故死亡,认定韦某属于因工死亡。
韦某单位对韦某属于工亡的认定决定不服提起行政复议。在行政复议过程中双方辩论的焦点是:韦某的行为是否属于违反治安管理导致伤亡。韦某单位认为韦某的行为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一)款“因犯罪或者违反治安管理伤亡的”应当不得认定工亡;劳动保障部门认为公安部门没有出具书面文书定性韦某的行为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而劳动保障部门无权定性韦某的行为是否违反治安管理,在单位没有提供公安部门相关文书的情况下,只能认定其为工亡。最终市政府维持了劳动保障部门的结论。
韦某的单位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在行政诉讼过程中,韦某的单位提出一个新的观点:韦某在上班途中与郑某相撞后逃离的200多米已不能定性为上班途中,而应当定性为肇事逃离途中,因此韦某的第二次交通事故即和电线杆相撞事故应视为肇事逃离途中发生的交通事故,不能认定为工亡。当地劳动保障部门则认为韦某第二次交通事故也是在上班必经的道路上,其行驶的方向也是朝单位方向,故应视为上班途中。[评析]
笔者认为在适用《工伤保险条例》十四条六款“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条款时,应同时把握“上下班途中”和“机动车事故”两个要素。“上班途中”不仅反映了职工的行为,而且强烈反映了职工的主观动机。对照韦某死亡案例,韦某从家中出发到死亡应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韦某从家中出发到和骑自行车的郑某相撞发生的第一次机动车事故,这时韦某的主观动机是去单位上班,第一次机动车事故应视为上班途中发生的机动车事故;第二阶段是韦某将郑某撞伤后逃离现场途中和电线杆相撞致死亡发生的第二次机动车事故,尽管韦某的行驶仍然是朝单位方向,但主观动机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其动机已由“上班”变为“逃离”,根本目的是逃离现场而逃脱赔偿责任,此时韦某的行为应定性为“按原行驶方向逃离事故现场途中”而不能视为“上班途中”,因此第二次机动车事故应视为按原行驶方向逃离现场途中发生的机动车事故,不属于《工伤保险条例》十四条(六)款的范围,因此不属于工亡。最终法院采纳了上述意见撤销了工亡认定结论,同时单位也给予韦某亲属一定数量的经济补偿,此工伤认定案件方尘埃落定。 (姚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