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曹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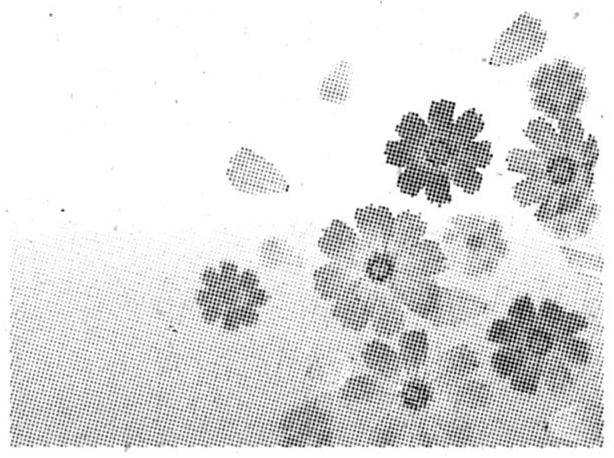
一天,一个人整理书橱,看见书橱的一角静静躺着一大摞旧信件。目光触及这些“陈年古董”,悠悠往事随着逝水的年华已成为人生隔岸的风景。这些信件都是我年少时的同学和朋友写来的,在我结婚以后,它们一直被我遗弃在父母的老屋里,直到数年前我回去,偶然间惊喜地发现了这些旧物,忍不住把他们带回来了。
我收到的第一封同学来信是在我心境及其痛苦和落寞的时候,那时1987年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春。当我的同学正在高中课堂里学习新知识时,我已卷起铺盖去部队了。生活在他乡,我仍走不出失学后带来的那片灰暗天空。同学子静的一封信寄到我的老家,辗转一个月后终于到了我的手里。在隐约的春风里,我静静地拆阅了这封普通的同学来信。信中,她详细叙述了她高中校园生活以及她遇到的困惑和烦恼,并询问我的近况和今后的打算。信中的末尾写道:“把所有的困苦和磨难都看作是有意思的吧!那是对生命的磨炼,是人生的一笔财富。部队是所大学,振作起来吧!你将看到生命的春天正向你走来。”我几乎是含着热泪读完她的信的,脆弱敏感的心被温暖的同学友情深深感动。子静是我保留的86封旧信里数量最多的一位作者。
有一些尺寸略大的牛皮信封,那是我一个远赴海南的朋友寄来的,她在写来的10多封信里,一直选用一种花色淡雅的漂亮信纸,再加上她娟秀的字迹,信件的折叠也别有匠心,富有视觉上的美感,装帧的像情书。我从她的文字里了解到她在特区的另一种生活以及人生地不熟的无奈心境。
还有几封盖着红色三角印的部队来信,那是我一个兵哥哥寄来的。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全是一个大哥哥对小妹妹的关心和爱护,用我今天的侦察性的眼光再来阅读,也找不到一句暖昧的话语。他的信在我为数不多的13封异性信件中占了7封,另外6封分别是在我20岁以后因工作关系或深或浅交往过的3个异性朋友,他们因了这样那样的原因各给我写过两封信,全都是纯友谊的,如今我们都已失去联系。我的旧信中没有一封是情书,这不能不让我感到有些许遗憾。
一些粉红色和白色的信封,从字迹上我便认出了是当年师大W同学和C同学寄来的,语言里或多或少地流露着她们当年的远大理想和美好憧憬……
我坐在书房的地上,在杂乱的信件中,从一封读到另一封,从一个友人看到另一个友人,多年前的信件在我手中无序地展开、折叠,再展开,仿佛过去的无数个白天黑夜被我随意地颠过来又倒过去,有一种置身于时间隧道的幻觉。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这令人揪心的日子悄然而至,离村几里外的公茔里,忽然间就飘满了忧伤。在公茔的东南角,安息着我的父亲。
父亲20年前离我而去,尽管时间推移,星斗转移,我也步入了多病的知天命之年,但父亲的音容笑貌,却时时萦绕在我的身边,对父亲的思念,常常伴随在我生活的白昼与心灵间。
父亲是个很普通的农民,一个地道的饱经风霜、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给人拉过长工打过短工的庄稼汉。解放后当过最大的“官”是生产队贫农代表。他一生最显耀的经历仅是在扶眉战役中给解放军用马车运送过弹药。76岁的他临终那年,我家老箱底翻出了他“贫协会员证”和49年解放军首长给开具的运送弹药的证明。
作为农民,父亲最大的能耐是耕作土地。据老辈人讲,父亲从青壮年起就爱田如命,解放前给财东拉长工时经常领工,给人家干活时心眼特别实,很卖力气,以至于地主老财和他也建立了“感情”,常年雇他。犁地,耱地,撒种子,扬场,摞脊,赶马车,样样精通。解放后我家自留地的庄稼是队上上好的收成。集体锄地时,小伙子们都不愿意跟他在一块干,嫌他锄地快,总把年轻人甩在后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