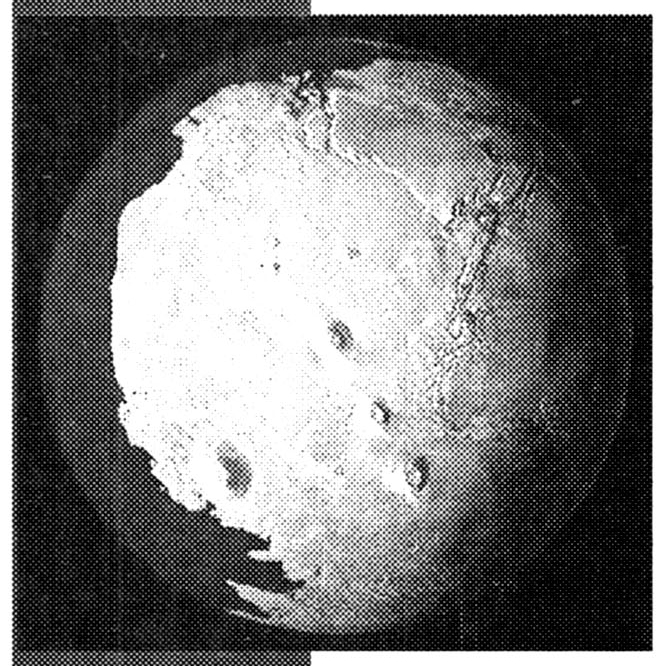《我的千岁寒》:它取材于《六祖坛经》,前三分之二有太多的东拉西扯,呓语连连,但还是有意味和质感的,想象性的唐朝“南方”弥漫着潮湿、传奇,间有妙语妙句。而后三分之突然转了,折了,脱了,气息全无、规规矩矩地把六祖惠能的传奇故事摹写了一遍。在这篇文字中,靠谱的部分是我们熟悉的旧故事,而属于王朔“创造性发挥”的部分多少都有些不太靠谱:譬如说“法海和尚”在故事中的介入;譬如他这样说庙:“庙,不聊了,庙就是和尚吃糖,歇转儿,出离物质观的地方,后来成了纪念堂,成了面面观,成了大使馆,成了邮局,激流中人摁下葫芦起来瓢投下物力等浮力——一报还一报的地方”,譬如在文中解析“一对人,生孩子,这是利己还是利他?”等等等等。《宫里的日子》:“阿武”是武则天,“老李”即唐太宗李世民,“小李”乃唐高宗李治……在王朔本书中,这是惟一一篇完整的、没有跑太远的文字,它的细节设置有趣,然而也过于简单了。《宫里的日子》,宫廷争斗只是背景性的,概念化的,王朔给予阿武、小李和高阳公主的是琐细的、类似过家家似的秘闻逸事,性格和内心被完全滤掉了,呈现给我们的只是表象性的东西,而且近乎是香港电视剧《武则天》的简写版。《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这里至少有两点他没有做好:一是佛经和古汉语中的丰富、多解和微妙被他的再译丢失了不少;二是它应当有必要的严肃和严谨,“必须觉悟!菩萨应该这样进村发动群众”、“菩萨不装人民的儿子”、“我牛掰我是罗汉”这样的句子调侃得太直白。《妄想照进现实》:两个人,一间房,惟一可利用的“道具”是一个厕所——我敬佩王朔给自己制造了难度,这难度几乎难以想象。一部电影,全靠两个人的对话来推进,那它必须在语言和细节上下大功夫聚起魅力,善于无事生非……然而,王朔在现实和世俗的场子里浸渍太久了,他缺少上升的能力,所以它最后仅仅是一男编剧和一女演员之间的日常对话“实录”,特别是后半部分,王朔又虚脱了,将它变成了简单的文字游戏,脱离了叙事核心一路卖弄下去……《与孙甘露对话》:绕的是电影,剧本创作,和钱。《唯物论史纲》:“全知——全能即上帝。物质全知——全能。——物质等于上帝。”“宇宙无限,宇宙无邪,所以宇宙不需要意志。——相互湮灭后只剩下秩序。”这是书中的原话。我不懂,不敢妄言。可在一则访问记中(同样是那篇访问记)说王朔依借毒品和佛经了悟了生死如何如何,我却有大大的疑问。这本凑起的书,凸显了王朔想象力、原创力上的不足。六篇作品,三篇有摹本,一则访谈,一则论文,真正属于自己原创的,只有一篇《妄想照进现实》,它还应当属于对日常的描摹。另外,王朔的语言也过于“拧巴”了,当然不完全是语言上的问题,更多的是思绪上的问题,他太信马由缰,缺少逻辑感,就是那篇《我是谁》的自序,最后也写走了,写飞了,写散了,充满了呓语。 (李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