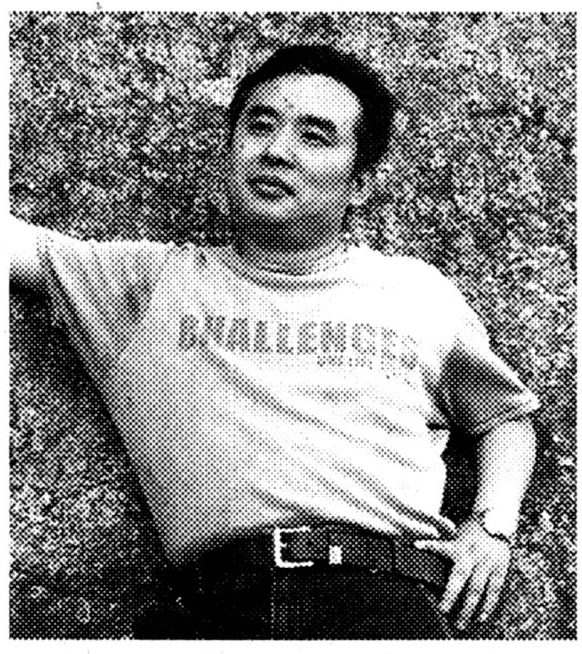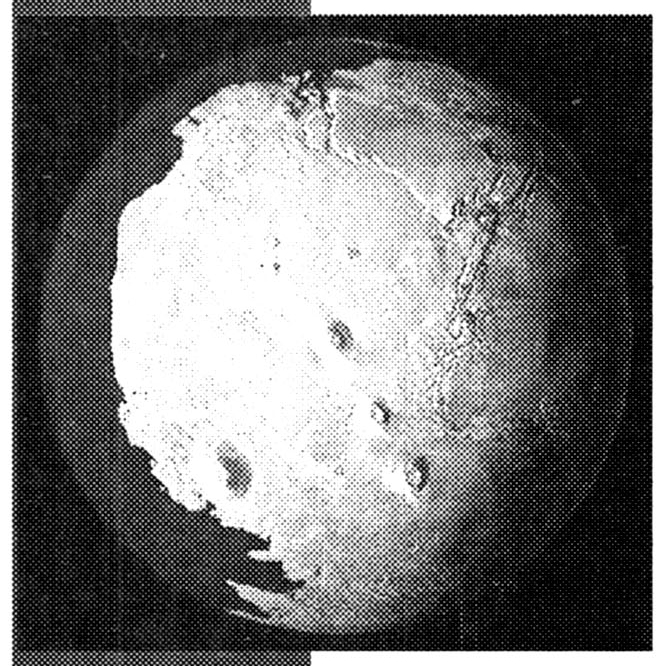我自小多愁善感,格外爱哭。大人们烦我,给我起个外号,叫“哭鬼”。成人之后却矫枉过正,该哭的时候我都能咬牙忍着,哪怕把泪水憋成血。我看上去总是嘻嘻哈哈,却常在觥筹交错之际倍感忧愁和孤独。很多次我在热闹的交际场合突然抽身告退,怕自己脸上不经意的阴云扫了大家的兴。医生终于忠告我:您患有抑郁症。
抑郁总需排遣,我的办法不是就医,而是读书。想来我读书解忧的办法,自小就试过了,只是当时并不自知。大概十一二岁时,一日百无聊赖,从大哥枕头下翻得一本残缺不全的《红楼梦》,竖排繁体。我半认半猜地看,知道那书里的人成天哭呀,拌嘴呀,要去死呀,要去做和尚呀,看得自己不禁流起眼泪。奇怪的是,看了书里人的忧愁,却忘了自己的忧愁。我并没有把自己看《红楼梦》的感受告诉任何人,只是独自沉醉。
小时候还有一本书,叫我十分惊奇。那是本《古希腊神话故事》,照样是残损得没头没尾。那时候乡村孩子能看到的书,除了学校课本,就只有红宝书。我至今记不得,这本讲述外国神仙故事的书是怎么到我手里的。这本书里讲到的神自然是法力无边,却比人有更强烈的欲望,更复杂的感情,更狭隘的心胸,更令人叹惋的命运。一个没受宗教洗礼的孩子,读这种书的结果就是对任何神充其量只有畏惧,不会信奉和敬仰。
我真正开始读书是上了大学之后。最初嗜读的是外国文学作品,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海明威。契诃夫的戏剧作品我尤其爱读,喜欢他的《海鸥》《樱桃园》和《万尼亚舅舅》中的孤独、怜悯和诗意。
我对法国文学情有独钟,为什么如此我也说不清。法国人好像天性浪漫感性,但他们的文学很思辨。我爱读拉伯雷的《巨人传》,多年之后还鼓动八九岁的儿子读。
中国古典文学中,最值得读的是诗。中国古典诗可以终生读,反复读。诗不但移情,还能移性,叫人纯粹和雅致。一个以写作为生的人,通常会困窘于语言,自觉脑拙笔钝。那么就去读古典诗,也许会拯救你的笔。沈从文先生说自己找不到语感了,就读几段《圣经》,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虽说读书解忧,而忧愁如影随形,不问人的境遇,不问周遭世情,那么,只有不断地读书。
常有朋友让我推荐书目,可我乐意介绍的总是很老的书。
(王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