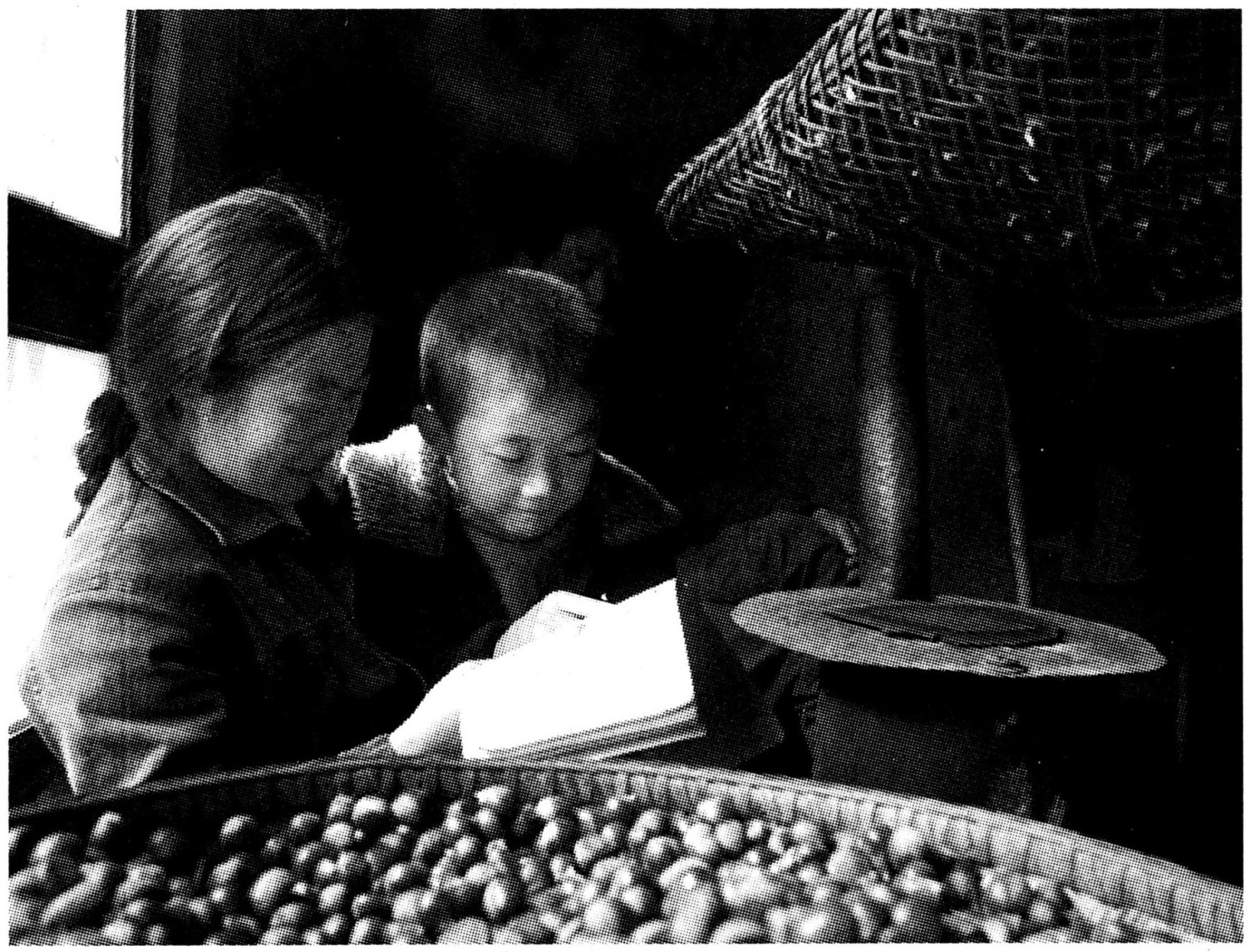□文/张丛笑
“笃!笃!”,又是敲门声。妻子没好气地走过去开门。只见门外一张陌生的脸,端在低头哈腰的身子上,问:“请问,这是杨局长家吗?”妻子立即耐心答道:“不,杨局长家在对面!”妻子没好气地关上了门,气咻咻走回来,坐在沙发上,对我说:“这帮人,手下大包小包的,送礼,连门都弄不清!”
我在看报,抽烟。这种事,我遇得多了,所以已经麻木了。记得读贾平凹的《废都》书,书中写到一个市长家里,进门后有一个库房,凡送的“礼”都给库房里放,什么电冰箱、电视机都有。这些手下捏包包蛋蛋的算啥?
这天半夜,妻子没有入睡,她摇醒我说:“你猜错了吧,你还说你是诸葛亮!”我说:“什么诸葛亮?”妻子说:“去年年初,杨局长的单位盖了房子,都是130多平方米的,你说杨局长很快会搬走的,他蜗居这里做什么。怎么现在还没搬?”我记起来了,去年起初,听说杨局长的单位建了一栋楼,又见他的僚员们一个个喜迁新居,已为杨局长指门指得烦透了的我家,当然只盼着他快点搬走;妻子更迫不及待,并用探询的口气问我:“杨局长搬不搬家?”我便撂出一句:“你放心,我是诸葛亮,会掐会算,保他‘五一’前搬走!”可是,去年“五一”过了,“十一”过了,元旦过了,眼看今年的“五一”来临,杨局长家还是“巍然不动安如山”。我们仍天天在“笃笃”的敲门声中,过着为许多人“指门认路”的日子。
“说话呀!诸葛亮!”
妻子问我。
我不知咋回答。
妻子叹口气说:“我明白了,他是永这不会搬走的了。”
“为什么?”
我问。
妻子说:“住咱这儿的人,是杂户,没人监督。他若住他们局的院子,那么多送礼的人,进进出出,门房还要登记,方便吗?弄不好,人家说他不廉政呢。住咱这儿,就不用操那份心,咱这大杂院正好是避风港!”
我一惊,说:“真的是这么回事吗?”
妻子说:“他今年多大了?五十二,那我们就再等八年吧!不信,你试试看!我的诸葛亮同志!”
我心下大诧,感到自己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