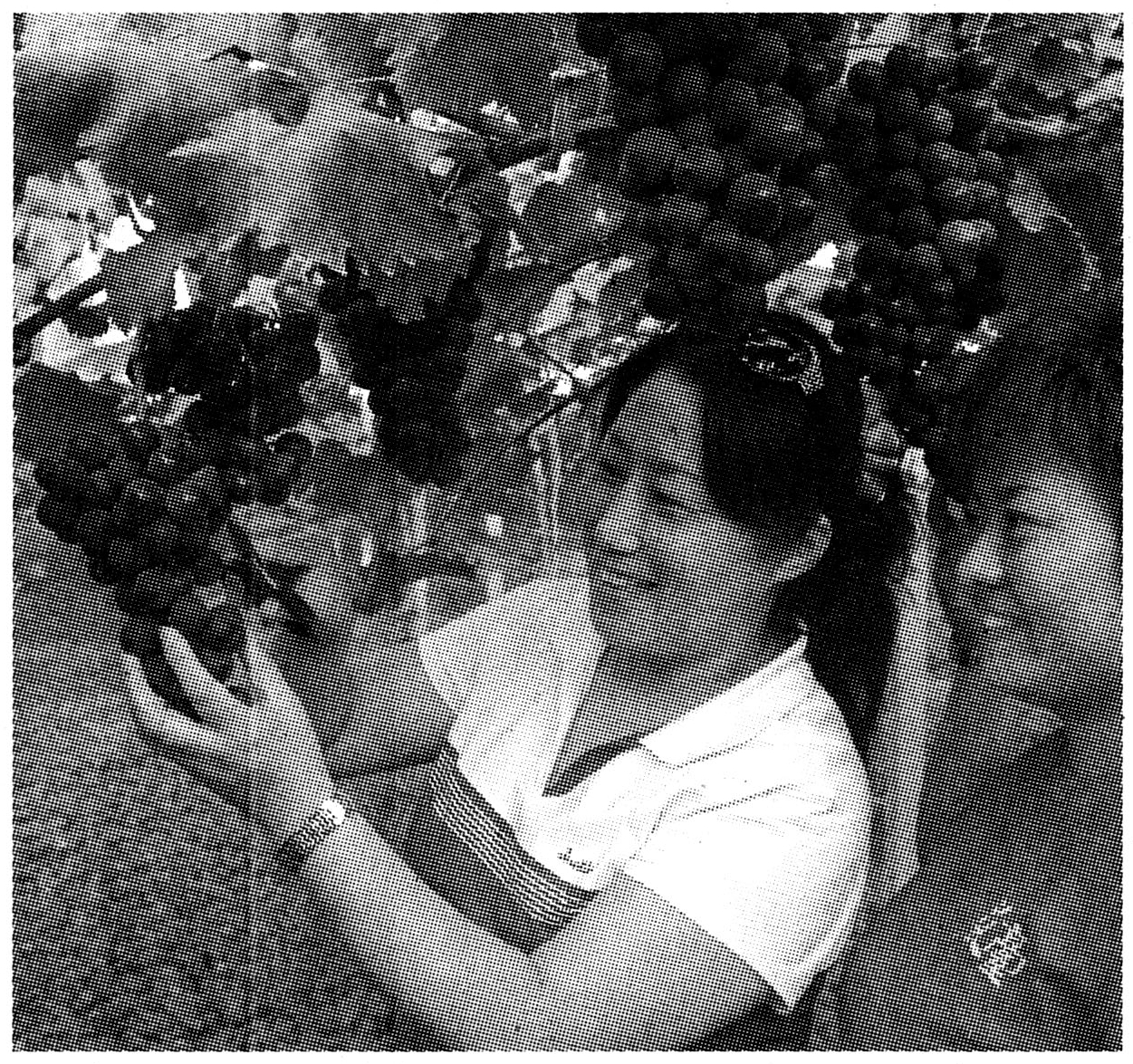□文/杨艳荟
从三原到耀州,关中平原的地质结构发生了奇妙的变化。放眼处不再是一览无余的“八百里秦川”,渐渐出现的山梁土卯一次次阻断了人们的视线。愈是向北走,黄土高原的地貌特征表现得愈明显。到了耀州北面的铜川老市区,就只剩一条狭长的川道了,古耀州窑遗址就坐落在黄堡镇的漆水河峡谷台地上。铜川旧称“同官”,属耀州管辖。这里有着冶瓷的天然资源:优质煤和上乘的坩子土。上世纪50年代初,考古人员在黄堡镇发现了大量的瓷器碎片和窑炉、灰坑遗迹,经深入考察和挖掘,证实黄堡镇即古耀州窑系的中心。那时大大小小的窑炉和瓷器作坊密如峰巢蚁穴,众多窑院你方熄火我又点炉,由南到北绵延数十里,被人称作“十里窑场、炉山不夜”。据陶瓷专家的研究,越州青瓷是中国古代青瓷发展的第一个高峰,耀州青瓷是第二个高峰。而江西景德镇在五代时受越窑影响开始烧制越窑系青瓷,并在北宋中晚期达到鼎盛。古越州和古耀州两地的青瓷,一南一北,各有千秋,却共同书写了青瓷烧造的神话。
耀州青瓷曾因“巧如范金,精比琢玉”而贵为贡瓷,在唐、宋、金、元时期被源源不断地送进皇宫。它有模印花、刻花、堆塑等技术。尤其是能够在素坯上刻、画、剔出各类图案,以及宫中专用的刻有龙凤图案的御瓷。我曾送友人耀州窑生产的黑釉剔花花瓶,外形是耀州窑有名的玉壶春造型,上有西安美术学院教授工笔绘就的美人图。值得一提的是,黑釉剔花烧造技术是现代耀州窑产品的新发明。黑釉的色泽干净凝重,在上面剔出各种图案,反而成为看惯了红红绿绿的现代人的最爱。
耀州青瓷瓷胎为灰色,釉色以青绿色为主,有青花釉、黄釉、酱釉、月白釉、茶叶末釉、黑釉、铁锈花等,色彩丰富、变化万千,但基本上一件瓷器只上一种釉色(这里不包括唐三彩,事实上耀州窑也是唐三彩的故乡)。景德镇青瓷却是白瓷彩绘,如粉彩孔雀牡丹盘,及近代的粉彩过枝梅花纹洗等都是白瓷彩绘的。与景德镇瓷相比,我还是更喜欢家乡的耀州瓷。因为除制作精美的贡瓷外,耀州生产的粗瓷与秦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甚至北方百姓常用的碗、盘、盆、罐、瓮、坛、缸等等,亦多与耀州窑相关。北人喜面食,陕西卖面的餐馆,多在醒目处画一只耀州大碗,而面食盛在这样的青花大老碗里,恰是相得益彰。近几年,有一种“老碗鱼”颇为流行,看着那个直径几十厘米的大老碗就让人心生喜悦,这也是耀州瓷的魅力所在吧。
耀州人生性质朴,说话、办事直来直去,高兴了吼两嗓子秦腔,家里要来了客人,女主人就倾其所有,碟碟碗碗地往桌上端。耀州粗瓷结实耐用,俗语中常用“耀州瓷壶”戏谑那些反映迟钝的人。而正是祖祖辈辈生活在黄土高原腹地的耀州人,在自家的窑院里潜心烧造瓷器,在土与火的舞蹈中,悠悠岁月在他们的手里化作了一件件晶莹如玉的宝贝。因此,我宁可相信,那些精美的耀州瓷是黄土高原的乐章,是黄土地的魂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