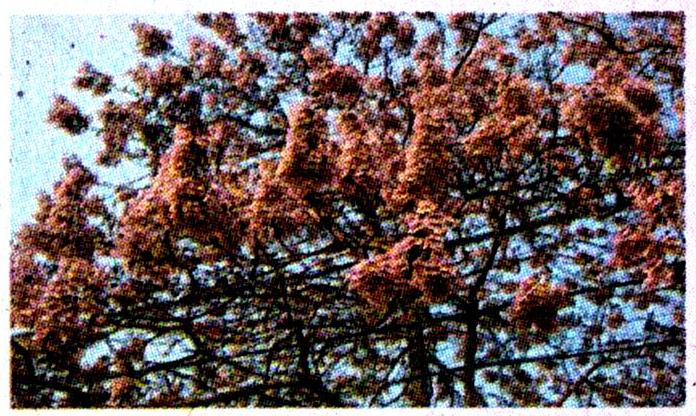(宝鸡)张少华
不知不觉,煤油灯已经走进了历史的封尘。
我有记忆的时候,家里就是煤油灯,全村都是煤油灯。我的童年就是在煤油灯的幽暗里艰难而又自然而然地度过的。上小学的时候,每天晚上奶奶在炕头点一盏煤油灯纺线,而我就趴在奶奶的纺线车跟前,凭借黄豆大的一点亮光铺开作业写字。
冬季上学很早,那时候家里没有闹钟什么的,奶奶说鸡叫三遍就是我该起床上学了,大约是五点左右就要到校。去那么早,当然学校是没有电灯的,小学生每人点一盏煤油灯,放在自己课桌角上照亮。有一天早晨出奇的冷,地上满是冰,一点月光都没有,我手里端一盏煤油灯,路过的一户人家养了条大黄狗,本来走到他家门口心里就诚惶诚恐,加之天黑路滑,我更是蹑手蹑脚。突然,黄狗“旺旺……旺旺旺……”地一叫,我一个趔趄,摔倒在地上,煤油灯还紧紧握在手里,油却洒没了,灯盖也不知摔到哪里去了。漆黑的夜啊,伸手不见五指,失魂落魄之中,我在地上瞎摸了一阵子什么也没找见,怕狗真扑出来,就下意识地撒腿跑开。等我气喘吁吁到了学校,别的同学都点起了煤油灯早读,我的桌子上当然是黑着的,老师就罚我站到教室外面。外面寒风刺骨啊,冻得我两手没处放,就撩起衣服直接插进棉裤腰里去,可风又从衣襟缝里钻进去,前心后心透心凉啊,双脚早都失去了知觉,记得鼻涕把胸前衣服弄湿了一大片,冻成了一片在晨曦中隐约可见的白光。我是听着教室里同学们嗡嗡嗡的读书声把课文背下的。站着站着,我听到老师问:“谁能背诵课文了?”教室里顿时鸦雀无声。我真是庆幸煤油灯下没一个孩子能背诵课文,直到天亮,老师叫我进教室的时候,我却突然放声大哭了。那种委屈,直到现在我想起来眼睛也是潮湿的。
如今,每每看到儿子在小书房漂亮的小橘灯下吃着零食做作业的时候,就会不经意地想起煤油灯,以及煤油灯下我的童年,想起那只黄狗……或许,我对电灯的向往就是从那个端着煤油灯上学的寒冷的早晨开始的。
几十年过去了,我对煤油灯的记忆格外珍重,是它最早给了我求学路上的光明,它昏黄得尽管微弱,但依然那么温馨,静静地跳荡着,暖暖地向我招手,久久映照在我生命中那个小小的酸楚的角落。每当看到今天的小学生快乐地成长,我更加坚信:一个人的幸福,其实就来自于让人十分怜惜的那一点希望,来自于蓦然回首不见灯火阑珊的童年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