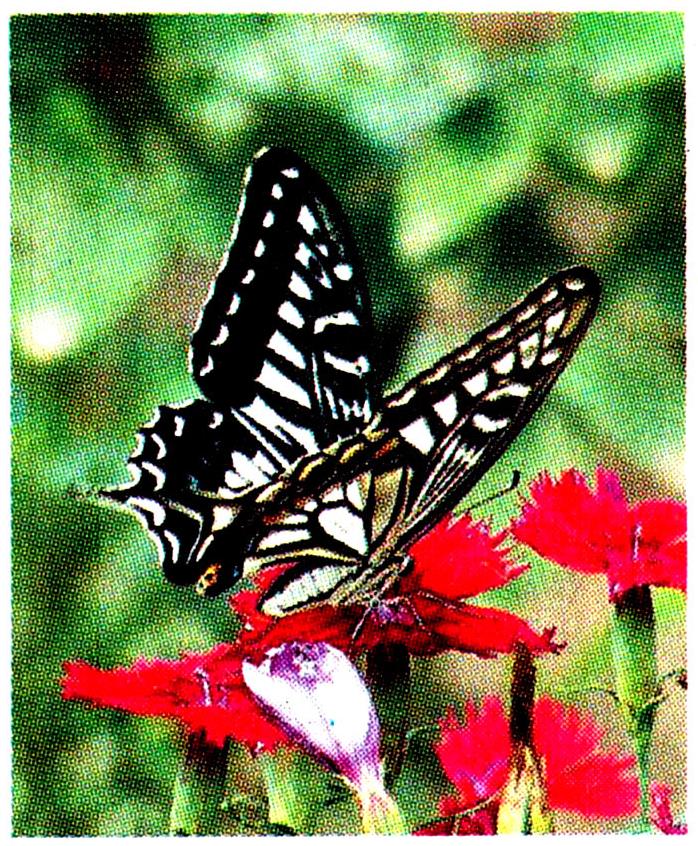文/张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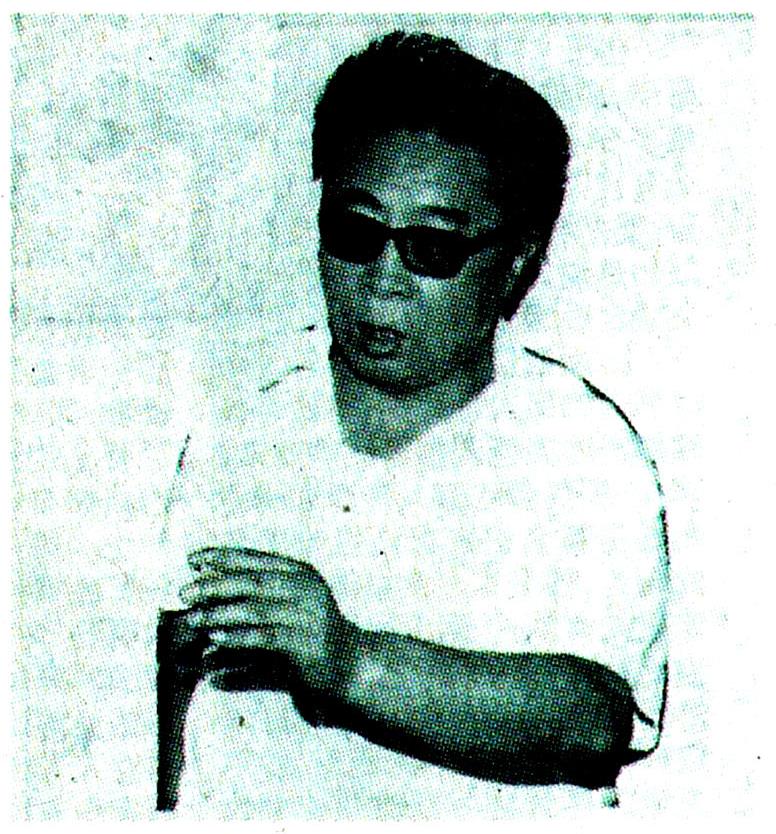
那是1983年7月的一天,我听到一个消息:作家曲波来到西安。我赶快把这个喜讯转告给我的好友----《人民日报》记者孟西安、《西安晚报》记者张逾升和四医大宣传干事舒英才。翌日,我们一行四人在四医大集体采访了曲波。
曲老那天心情特别好,高兴地打开了话匣子,向我们娓娓道来小说以外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他说,不少读者认为《林海雪原》中的少剑波是我本人,这不确切,只能说是我的一段经历。我只读过五年私塾就被迫停学了。15岁参加革命,17岁任连长,22岁在团里当政委。这个团没有团长,只有一个参谋长和一个政治处主任,我直接指挥作战。在林海雪原剿匪,和土匪打了72仗,有丰富的生活素材,为我写《林海雪原》打下了厚实的基础。1953年,我已从部队转业到铁道部齐齐哈尔车辆厂任党委书记。1954年腊月三十日的除夕之夜,窗外大雪纷纷扬扬,爆竹震天响。我特别怀念杨子荣、高波、孙达得等战友,他们的英雄事迹是这样的伟大,这样的感人,感情一下子把我带到了东北的战争年代。由于是亲身经历感受特深,所以下笔时十分顺畅,一气呵成。我只用了8个月时间,《林海雪原》这部40万字的小说就写成了。完稿后,我抱着一大堆书稿去找出版社,由于外文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是对门,我送到了外文出版社,后来才转到人民文学出版社。20天后,编辑王笠云打电话找我,让我把白茹和少剑波的爱情再展开写一写,于是,我又加写了“少剑波雪乡梦情心”插进了小说。
当谈到《林海雪原》中的人物时,曲波说杨子荣、高波、孙达得及敌方的座山雕、小炉匠都是真人真事。杨子荣当时是侦察排长,我不愿写他牺牲,实际上杨子荣是在林海雪原中打最后一仗时,被郑三炮打中一枪而牺牲的。杨子荣墓在牡丹江地区海林县烈士陵园,1966年重新修整并取名“杨子荣烈士陵园”。
我们问起小说中的白茹是否确有其人时,曲波说这个人物是虚构的。接着他风趣地回忆,1956年,他在北京市人民医院住院。一天,他正和医务人员闲聊,突然贺老总穿着住院服走了过来,贺老总听说他是一机部的(曲波1955年调至一机部第一设计院),就说:“我向你打听一个人,你们一机部有个叫曲波的,他写了一本书叫《林海雪原》,你认识他不?”他赶紧敬礼回答:“我就是曲波。”贺老总马上热情地把他介绍给周围的医护人员:“他曾是一位年轻的军官,他写了《林海雪原》这本书,你们都要看!”医护人员说:“我们都看了。”贺老总说:“你们要多看几遍。”接着又问他:“你爱人白茹来了没有?”他说:“我爱人叫刘波,14岁参军,15岁当护士长,参加过东北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现任北京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贺老总以军人的口气命令说:“我不管她叫什么,就叫白茹!”当时他也不敢纠正,显得很尴尬。
继《林海雪原》后,曲波又相继写了《山呼海啸》、《桥隆飚》和《戊萼碑》三部小说,深受读者好评。
采访结束时,曲老为我们四人分别题词留念。为我挥毫疾书“奋进,求索”四个苍劲大字。曲老说:“这四个字是我的座右铭,奋进是为了求索,愿你们年轻人奋进不息,求索不止!”每当我看到老人的题词,缕缕情思油然而生,这教诲时常萦绕在耳畔,教我写文,教我做人,受益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