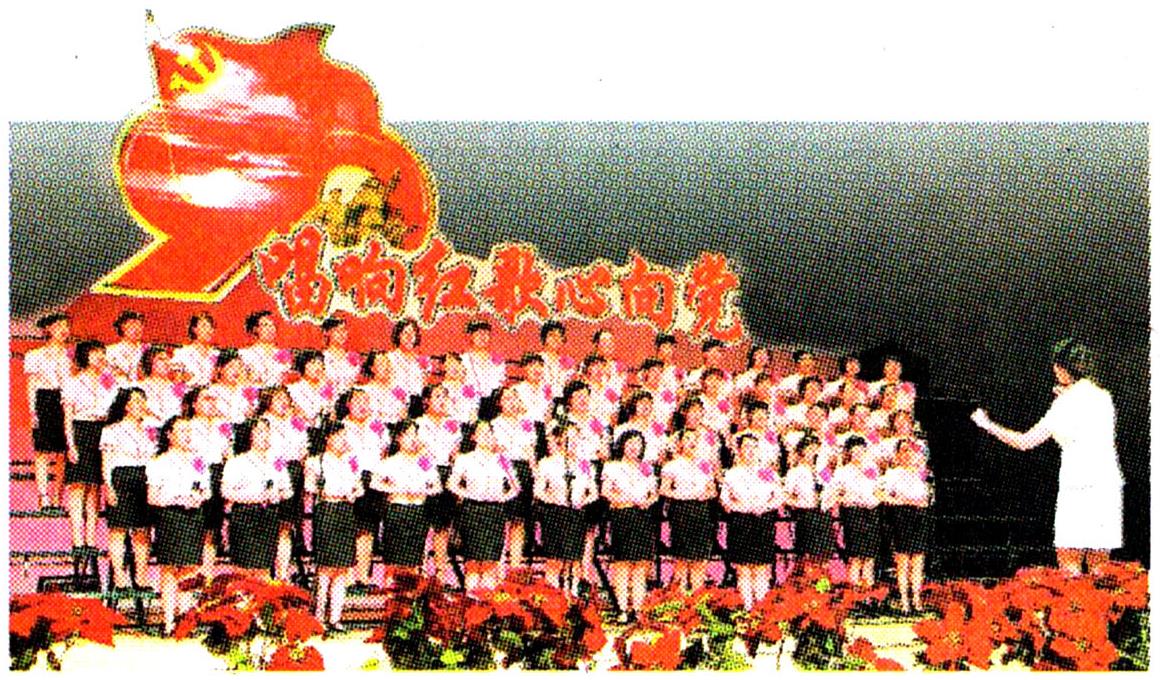文/王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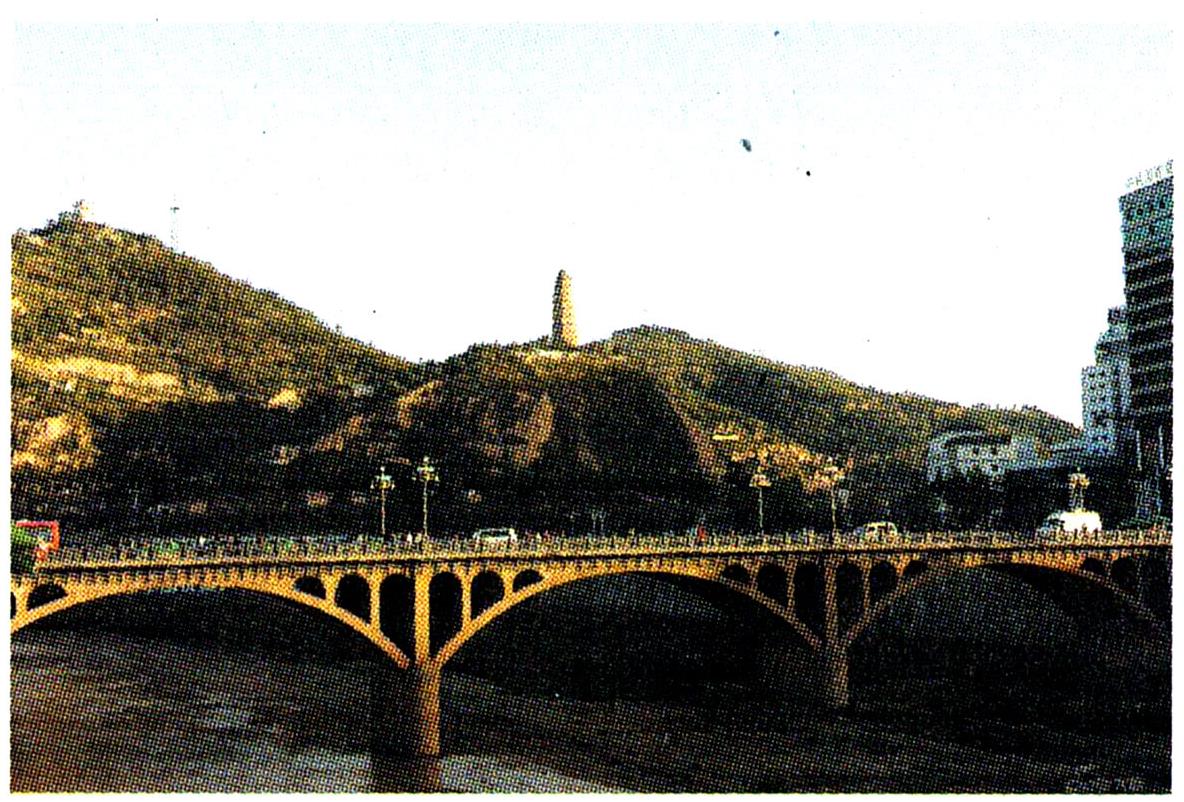
1948年月1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辖区陕西、宁夏、甘肃的23个县,在首府延安召开“陕甘宁边区妇代会”。没几天,接到上级通知,我做为教员代表,被推荐参加此次会议,同路结伴去的还有同乡女干部代表张铁莲、女农民代表张贵贤、女学生代表王凤琴。延安像革命摇篮,寄托了多少年轻志士报效祖国的梦想。我激动得彻夜难眠,背着母亲,悄悄离开了家乡陕西韩城。
从韩城到延安,要翻山越岭,淌河跨涧。遥遥三、四百公里的路程,徒步行走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那时,没有交通工具,领导怕耽误时间,给我们派了两头毛驴,还雇了两个赶脚的中年男人,兼做保镖,让用最快的速度抵达延安。
腊月的天气,寒风凛冽。望着远处满山遍野被风吹拂的枯枝、干草,还有田野里残留的包谷,让第一次出门的我格外新鲜,情不自禁地边走边唱。路途上,碰到邻乡追赶上来的姑娘们,她们也是奉命去延安参加会议的。共同的担当,增添了几分亲情。有个穿蓝色制服的女干部扯着清脆优美的嗓音,教我们唱《蓝花花》、《揽工人儿很难》、《兄妹开荒》、《王桂花纺线》等歌儿。年轻人记忆力好,很快我就学得有模有样。至今想起歌词还十分清晰,朗朗上口。
我们四个女同志分为二组,骑驴或步行,20里路调换一次。黑色的毛驴身上搭着一个木框架子,两边驮着我们去延安用的铺盖卷,暴露的驴背刚好是人坐的地方。我壮着胆子骑了上去,感到平稳、舒服又省力。
80里路为一站,到站是兵站或骡马店。兵站是专设的接待站,有热腾腾的饭菜和休息的宿舍。骡马店很简陋,睡的全是大通铺。每天天不亮就要赶路,中途没在歇息的地方。碰到下雪天,手脚冻得裂开了口子。饿了只能吃随身带的干粮,就几把路边的白雪。我带了两双布棉鞋,每到一站守着火盆旁,替换下白天在泥泞雪水里浸泡的那双棉鞋,烤干了第二天备用。
走在荒凉的羊肠小道上,不时传来一阵阵野狼的哀嚎,还有暗藏的国民党残渣余孽与当地特务分子几股邪恶势力的干扰捣乱,自然与人为的种种不利因素,还是让我们小心翼翼。赶脚的乡党不停地安慰我们,拿着棍棒,为我们驱赶恐惧。
直到第六天,我们到达了黄龙专区(今洛川县)。组织安排,要在这里集中一下,等候洛川、宜川还有其他远道来的小队人马。在办公驻地,我们帮着印刷文件,作登记,整理成册。
经过九天的行程,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一走进延安,在敲锣打鼓声中,在“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标语的渲染下,感到一股革命浪潮扑来。来接应的女干部身着蓝色制服,齐耳短发,干练利索。热情谦和地拉着我们的手,不停地询问路途的辛苦。等安排停当,就与我们拉家常,消除彼此间的陌生。晚上睡觉,女干部轮流查铺,生怕着凉,替我们把被子拽好。
每天开会,领导都要讲解妇女翻身解放,不再受压迫的道理。循序渐进地教育和引导,让我逐渐明白,旧中国妇女地位低下,愚昧无知,是遭受封建制度奴役所至,贫穷生活让她们受尽欺凌,没有上学受教育的权力。现在面临全中国解放前夜,就要靠我们与广大农村妇女一道,勇敢地铲除落后根源,与腐朽势力作斗争。
到了晚上,老区演出团表演扭秧歌、交际舞,还有编排的“穷人恨”等节目。用艺术的形式展示了万恶的旧社会带给穷苦大众的悲惨生活和翻身求解放的喜悦及男女平等、摆脱束缚枷锁的新妇女形象。
“妇代会”开了半个月,有三、四百人参加。习仲勋书记作了报告,贺龙司令员与全体代表一同进餐,用装满酒的大茶壶给大家敬酒。会议间隙,我们还参观了毛主席等中央首长的办公场所和杨家岭、枣园、党校、幼儿园旧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了中国的解放事业呕心沥血、历经险阻、艰苦奋斗的忘我精神,深深打动着我。
共同的信念、追求,铸就了这段弥足珍贵的时光,让我增添了不怕危险和困难的才干。立下决心,回去要大干一场,不辜负党的培养,为妇女解放事业做贡献。
不久,我调离学校,到乡、区妇联工作。我响应党的号召,投身到土地改革运动中,支援前线做军鞋、宣传婚姻法、组织识字班、交购统销粮、排练文艺节目。由于我思想进步,工作表现出色,先后担任了韩城县、朝邑县、大荔县妇联主任。1954年,我从县上调到渭南地区任妇联主任。
我今年已是85岁的老人,1986年从工作岗位上离职休养。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每当回想起去延安的那一幕,心里仍然很激动。在建党90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愿用这段难忘的回忆,真诚地祝愿党永远朝气蓬勃,永远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