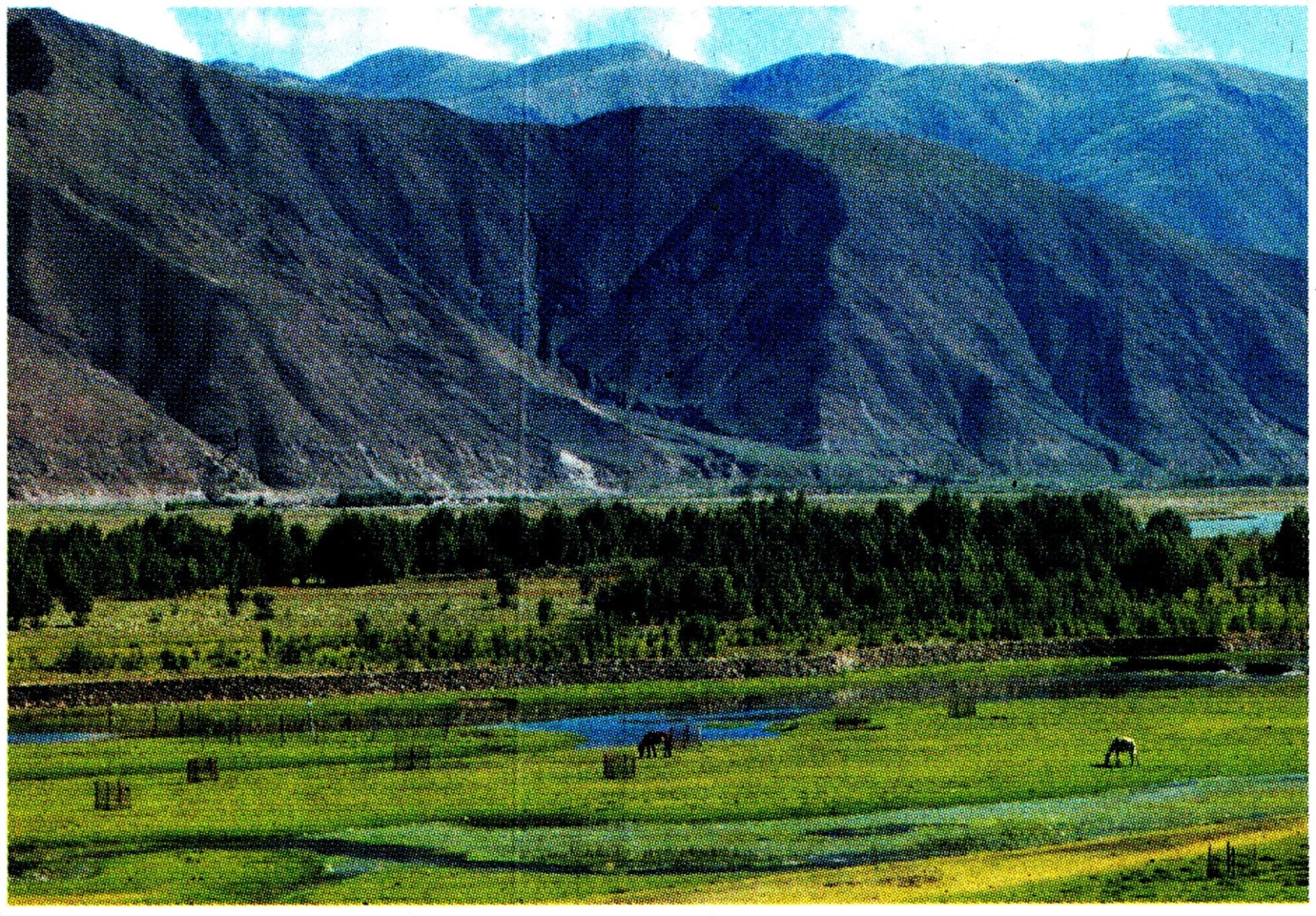文/赵明华

从我出生时起,在我家门前,就有一棵远近闻名的大槐树,树干呈深褐色,粗壮挺拔,三四个小孩也抱不住。高大的树冠犹如一把张开的巨伞,遮天蔽日,枝繁叶茂。关于它的年龄一直是个解不开的谜团,据祖辈们回忆,好像是老祖先民国时期留下的。其古朴苍老的身躯因饱受岁月和自然灾害的磨难早已布满累累伤痕,也留下了历史的沧桑和写照。
每年五月初,枝头上就结满了槐花,抬头望去,一簇簇盛开的槐花,掩映在青翠欲滴的绿叶丛中,宛如阳春白雪,晶莹剔透;一阵微风吹过枝头,一串串槐花旋即随风起舞,宛如少女千姿百态的舞姿,婷婷玉立,妖娆迷人,甚至连空气中也散发出沁人心脾的幽香,令人心旷神怡。特别是一场春雨过后,绿叶泛着露珠,洁白的花蕊更是冰清玉洁,分外惹人喜爱,常常引来街坊四邻的孩子们,在大树下开心地嬉戏、玩耍。
七十年代初,我刚刚上小学,记得那时的生活虽然比较艰辛,但只要一放学,我们就身不由己地跑到树下的空地上玩骑驴、赢三角、包子、滚铁环等,甚至为了小小的输赢常常争得面红耳赤。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炎热的盛夏,我们或在大树下避雨,或在大树上抓麻雀、知了,夜晚则围在树下抓蛐蛐或者避暑乘凉,大槐树不仅带给我们无穷的快乐,更为我们枯燥、单调的童年生活平添了许许多多令人回味无穷的乐趣。
每当盛夏的夜幕降临,由于屋子里闷热,加之各家的条件都不太好,更谈不上用电风扇了。那时我和邻居的几个小伙伴经常相约,各自带凉席铺在大槐树下乘凉,大人们则聚在一起拉家常。由于大树底下既凉快地方又宽敞,我们小孩子经常在几个凉席间跑来跑去,甚至打打闹闹直到深更半夜,一点不知疲倦,直到第二天太阳晒到屁股上了还昏睡不醒,常常惹得大人生气,甚至拧耳朵才懒洋洋起来。
记得七十年代,当时由于国家实行粮食定量,粗粮多细粮少,甚至连肉也吃不起,加之孩子又多,各家的粮食基本上都不够吃,自然蒸槐花就成了各家饭桌上都少不了的补充食品,也是困难条件下填饱肚子的一种补救的土办法。每当槐花盛开的季节,家家户户几乎都想尽一切办法弄槐花蒸疙瘩。我从小就喜好爬树,等到有一天槐花刚刚张开初放的花蕾,我就迫不及待地爬上了大树,一手抱住树干,一手拿着自制的竹竿树钩,看准一簇簇茂密的槐花枝叶,用树钩慢慢地旋转枝叶,只听“咔”的一声,树枝带着槐花缓缓飘落到地面,等到树上盛开的槐花钩得差不多了,我就从树上滑下,脸上带着胜利的喜悦,兴冲冲跑进厨房找一个搪瓷盆,细心地把槐花和花蕾从花茎上捋下来,经常是边吃边捋。有时一不小心就会被树枝上的刺划破手指,那时一点也不感到疼。等采下来的槐花装满一大盆,我就不管了,接下来就由妈妈或奶奶洗净控干水分,然后倒在厨房的案板上,拌上面粉,再撒上盐和五香粉,用双手反复揉搓和匀,才放进笼屉里蒸。等到槐花的芳香随着一股股热气飘散在厨房上空,就说明蒸熟了,然后下笼把槐花疙瘩倒在案板上摊开。有时不等大人们忙完,我们姊妹几个就争先恐后地各自拿起搪瓷碗,盛上一碗狼吞虎咽地下了肚。有时如果条件好,泼上菜油,拌上炒韭菜,再调上油泼辣子,吃起来那就更加美味可口了……
由于我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常常令周围的邻居和孩子们非常羡慕,有时我奶奶也毫不吝啬地会把蒸好的槐花疙瘩送给左邻右舍分享。
大槐树承载了我家祖祖辈辈几代人的期望和寄托,在我的眼里,它就是这个家庭的一员,和我们风雨相伴,相依为命,它的命运时刻和我们紧紧相连。在往后的日子里,它没有被风雨雷电击倒,也没有被病虫折磨而枯萎,而是极不情愿地把自己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了这个家。
七十年代末,由于家庭负担日渐沉重,为了让我们吃饱穿暖,奶奶就没有和任何人商量,一狠心悄悄把大槐树以一百多元的价格卖给了街道的生产队,槐树被生产队用来做成了马车的车辕。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童年的往事早已成为过去,一去不再返。但是我始终难忘那个大院,难忘那个曾经带给我和伙伴们无数快乐童年的大槐树。每当槐花盛开的季节,我在梦里更想念它,更难忘槐花的清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