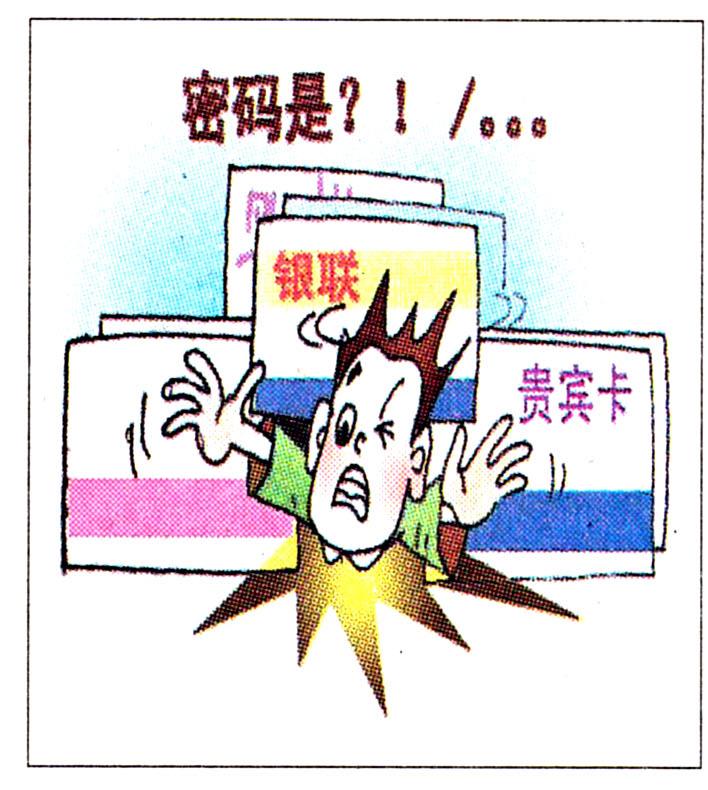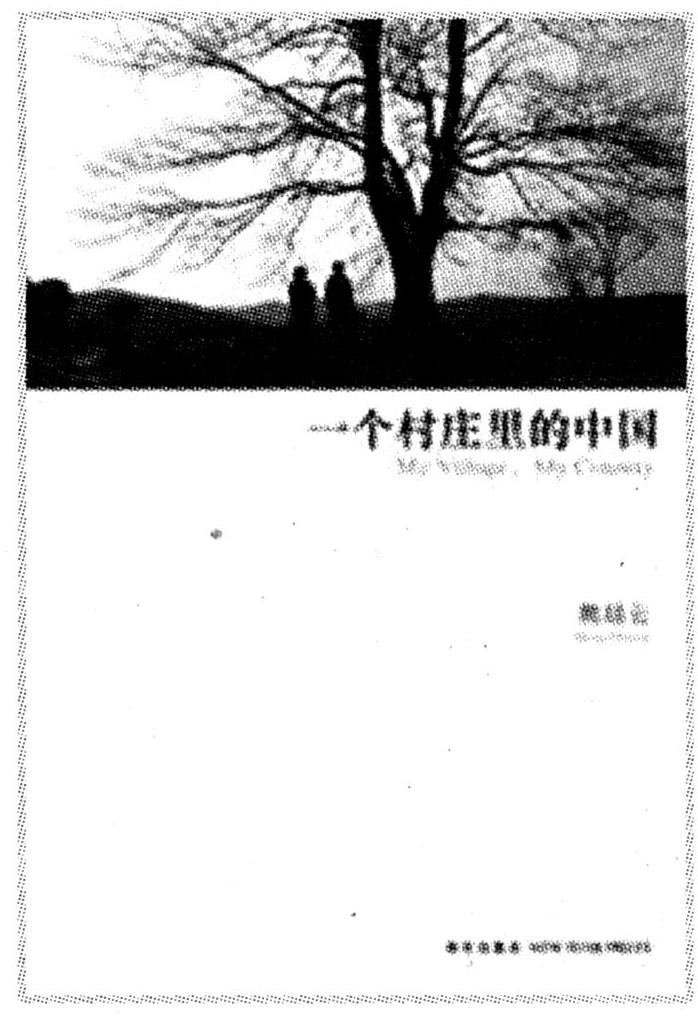
传统乡村、农业、农民陷入衰败,似乎是个难以阻遏的潮流。法国农村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就曾断言,法国农民走向终结,由千千万万户小农组成的传统农业文明被现代化大规模工商业文明所取代。当代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典型国家美国,农村、农业、农民也有了根本性的内在转变,尽管农民仍然在美国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这个群体本质上已经变成了依赖工业机器生产和都市生活方式的农场主,及其雇工,不再具有美国开国前后“乡民”的文化特质。
基于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在全球推进的时空差异,不少后发国家(二战后独立的新兴民族国家)曾相对完好的保留了传统农业、农民,乡村形态似乎仍停留在一种让欧美知识分子赞叹欢欣的田园牧歌式梦幻状态。但这仅仅也是暂时的,这些国家同样或主动或被动卷入全球化浪潮,传统农业和乡村不能不为之改变,否则不能更好地为更高层次的工业、服务业、更大规模的城市服务;土地资源也不能整合集中起来为资本服务,创造出更大产值。农民成为这个潮流下,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劳动力廉价来源,并被迫承受大量的转型成本。
熊培云先生的新著《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就以其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的故乡村庄为起点,从各个侧面梳理了中国乡村这一百年来经历的多次不成功转型,以及由此带来的乡村衰败。这本书的后记归纳了书中各章就中国乡村一百年来经历的现代化、革命化、城市化三大转型浪潮,指出自此导致中国的文明重心及人力、物力资源开始由乡村转向城市,成为农村萧条之始。
熊培云先生指出,中国的乡村衰败,既有时代潮流推动的自然发生,也包括革命暴力与建设暴力,建设暴力更以近年来激越的城市化而掀起高潮,形成了当前农村“乡村精英的流逝,政治上的不设防,法律上的缺位,自治精神的萎靡,城乡发展的严重失衡”局面。简言之,乡村衰败的程度,已经让人担忧中国的发展,成为了卡尔维诺笔下的“一个装载欲望与恐惧的容器,。一段只有去路没有归途的旅程。”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是一本闪耀着对乡村、农民深切关怀人文主义精神的佳作。这本书的源头,或者说生发观察与思考的引子,是在熊培云先生个人的故乡村庄,但记述的问题却带有普遍性,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乡村百年来遭遇多轮外力驱动转型的负效应总结。书中提出的思考,并非作者臆造,也非理论观点对历史和现实的简单投照,而是建立在作者对方方面面文献资料的收集分析基础上,以及坚实的实地访谈。熊培云先生在书的自序引述了农学家董时进1932年的一段评论,可以作为一种印证、一种标准:
“我素来认为要知道乡村的秘密,和农民的隐情,惟有到乡下去居住,并且最好是到自己的本乡本土上居住。依着表格到乡下去从事调查,只能得到正式的答案。正式的答案,多半不是真确的答案。我因为要明了乡间的情形起见,早想回到我乡村老家去住些日子——不是去做乡村调查,只是去居住,希望籍着居住,自然而然地认识乡下。”
(郑渝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