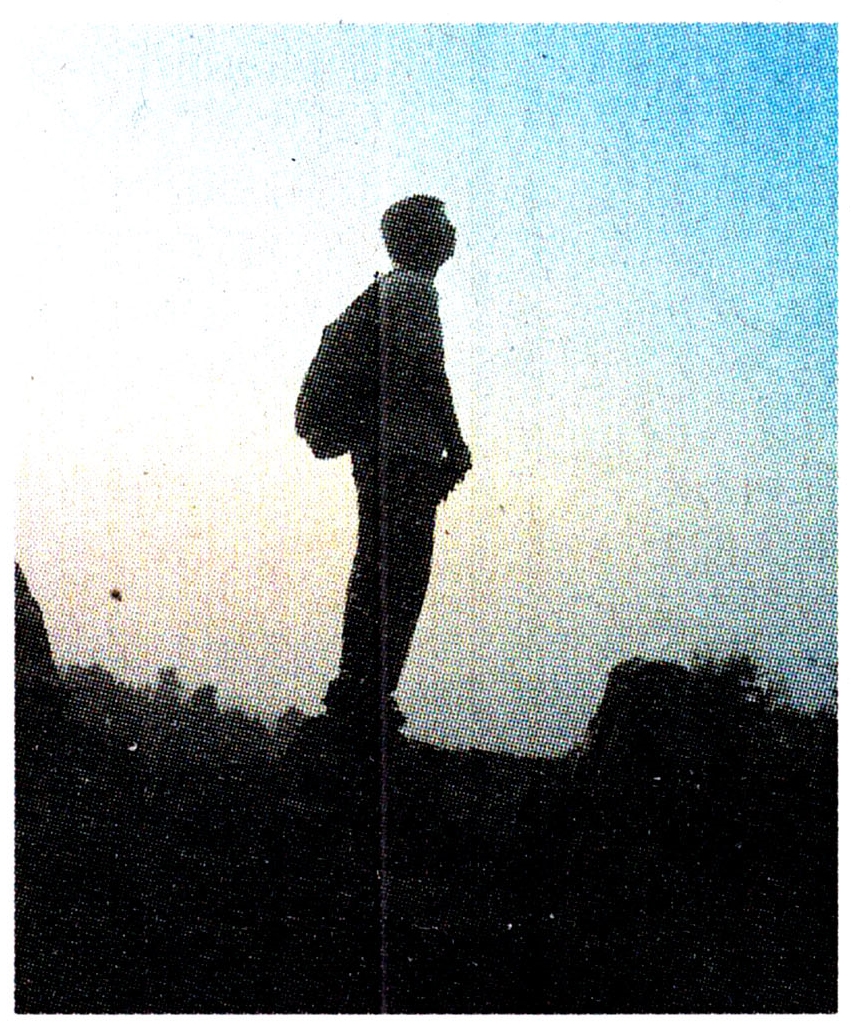文/秦延安
不知是黄土高原的屏障阻挡了瑞雪的脚步,还是它没有搭上呼啸的西北风列车。在深冬的那个季节,西安仍然是隔三差五地飘着冷冷的细雨,让人不由地怀念曾经雪满大地的日子。
雨让古城早早地走进了夜幕。在出门之时,我又看到了守在门前丁字路口的熟悉身影。披了一件雨衣,依旧偎在用汽油桶做成的炉子前。那炉子不仅烤着喷香的红薯,而且还散发着浓浓的暖意。让守卫在它旁边的人可以在凄冷的寒夜里得到一丝温暖。从这个夏日开始,她几乎每天雷打不动地守在那里,无论刮风下雨,无论天寒地冻。不知是被炉火熏烤的,还是被日月摧残的,乱蓬蓬的短发下是一张乌黑的面孔。那一双无神的眼睛,总是在张望着南来北往的客,期待着一个个顾主的到来。我不知道她家是哪里的,也不知道她住在哪里,但从她那口音,我知道她不是这个城市里的。为了生计,她来到了这个色彩斑斓的城市,在这里追寻着她自己的梦。也许她的家远在千里之外,那里有她牵肠挂肚的至亲爱人,或许她的孩子此时正在灯下做着作业想着妈妈,或许正在独自烧火做饭。为了孩子,为了生计,她在这个城市的一角,卖着烤红薯,虽然利润微薄,虽然顾客时多时少,但她在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着她的未来。
和她一样,为了生活,许多人都在忍受着寂寞与思念。在去陕南途中服务区小憩时,一名环卫工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一位穿着橙色环卫服的40岁左右的女人,手中拿着一个装有热水的瓶子,在手里倒来扔去,不是那水瓶热得烫手,而是为了驱寒。那另一只手上拿的手机,放着欢快的哥想妹的情歌,那歌声不知是特意选取的,还是无意中下载上的,但那歌声又似乎就是这些女人的影子。而随着那调子,女人晃动着步子踩着调。那一脸布满岁月沧桑的面孔,那一双在细雨中穿望的眼神,让人对这悠扬的歌曲产生了无尽的遐想。四周望去,秦岭深山看不到人家,不知这些环卫工家就在附近,还是远在千里。但她们依然有她们的乐趣,在劳动之后,以自己的方式追寻着自己的乐趣。虽然她们已不是追潮的年纪,但她们依然不落伍。
在临近年末的最后的日子,我又踏上去西府的路程,去送别一位把生命遗落在治水工作中的“关中楞娃”。一个8岁丧父、身为长子的农家孩子,和身体残疾的母亲相依为命。十年寒窗苦读,终于走出农家小院,投身水利建设。扎根基层27年,与爱人一直两地分居。从一名普通的水利职工干到县水利局总工、纪委书记、治渭办常务副主任,凭着业务精、能力强、不服输的陕西楞娃劲,硬是把别人躲着走的事挑了过来,把别人干不成的事千成了。四年前痛失爱弟,苦苦支撑着一大家子人的顶梁柱,照看着弟弟留下的一双儿女。忙,让他几过家门而不入。强,作为局里五名领导唯一科班出身的他,曾是局总工,为全县水利事业规划了发展蓝图,解决了一道又一道的建设难题,手把手地培养起了一批又一批水利人才。他将他的爱和恨都洒在了生他养他的土地上,为了工作,他忘记了劳累,没有了白天和黑夜,更没有了节假日。一个平凡的水利人,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用自己的心血和智慧真实地践行着自己的无悔选择,在生命的履历上描绘了大写的人生。
沧海桑田,岁月匆促,在时光的大海里,一切的往事都如过眼灰尘,转眼即灭。在回望一年的匆匆脚步,在细捋一年繁杂的事务时,我才发现,人生的多少灿烂就在自己的身旁。卖红薯的异乡客、秦岭腹地的环卫工、累倒在工作一线上的水利人,他们对人生的质朴追求、他们对生命的真诚注解,如一股巨大的清流,穿过了这个寒冷的冬日,让我被尘垢蒙蔽的浮躁心灵,如沐浴阳光的向日葵似的,感受到了春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