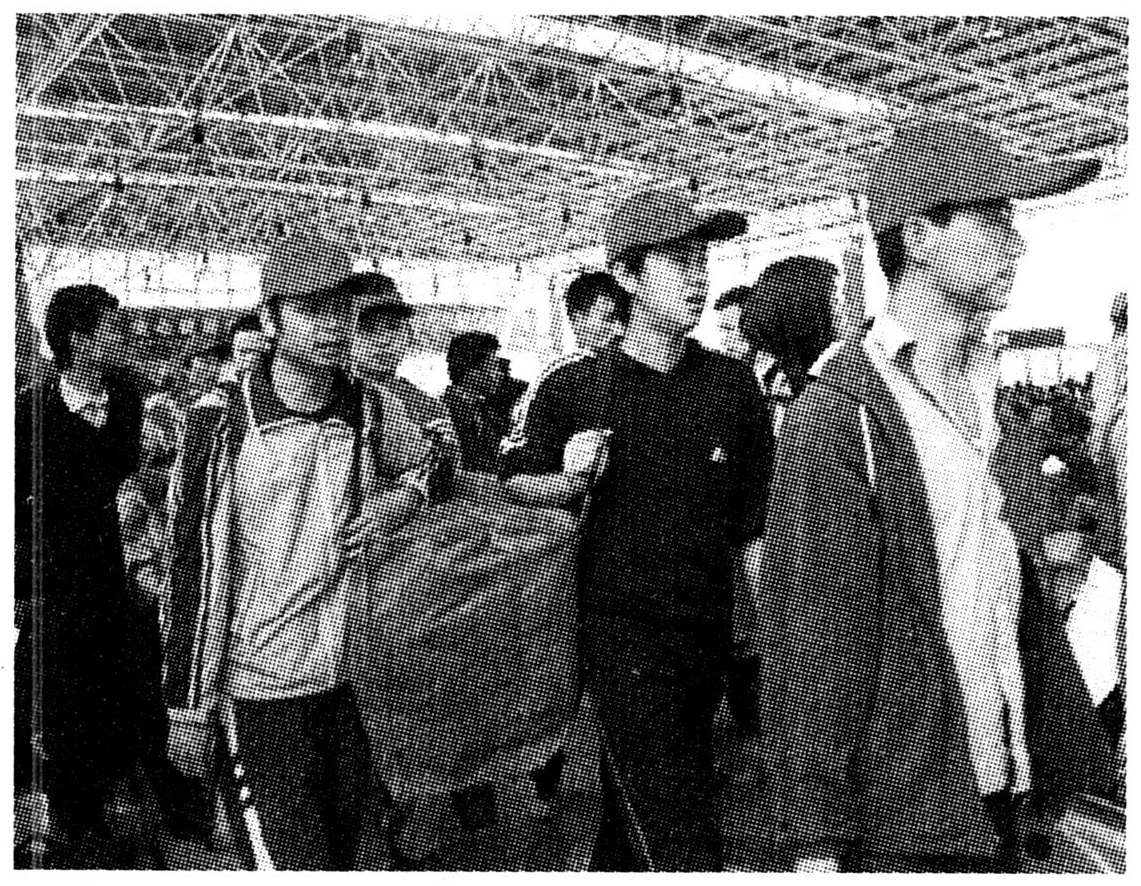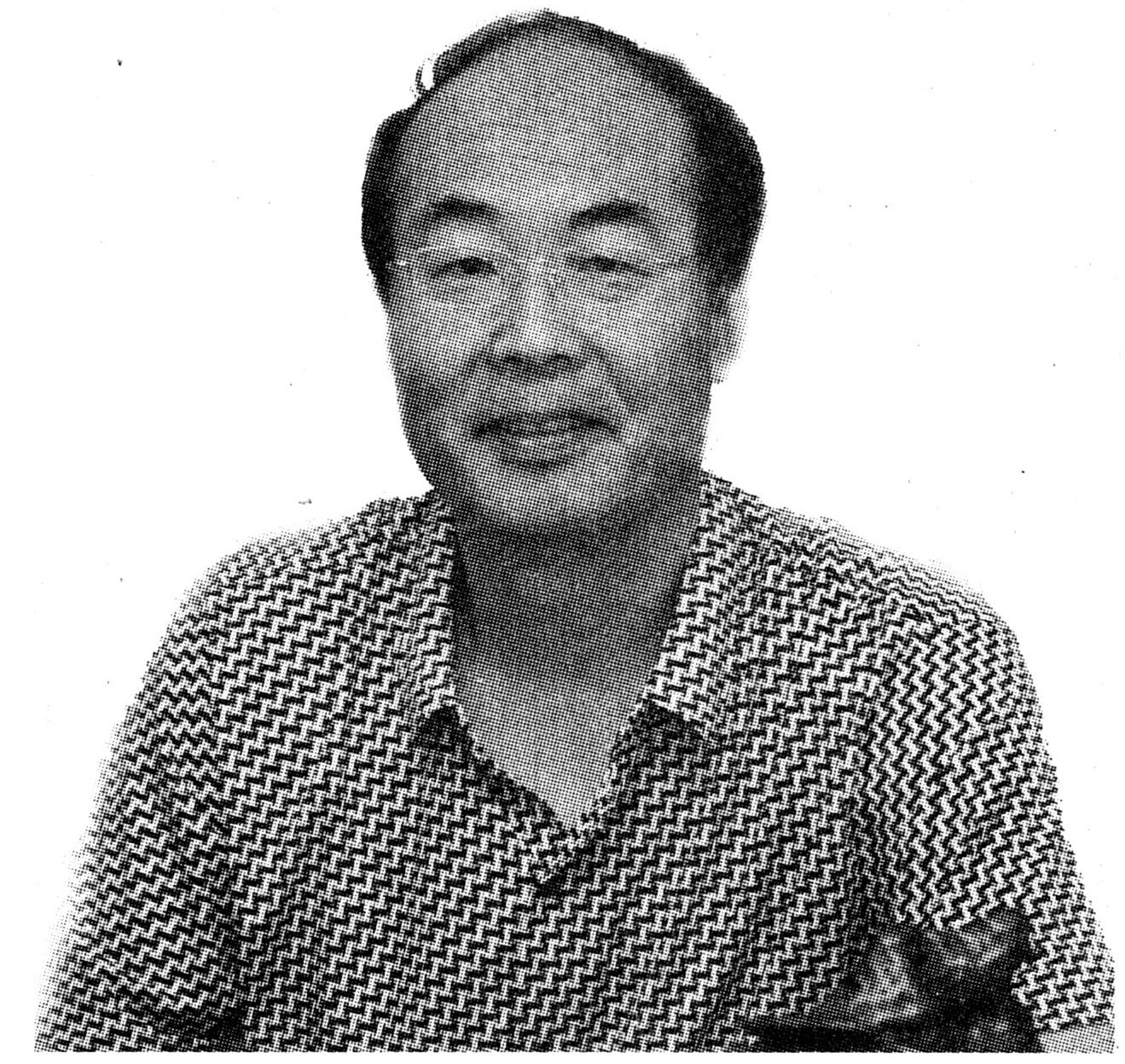工作不到一年的银行职员赵子宣端午节前没有领到发给正式合同工的800元过节费。她告诉记者,单位对劳务派遣工存在严重歧视,同样干营销,收入只有正式工的一半。
同工不同酬在两种用人方式并存的单位广泛存在。在全总对省总工会的调查发现,相同或相似的工作岗位和工作业绩,劳务派遣工与正式工收入差距少则30%,多则四五倍。
“同工同酬是劳动合同法的重要原则,对劳动者来说是一项基本权利,劳务派遣工没有理由‘低人一等’。”赵子宣告诉记者,同工不同酬,根本原因在于用人单位通过这种方法最大限度压低用工成本。虽然此次《劳动合同法》修改案草案增加了劳务派遣单位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的劳动合同以及与用工单位订立的劳务派遣协议,载明或者约定的向被派遣劳动者支付的劳动报酬应当符合同工同酬的规定,但是劳动者的收入还包括住房公积金、企业年金以及其他福利待遇,“我建议草案应明确规定被派遣者享有与用工单位同工龄、同工种的劳动合同制员工‘同工同酬同待遇’的权利。”
此外,对于此次修正案草案中对“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三类岗位使用范围的规定,赵子宣也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此次修法对临时性、替代性都有了较为详细的界定,但是为什么在辅助性上就说的很模糊呢?究竟要在辅助性岗位上干多少年,才能转正呢?”赵子宣说自己2009年大学毕业后,通过层层考试、面试后才开始在这家银行上班,如今三年过去了,不管工作多么卖力,和合同制的同事相比,她的工资永远没有办法超过他们。
“如果对‘辅助性’没有一个时间限制,那企业将很可能在所谓的辅助性岗位上大量、长期使用劳务派派遣工,这是立法的本意吗?我建议将‘辅助性’岗位设立一个时间限制,两年也好,三年也罢,让我们这些派遣工看见点希望总是好的啊!” 本报记者 鄢山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