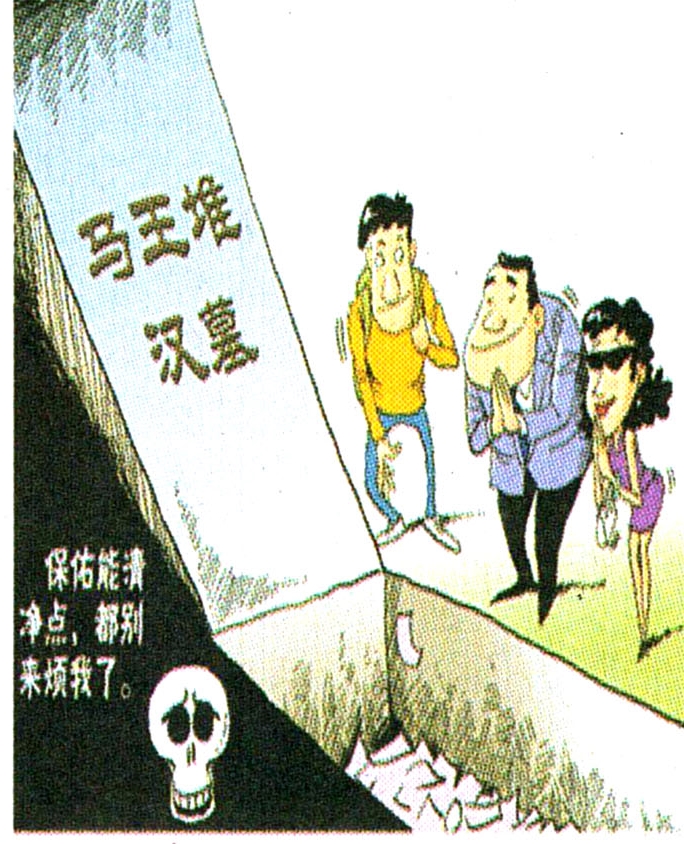一个身处底层的农妇李雪莲欲生二胎,与丈夫假离婚,不料弄假成真,丈夫另结新欢。农妇想要出这口气,开始上访之路,从乡镇到县、市,最后闹到北京人大会上,一直闹了二十年。她在试图改变自己命运的过程中,改变了一大批官员的命运。最后,尘埃落定,二十年上访成了“笑话和羞”——就像这篇小说的结构,两篇长长的序言之后,仅占全文不到百分之五的正文标题:玩呢。
这种结构有什么寓意?刘震云解释说:小说探讨的是生活的逻辑,一件事是怎样变成八件事的,要说清楚一个道理,就要把其余很多事说明白。
这种解释差强人意;当然,它不影响你的阅读,它只是改变了序言的本意——所谓序言,是引子,是龙套,是说明书。而这个序言,它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它甚至决定了标题。
整个小说读下来,从各级政府、涉事官员的角度讲,主人公更像是清末轰动京城的“小白菜”;从李雪莲本人讲,她是“窦娥”;标题所提到的“潘金莲”,更像是一个幌子,阅读的过程中,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不能说标题哗众取宠,但总是与内容牵强,有生拉硬套之感。
作者估计也认识到这个问题,关于李雪莲是“潘金莲”的说法,特意有交代,但一来显得突兀,二来属细枝末节,与整个小说的立意、主题关联不大。
我注意到,刘震云在采访中,曾经提到过这篇小说的另一个标题《一万句顶一句》。他的《一句顶一万句》获得第八届茅奖,知名度已经有了,考虑市场的话,这个标题更好。
我倒以为,真正从小说的内容来讲,最贴切的标题是:一万句不顶一句。
你看啊,因为想要得到前夫的一句肯定,李雪莲折腾了二十年,对人说了无数的话,但没有人相信她,已经痴狂到和牛对话的程度;不是一万句不顶一句嘛!不是一出荒诞的正剧吗?
说其“荒诞”,是因为本来只是一对农村夫妇的家事,一步一步,芝麻变成了西瓜,蚂蚁变成了大象,演绎成惊动国家领导人的大事。荒诞的人物,荒诞的情节,荒诞的境遇,随着故事不断向前推进,你觉着怎么会是这样啊?怎么会成这样啊?
说其“正剧”,是因为小说正面描写了我国法制社会建设进程中的一个现实困境:上访,这个被国家法律明确的公民诉求渠道和政治表达形式,被各级政府和官员导演成为当下中国最大的一幕闹剧和丑剧。作品通过冷静的文字,描写了李雪莲是如何成为地方官员的“心病”,上访又是如何成为一桩“严肃的笑话”。
刘震云将其认为是一部“底线之作”,一部探寻喜剧生活中幽默和荒诞底线的作品。他在采访中说:真正的逻辑还是人的逻辑,人的荒诞才会导致社会的荒诞、生活的荒诞。窃以为恰恰相反,正因为社会的荒诞才导致了生活的荒诞,进而是人的荒诞。
刘震云先生不可能认识不到这一点。这也就不难理解他塑造了李雪莲,这个在常人看来思维怪异、难以沟通的农妇形象;安排了一个××省××县××乡的模糊背景;罗列了上到国家领导人、下到基层民警等一系列性格各异的公务员——这样的描写,难道是为了说明“人的荒诞”吗?
同样是农村妇女的形象,同样是告状这个题材,我无法不把李雪莲与《秋菊打官司》的秋菊做个对比。相比之下,我更喜欢秋菊——这个性格执拗、心地善良、坚持正义的西北妇女形象。至于李雪莲,喜不喜欢不要紧,问题是,在现实生活中,类似李雪莲这样的人物绝非另类,类似李雪莲这样的故事绝非个案。
在当代文坛大家中,像刘震云先生这样,着眼于现实生活,着眼于草根百姓,着眼于民生艰难的作家不多。虽然从文学性讲,《我不是潘金莲》算不得刘震云的最好作品——我甚至认为他没有用力写:主人公性格几近偏执,让人难以理解;有的情节设计不合理,感觉刻意为之;前半部过分讲究语言的简洁洗练,导致后半部大段大段地论述以自圆其说。而从现实意义讲,这是一部“有良心”的作品:它直面当代中国,用形形色色的人物、热热闹闹的情节,演出了一出荒诞的正剧。
□刘紫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