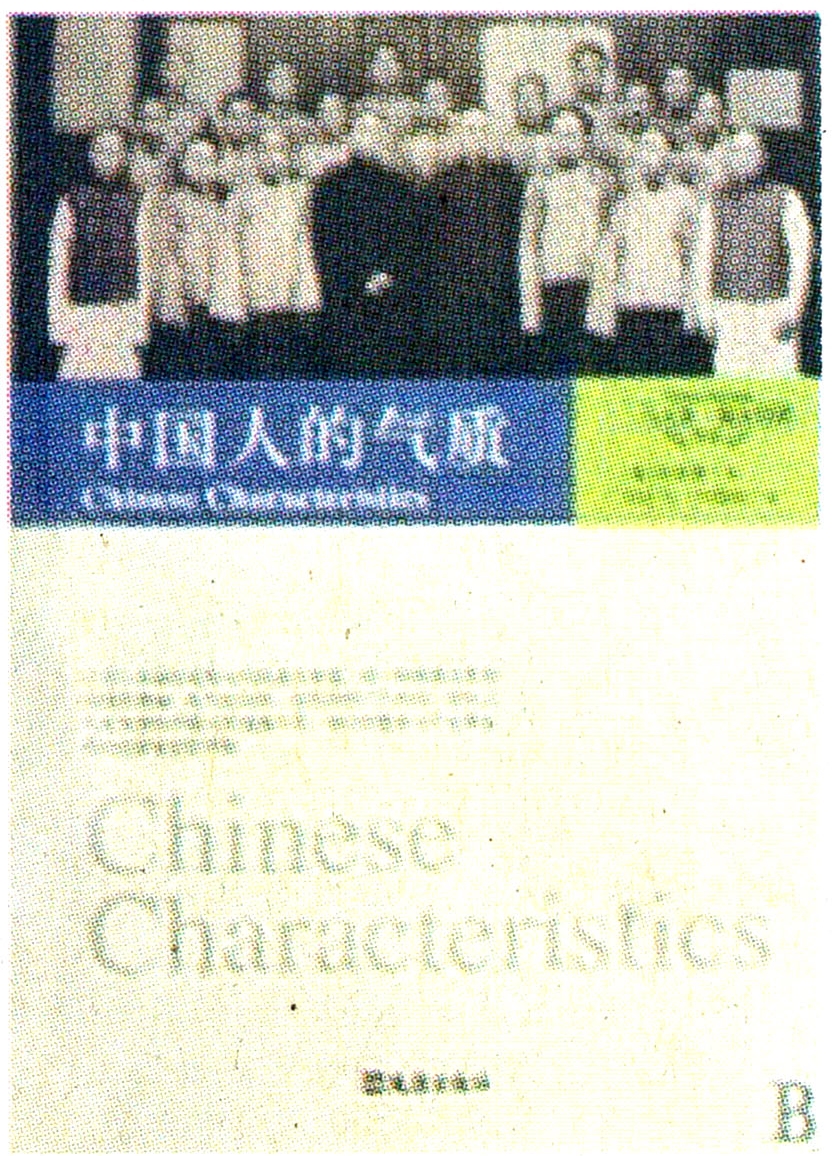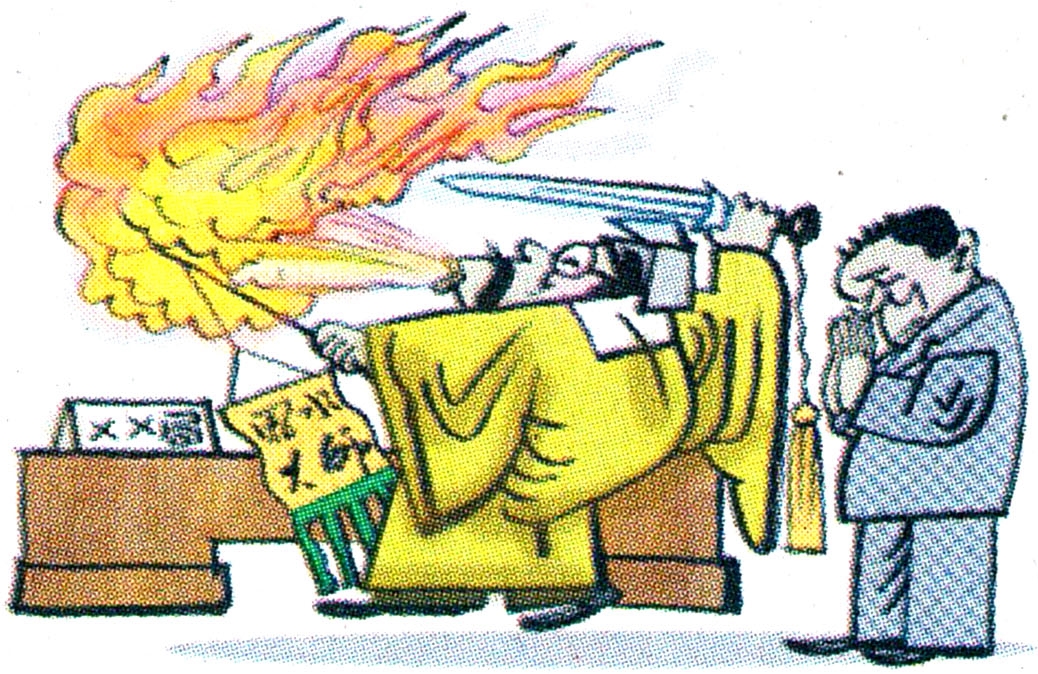记得很早以前看过这样一个笑话:钱包丢了,各国人会是什么反应。美国人会立马打电话报警找律师,德国人会凭记忆绘制方格地图确定钱包的失踪范围,日本人会闭门思过,中国人呢,狠狠跺一脚,说:“呸!谁捡到了谁买药吃!”自然,这是中国人编出来的笑话。还有关于“国民性”的外国笑话,比如:在酒吧里讲一个黄段子,捷克人立马哈哈大笑,德国人过五分钟才笑,荷兰人过半个钟头才笑。后来接触西方国家文化,发现类似的段子也是举不胜举,墨西哥人喜欢编嘲笑本国人的笑话,西班牙各地区的人民喜欢编段子互相攻击,似乎唯有阿根廷人不喜欢笑话自己,倒是其他拉美国家的人民编出了成千上万个笑话阿根廷人的段子,乐此不疲。这些笑话虽不能作为学术研究的资料,却仍不失为某一个人群的漫画式写照,其中蕴含着某些东西,用西班牙九八代思想家的话语来说,代表了“民族灵魂的精髓”。
“民族灵魂”真的存在吗?所谓“国民性”,是真实存在的还是主观臆造的?如果我们承认,每一个民族都拥有独特的精神,导引着这个民族的一切行动,引领他们创造出自己的文化,我们高中时代的思想政治老师就会跳出来批判,说这是典型的唯心主义观点,归根结底还是物质在先、经济基础才能决定上层建筑嘛!可是,如果说民族灵魂、国民精神并不存在,或者说生产力水平决定民族气质,那么该如何解释那些读来真觉贴切刻薄的讽刺各国人特性的笑话呢?如何理解那些在美国居住多年,过着与一般美国家庭无异的生活,却在文化上、气质上并未远离故土的墨西哥人?如何解释,比如说,读过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一书之后,许多中国人会觉得,我们与一百多年前的我们竟然如此相似!为什么经历了物质生活上如此巨大的改变之后,我们还是……这个样子?
如果我们能平心静气地看看作者明恩溥(1845-1932)列举出的中国人的种种特质,我们不能不承认,他揭示了我们自己并不容易发现的一些方面。比如我们的勤劳,我们的孝顺,我们的“缺乏公共精神”,我们融儒释道于一身于是成了“彻头彻尾的不可知论者和无神论者”,我们关于责任的理论和实践“给社会的每个成员都戴上了难以挣脱的铁镣”……作者对中国人既有褒,亦有贬,不似辜鸿铭那样一味地将中国文化理想化,也不似鲁迅那样致力于深挖这个民族的丑陋之处。他常常引述自己生活中遇到的实例,笔调不乏幽默,却始终是审慎的。
比如“漠视精确”。现代社会相对于封建社会的一个特征,就是对数量的重视。土地和时间都得到了更为精确的测量,整个世界都被纳入有比例有系统的规划图中。无疑,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人大多还生活在漠视数量精确的时代。一个从工业化社会初抵农业化社会的“文明人”,自然要被这些“野蛮人”的马虎毛糙折磨得发疯:他不能明白,为什么这个帝国的一条重要干道从北到南全长一百八十三里,从南到北却变成了一百九十里;一个只知自己的属相、自称“七八十岁”的中国老人究竟是七十岁还是八十岁还是介于七十岁至八十岁的区间;为什么这个地方的“两”和那个地方的“两”不一样重,从而给诚实的人带来无尽烦恼……“中国人无法理解西方人为何对万事万物都如此力求精准,他们会认为这是一种病态的癖好。”作者这样论断道。今天的中国人已经晓得,如果不怀有这种“病态的癖好”,我们的生活就会陷入一团糟。往大处说,如果列车的运行不遵照严格的时间表,全国铁路网就会瘫痪;工程师算错一个小数点,火箭就上不了天。往小处说,购房拿房时如果不丈量一下实际户型面积,就有可能被开发商骗去一笔数目可观的血汗钱。
再比如“缺乏公共精神”。“一条道路或是其他什么东西是属于‘公众’的,这样的概念完全没有进入过中国人的大脑。‘江山’(也就是帝国)被认为是皇帝的财产,他在位一天就拥有一天,统治一天。”现代性打破了小农自封的樊篱,将一个个陌生人聚集在市民社会中,以公共精神取代神权统治,以法制体系取代宗亲、乡党关系。昔日的落后农业大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入城市化。随着公民概念日渐深入人心,我们正逐步意识到公共精神的重要性。谁也没有充足的理由否认,这个国家不是属于哪一个人或哪几个人、哪一个或哪几个利益集团的,而是属于你我他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人都有相应的权利,以及相应的义务。我们辛勤工作,我们爱我们共同的家园,我们按时缴纳物业费,如果物管做不到位,我们有表达抗议的权利。看看今天的这个国家,一方面有层出不穷的案例见诸媒体,让我们对同胞的自私和冷漠痛心疾首;另一方面,也有层出不穷的积极力量在推动公共精神的广为传播,有人教我们如何开会,有人给我们示范如何聪明地维权,有人致力于公民教育从娃娃抓起……在度过了GDP的迷狂之后,我们开始关注更深层次的东西。这是改革走向深度的必然。明恩溥在书的末尾似是忧心忡忡地感叹道:“这样的文化中没有任何改革属性。”他未尝预料到,今天的中国人在接受一些新事物时,快得令西方人也要吃惊的。
中国人的另一些特质,则恐怕是根深蒂固的,难以在现代性的扩张面前式微的。比如所谓“拐弯抹角的才能”。“用不着与中国人打太多的交道,一位外国人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来,即仅凭一个中国人所说的话,是不可能了解他的真正意图的。”“对于任何一位想与中国人成功相处的人来说,除了熟练地掌握中文之外,一种强大的推论能力也是很关键的。”不喜欢直白地表达自己的意图,倾向于用委婉的话语、暗示的方式传递信息,这仿佛是中国人与生俱来的习惯。在这种习惯的背后,有古老的哲学思想,有代代相传的教诲,有无数次与人相处的经验。尽管有种种不利之处,这种习惯并不妨碍我们接受现代文明的成果,也并不至于让我们陷入与西方人无法沟通的境地。中国人的含蓄,中国式的繁文缛节,也并非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起码不比早已步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日本人来得更为夸张。西方人在经历了不同信仰的冲突所导致的种种悲剧之后,回过头来看中国人,始觉这个民族的睿智之处。他们觉得,中国人似乎从来都不是哪种信念的忠实信徒,也因之不会拘泥于某一种理论、某一套教条,每前进一步都能随着形势的变化灵活地制定下一步的策略。中国人的思想方式非但不会有害于逻辑思维的形成,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有益于科学理性的思考。
在钓鱼岛危机掀起的怒火中,面对社会秩序、公民私人财产乃至人身安全公然遭到破坏和威胁的惨象,终于有国人喊出了“理性爱国”的口号,并得到大多数同胞的赞同。既然要理性地爱,那就要先理性地认识被爱的对象:我们,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我们痛恨“小日本”,到头来发现我们对“小日本”了解得如此之少;我们甚至对自己都缺乏足够的认识。可是,对本国国民性的深刻了解,有没有导致失望、沮丧乃至转投他籍的危险呢?我相信每一个理性的人都不会认为,改换民族属性就如同申领几份文件那般简单,而所有有胆有识的人都不会放弃让自己和自己身边的人过得更好的努力。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爱国主义?在古巴诗人何塞·马蒂看来,祖国就是人类,就是我们就近看到的、并在其中诞生的那部分人类。为你身边的陌生人多做点有益的事情,对于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来说,远比唱歌喊口号式的爱国主义来得更实在。 □张伟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