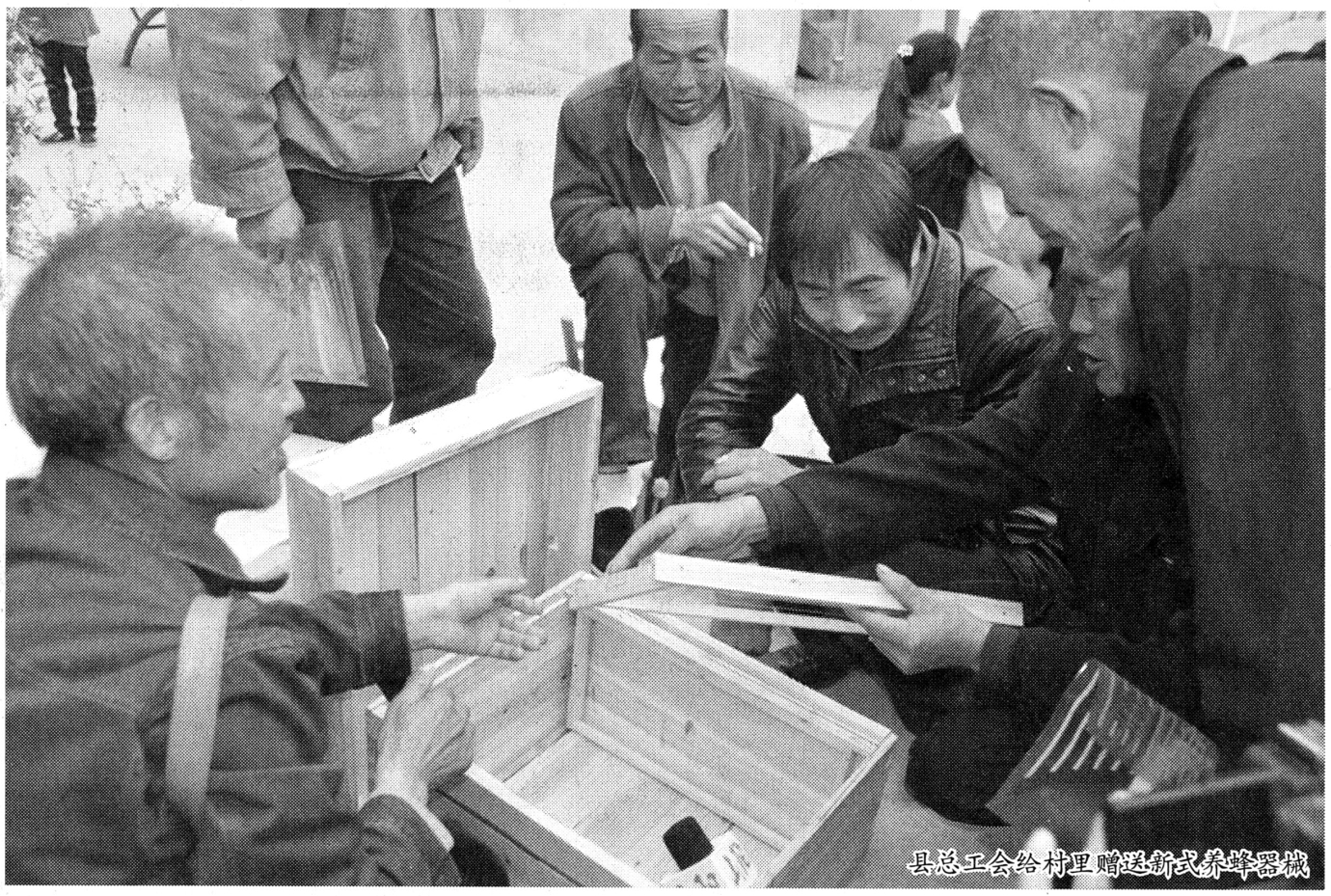两千多年前,孔子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自己的道德底线和做人处事的基本准则。在圣人看来,自己做的事情不一定非得要别人去做不可,但是若为“己所不欲”之事,则万不可强加于他人。十八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则提出“己所欲并欲人亦欲”是“我们应该为服从而服从的规律”。这种道德边界未必就是金科玉律、千古不变,但对于我们今天道德滑坡的严峻现实来说,在安全生产中引入这样的道德边界扎紧最基本的道德篱笆,依然十分必要。
现代意义的生产不论从动机、过程还是结果来看都必须要有安全的考量,都必须作出道德的评判。道德是人们社会性的基本要求,没有道德的维系,社会很难建立起正常的有效的低成本的秩序。在社会化的有组织的商品经济条件下,生产不再是个人孤立的行为,其安全的道德边界就显得十分重要。企业主不能无视员工的安全,企业也不能无视消费者的安全,不然,安全生产就会被极度扭曲。诸如大量煤炭企业(包括国有大型煤业集团)就会无视矿工的安全,为完成生产任务(或某项经济指标)而逼迫矿工下到瓦斯超标或有冒顶危险的工作面;类似富士康那种“血汗工厂”也会层出不穷;而像“三鹿”那种视消费者健康乃至生命为儿戏的无良企业,也会不断花样翻新后再次粉墨登场,继续祸害消费者,践踏市场法则,挑战人们的道德神经。
一切无视安全生产的行为都是利益驱使的结果,因此要保证安全生产就必须找到安全与利益的平衡点,既不能把企业只看做是赚钱的机器而无视任何社会责任,也不能“劫富济贫”,把企业当“唐僧肉”,用无休止的社会责任将其压垮。而是应当使企业的社会责任与利益诉求有机结合良性互动,要使企业在追求更大的盈利的同时更好地履行其社会责任。这样,用适度的社会责任将企业与社会紧紧连在一起。这一适度社会责任就是企业安全生产的道德边界。
安全生产的道德边界不是固定的,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会有很大不同。有时企业可能会更多地考虑到企业利益,比如企业本身真正(而非造假)处于亏损状态时,是无法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这时倒需要社会尤其是政府给予企业更多理解与帮助;而有时企业则可能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如战时经济,虽然它牺牲了太多的职工利益,但这毕竟都是特例。一般情况下,企业的任何生产活动都应被框定在安全生产的道德边界以内,应当努力道德地生产,生产“道德产品”。
具体来说,一个企业生产什么,怎样生产,按照什么标准去生产,都必须有道德的标准,生产者应该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考虑产品的安全问题。你生产的汽车自己都看不上、不放心、不愿坐,怎么能吆喝着让别人去坐呢?你加了三聚氰胺的奶粉先给自己的孩子喝喝,加了瘦肉精的肉自己不妨先吃吃再说。如果自己心知肚明,对有问题的东西不吃、不喝、不坐,你凭什么要让别人去吃去喝去坐,这是利欲熏心,利令智昏,它刺穿了安全产品的道德边界。产品不再是“道德产品”,而是道德杀手。在生产过程中,一些无良企业主,包括某些大型国企,有的无视员工死活钉死车间门窗,致使火灾时员工无法逃生;有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生产带血的煤炭;有的为了取得超额利润,极力压低员工待遇,甚至雇佣童工等等。这些企业应想一想,将老板自己赶到危机四伏的井下生产带血的煤,“囚”在有火灾隐患的屋子组装产品,把待遇压到勉强吃喝,你能接受吗?你觉得很道德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将心比心都是一理,没有了道德边界的生产,就只会是生命的无底黑洞,没有任何安全可言。
生产道德的约束毕竟局限,只有立法上对敢于突破生产道德底线的行为进行严惩,要让其付出高昂的、难以忘记的代价,让其永记安全生产的道德边界,要让自己挖掘的道德黑洞成为自己的坟墓,让其每每离开这一边界,就会想起曾经付出的代价。 (张同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