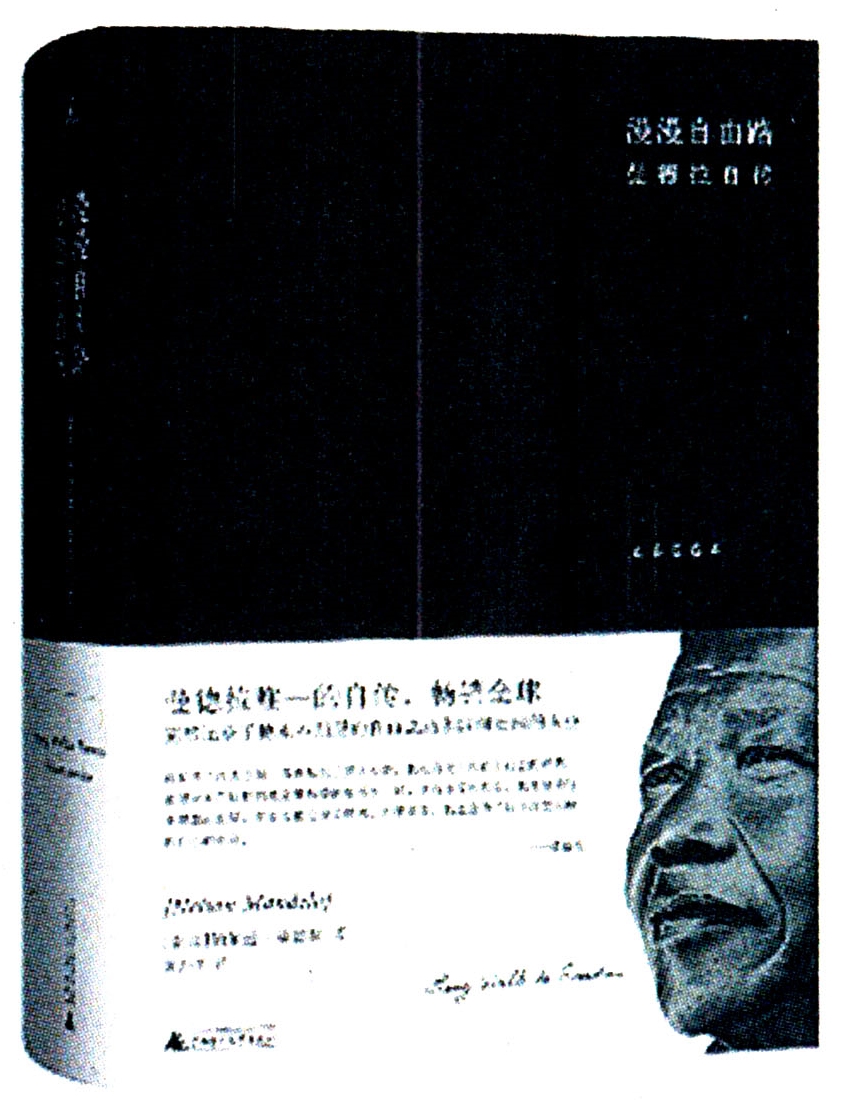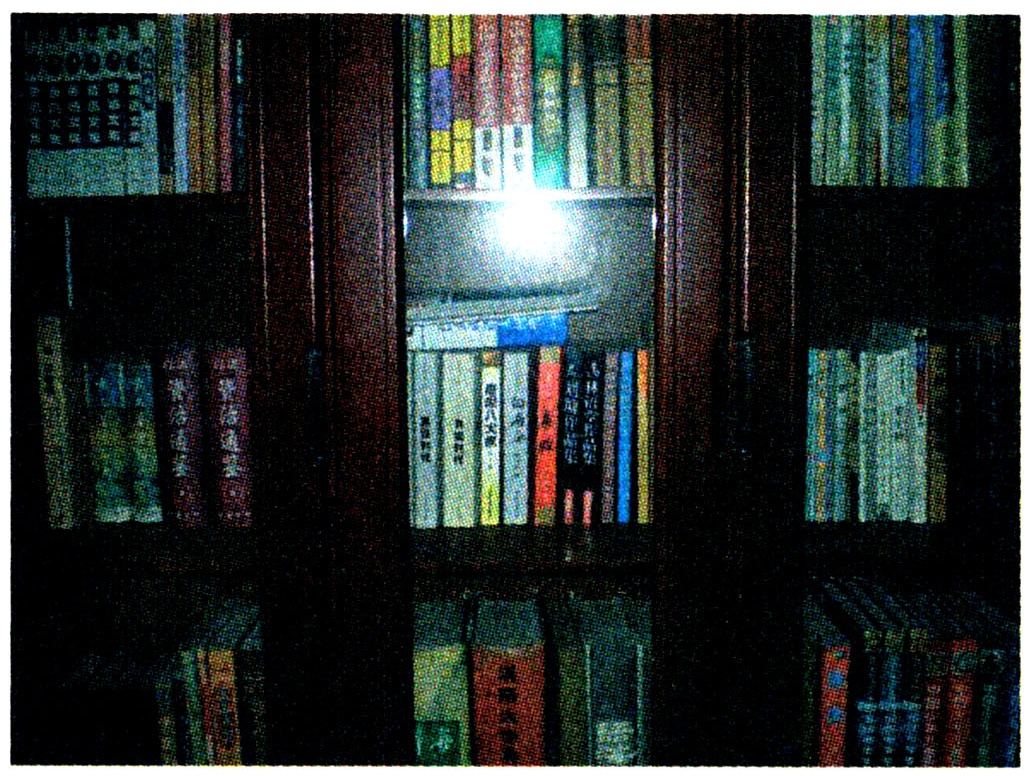
是否喜欢读书,是另外的话题,我是喜好藏书的。晚上或闲暇时,喜欢坐在书桌前,看书架上一排排的书。或者只是这样看看,或者取下其中的某一本翻上几页。
这些书,有书店买的,有网上购的,有旧书摊淘的,有朋友送的。时间长了,日子久了,书架就一层层摆满了,书桌上也堆了不少。
再说说我儿子的书吧,他两岁十个月。年龄不大,书不少,床头柜上堆不下了,妻子便集到了收纳箱里。儿子的所有书要堆起来,足有一尺多厚。他之所以有这么多书,我想,与其父望子成龙有关外,就是与爱书、喜买书不无关系。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说有关我藏书的话题。
我两岁十个月大的时候,也就是我儿子这般大那会儿,属于我的书,应该是没有一本的。因为自打我记事起,家里仅有两本书,依稀记得一本是《农村百科知识》,一本是《果树修剪100问》。在小学四年级以前,在家里,我再没见过除我和姐姐课本以外的任何书了。
属于我的第一本书的得来,印象极其深刻。当时上四年级,忙假刚过,父亲带我去镇上缴粮。粮站门口装得满满当当的架子车、手扶拖拉机,蜿蜒排了二里多路。从早上八点一直到中午十二点粮站人下班吃饭,都没有轮到我们。于是,父亲就带我去了附近的新华书店。
进了书店,迎面是大U型的柜台,后面是大U型的书架,上至天花板。我平生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书,心里无比兴奋。这边瞅瞅,那边看看,总觉得眼睛不够用。父亲嘱咐我先看着,他缴完粮,过来给我买一本书。
柜台距书架有两米左右远,我从进门的左边开始,一个书架一个书架地往过看。从上边到下边,从左边到右边。摆得整整齐齐的书只能看到书脊,看不到封面。就凭着书名,我让阿姨拿书给我看。一本书接到手翻几页,看不懂,再换一本,还是看不懂。然后再要,再看……阿姨懒得理我了,径直到办公桌后边聊天去了。
父亲大汗淋漓地进来后,问我有没有选下什么书,我摇摇头。看我不愿离去的样子,父亲只好帮我选。因为没有小学生能看的书,在阿姨下班的催促声中,父亲选了一本《校园诗歌精选》。我现在想,没多少文化的父亲当初可能是觉得那本书内容少,句子短,字我都认识,小学生能看得懂吧。回家的路上,坐在父亲的架子车上,我将书捧在手里,一会儿翻一翻,一会儿又抱在怀里。
回家后,我在本子上练习了几遍,并看了挂历后,在书的扉页上写下了“购于法门镇新华书店 某年某月某日”。吃完饭,当我真正去读那本书的时候,可怎么也看不懂书上说的是啥意思。看了后记后,才恍然大悟,原来书上所说的校园,是大学的校园。天哪!大学校园是啥模样我一点都不知道。尽管读不懂,我还是把书放在了我写作业桌子的抽屉里,而后,也时不时拿出来翻一翻。
村里有个叫军利的同龄孩子,其父应该是个干部吧,在城里上班。他家里有很多的花书(连环画),我和他的关系很好,经常给他带红红的软柿子吃。他也让我去他家看花书。后来,军利偷偷地送给我两本,我将其放进抽屉藏了起来。现在想想,我俩关系之所以那么好,原因不外乎书这个媒介。
初中三年时间,有关书的记忆是模糊的。只记得初中毕业时,母亲在过年扫舍时,打算将我以前的课本当破烂卖掉,我玩耍回来刚好碰上,硬是将那些书留了下来。
上高中时,家里盖房请来木匠做门窗。在我的极力争取下,父亲让木匠用多余的木料为我做了一个简易的书架。我郑重其事地将我几年的课本及平常收集到的书摆上了书架,竟也有两排之多。看着整整齐齐那么多的书,心里很是满足。
上大学,包括后来工作的几年时间,我买书越来越多,当时去我住处的人都说,有这么多的书啊,可以开个阅览室了。后来在我离开西安时,书多得无法搬走,没有办法,只能忍痛割爱,精简又精简后,带回了两箱子的书。
坐在书桌前,看着书架上的书,竟然想了这么多。一段关于书的思绪飘飞,使我心情无比宁静,如窗外的雨,滋润过心田一样。
□陈云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