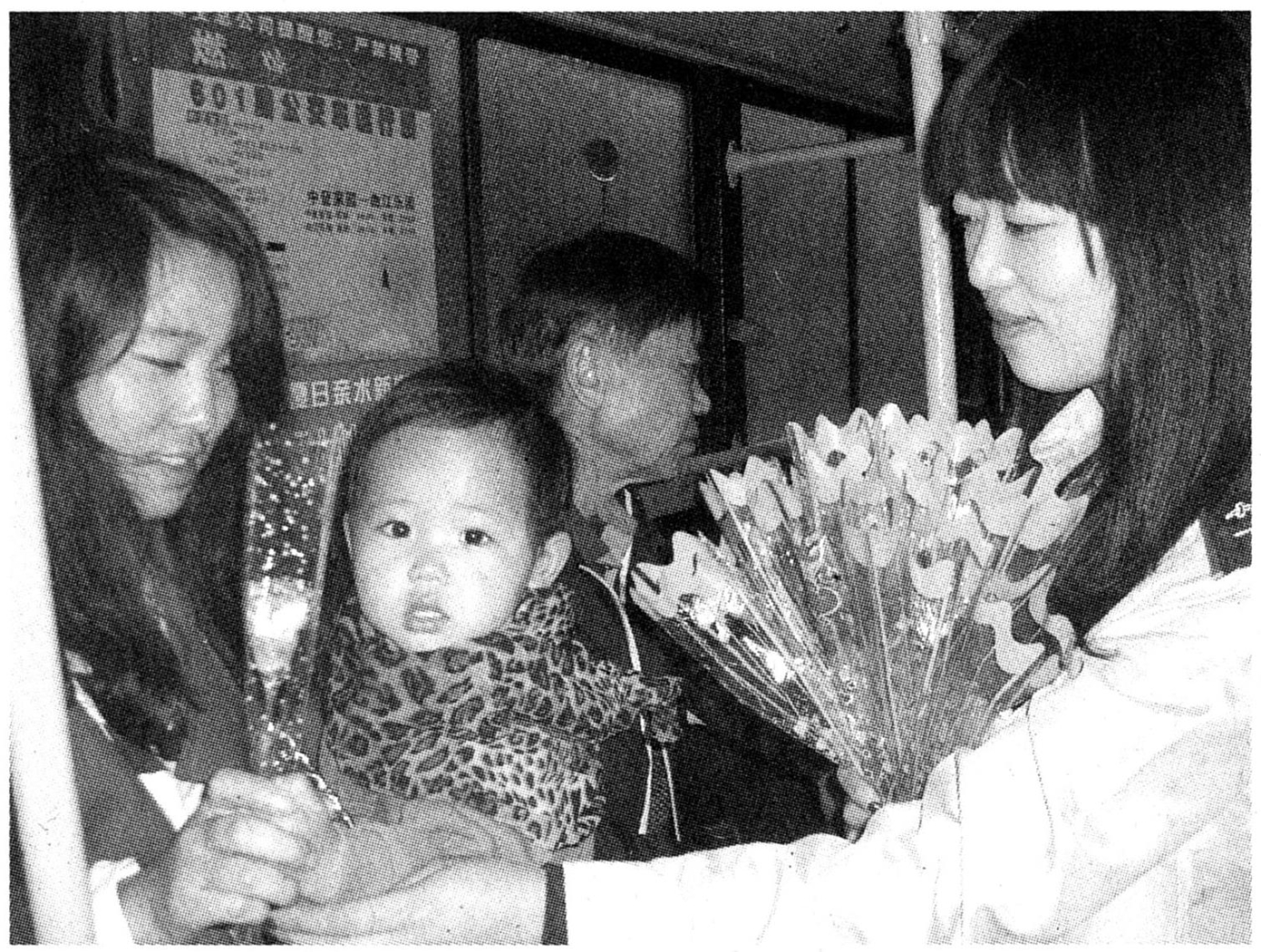(上接一版)
“工作就是打‘游击’战”
“忙一个地方的地质调查,再次带着自己的衣服、帐篷、睡袋、锅灶、喷灯等,雇用当地附近居民的一头驴或者一头马,也或者是一头牛或者一头骆驼,驮着自己的这些行李,然后转战另一个工作根据地。有一次,在一处无人区最艰苦的地方忙完工作任务后,等回到‘大本营’,同事们几乎都不认识我了,我发现自己已经32天没有洗过头、洗过澡。”张文峰说。
新疆乌恰项目地处帕米尔高原,往西不到五十公里就是中亚邻国吉尔吉斯斯坦,公路在项目工作范围外十公里处就中断了,工作区内仅有简易牧道通行。这里地形切割强烈,沟长且深,一般的GPS信号接收器和卫星电话都得在半梁上才有信号。在这里的工作,张文峰和他的同事们就是依靠“打游击”的方式才完成。
西藏萨迦项目地处喜马拉雅山北部,调查区平均海拔4400m以上,5000m以上高山区面积394平方千米,约占总面积的15%,且调查区南部高山区的地质工作最难开展。综合考虑后,他亲自带队,和2名业务骨干去完成剖面测制任务。在海拔5740米的山峰上,他们冒着寒风小雪,用了一天半的时间登顶,除了工作,他还要花费更多的心思,考虑和寻找选择安全的帐篷营地和干净方便的水源。为了减少物资重量,也为了相互取暖,晚上三个人挤在一个帐篷里睡觉。每天早作晚歇,在第五天终于结束这条剖面的测制工作。
机关办公室主任白宏伟介绍,张文峰是南方江苏人,又是八十年代后出生的家庭独生子,最初大家都怀疑他能否适应工作环境,担心他半路当逃兵。当大家看到他遇河淌水、遇梁翻山的行动后,都不由得给他伸出了大拇指。
“成绩在向前多走的一步之中”
西藏乃东项目地处青藏高原雅鲁藏布江两岸,海拔高、紫外线强、风沙大、经常有雨雪冰雹天气,塌方泥石流亦是常见。2008年9月,区调组为联图需要,在已完成了矿产填图工作的范围内,又布置了两条穿越地质路线。为绕过风成砂直接观察露头地质现象,张文峰和同事往山坡又爬行约200m后,沿等高线继续当天的任务。
然而,在这一次绕行跑偏的路线上,他和同事两个人“意外”发现了铜矿化转石,随后又艰难地往上爬了80m后,又发现了宽约5m,长约25m的矿化石英脉露头,这便是后来滚动勘查的洛村铜矿最早被发现的也是最富的矿化石英脉露头。根据这一线索,经综合研究,项目组将此地区列为找矿重点工作区。
2009年7月,他和项目组同事顶着沙地强烈的日晒和反射,每天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沙地中上下一千多米地搜寻。功夫不负有心人,三天后在一片风成砂覆盖较浅的灌木丛下,发现了大量铜矿化矽卡岩转石。经槽探工程揭露,控制矿体长度超过200m,宽度9-20m。随后,项目组对矿区已知矿(化)体开展了系统的探槽揭露与编录,并在东侧又发现一处矽卡岩型矿体露头,工程控制长度也超过200m,宽1-1.5m。刻槽化学样分析结果显示,所有的样品均达到边界品位,绝大部分达到最低工业品位。
同年9月上旬,听到当地藏族民工无意说起,在已发现铜矿的大沟东侧,曾有人拉出过两车黑乎乎的石头。他又和一名负责矿产工作的同事放弃休息,又去了洛村。而大沟东侧不同于西侧满山坡的细砂,这里全部都是一人高的带刺灌木,二人在灌木里钻了四五个小时,水已全部喝完,在浑身带伤而快灰心的时候,终于在地上发现了一块只有拇指大的矽卡岩,随后又发现了一块婴儿拳头大小的铜矿化矽卡岩转石。于是,他们越爬越高,发现眼下的矿化转石越来越多,最后发现了一个被挖过的大坑。当天,二人再也顾不得烈日暴晒和灌木的随时划伤,又对接触带作了简单追索,发现此地出露矽卡岩露头长约150m,最宽处约7m。因此,一个有着广阔前景的铜矿产地终于被揭开了神秘的面纱。该项目随后作了滚动评价项目。
对同事们介绍他的这些事迹,张文峰说:“地质调查工作,没有这点韧劲和追寻探索的精神,就没有办法干好。而希望和工作成绩也往往就出在你向前多走的一步或者一米之中”。
“每天都演绎着不同的艰辛”
面对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个人荣誉,张文峰一再强调说:“这是属于大家的,属于同事们的”。白宏伟也说,每次申报他的事迹参评各种先进,他都是推辞,要求让申报其他同事。
无论是在机关还是在项目一线工作,无论是当项目负责人还是作为一般员工,张文峰给同事们留下的都是一个吃苦耐劳、为人谦虚低调的良好印象。
2010年的西藏乃东项目后期,张文峰开始担任项目负责。在野外工作期间,他总是将最艰苦最复杂的路线留给自己,把方便尽量让给别人。一次,坚持完成了当天的路线,但因采集样品过多过重,加之工作区雨水较多,在越过一道小溪时不慎摔倒在地,右腿膝盖被尖利的石头划伤,鲜血透过内衣将厚实的牛仔裤染得殷红。尽管如此,他要求一起的同事不要声张,连续几天依旧坚持工作。
还有一件让人难忘的事情。那是一天下午6点,天黑之后,暴雨突降。原本山间的简易路上,已经流水成河,更令人揪心的是,一个刚刚参加工作的同事小王,在结束了当天的物探工作后却没有下山。从野外回到驻地的张文峰得知,带领几位同事带着馒头和热水,把车开进工作区域去寻找。晚上11点左右,才发现小王的身影出现在河对面。这时山谷里的洪水夹着几百公斤的石头在河里翻滚,等到凌晨2点河水小了一点,张文峰带头,和大家一起才把小王接过河岸往回走。然而等出了村口,去时的道路上全是一米厚的泥石流,车子陷在里面像是被焊住了一样。待大家回到项目驻地,已经拖着一身的泥水、寒冷、饥饿、疲惫坚持了21小时。
白宏伟说,像这样艰辛的工作事例,对于在高原上从事野外地质工作者来说,并不是新鲜事。他们每天走着不同的路,演绎着不同的工作艰辛和人生故事。
本报记者 杨志勇
采访手记:张文峰是高原上的一个地质行者,只有“行者”最能概括他的思想追求和精神境界。试想,如果没有行者的信念和追随精神,又如何能够坚持这份工作?又如何能够在这份工作中以苦为乐并取得成绩?写完关于他的通讯稿,记者坚信了一句人生哲语:人生的矿藏就在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