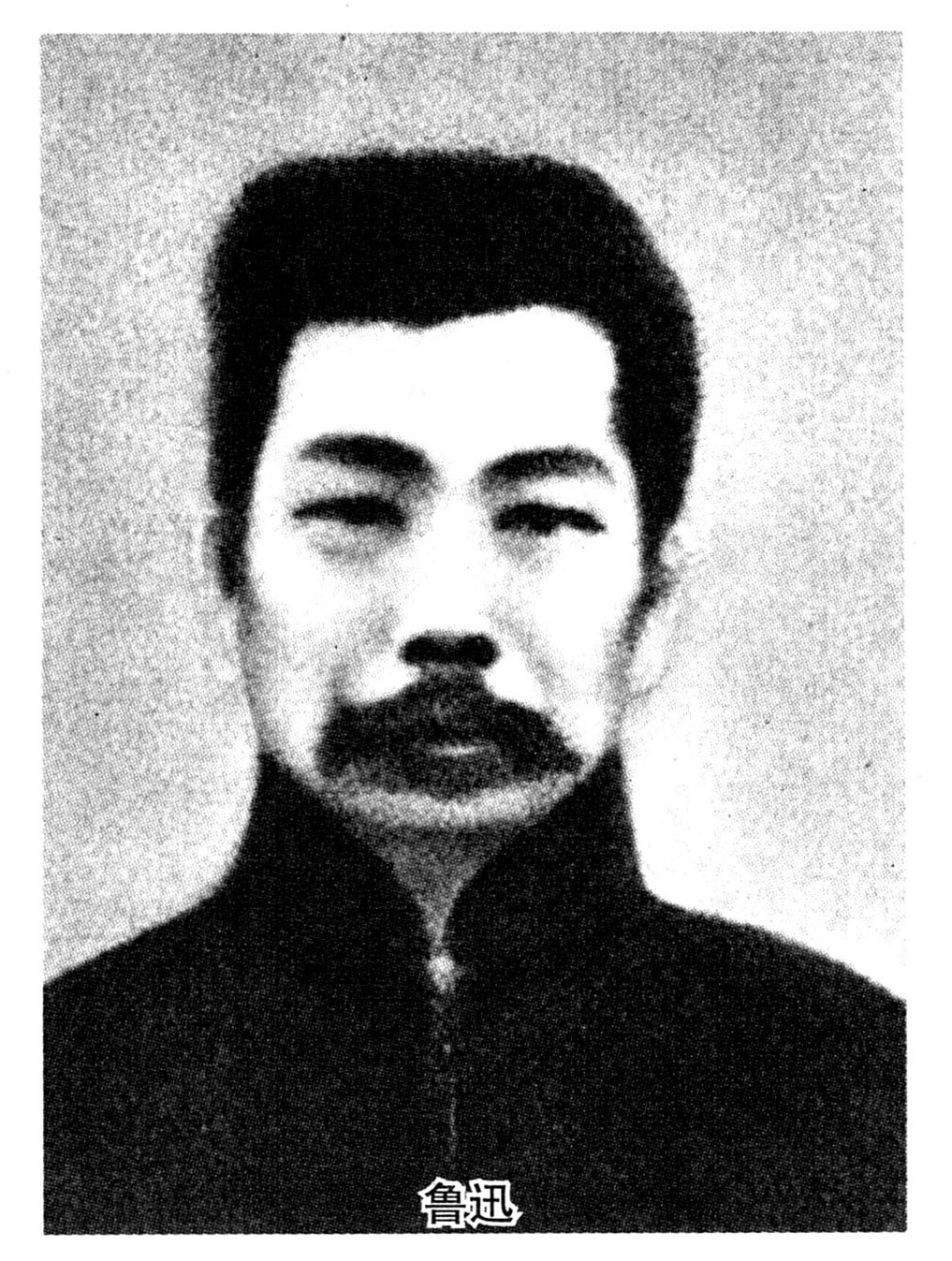
鲁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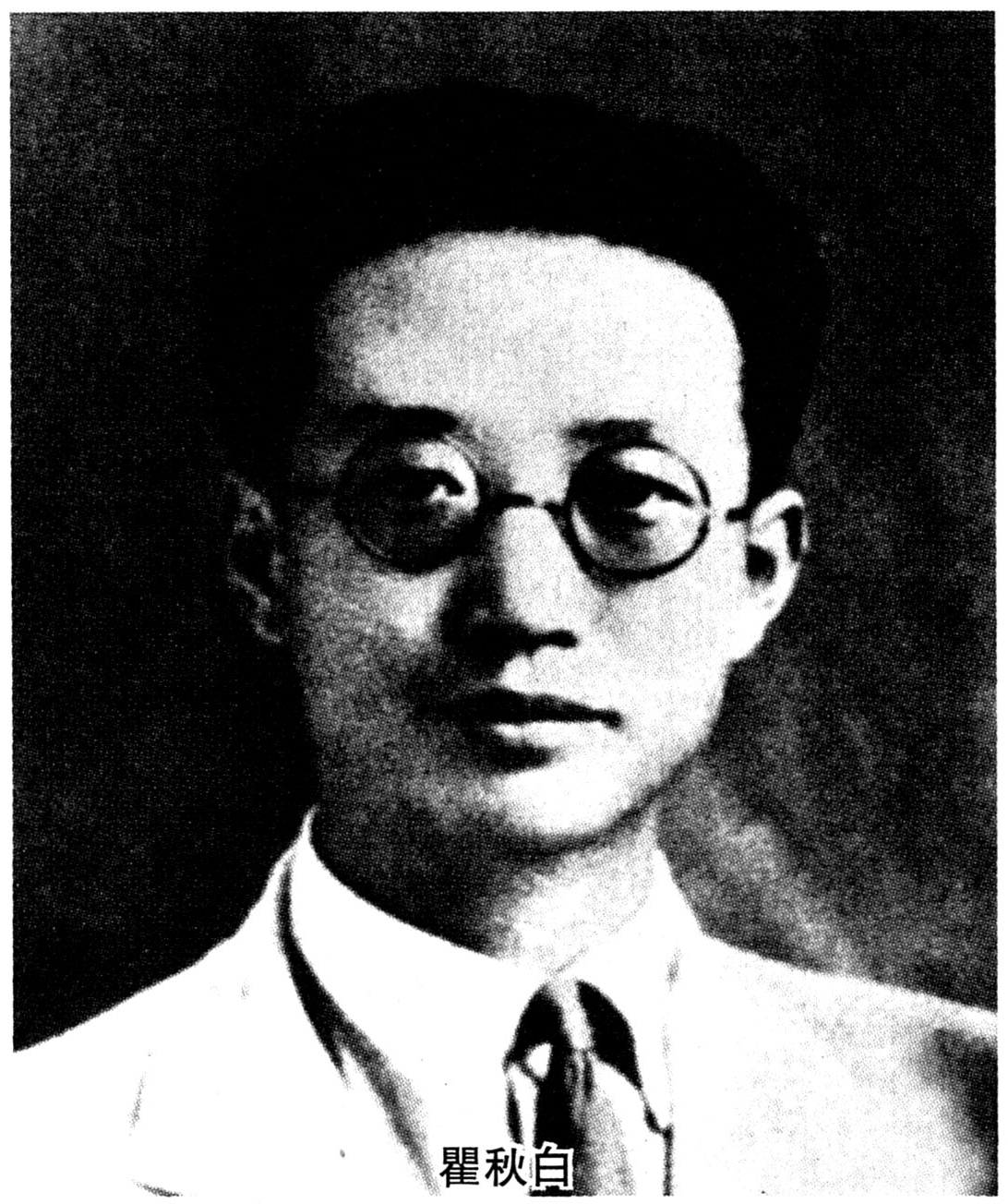
瞿秋白
从弄堂口出去,沿山阴路向南,步行不过三五分钟,便几乎同时可见瞿秋白旧居和鲁迅故居。两者距离之近,似乎也从空间上昭示着这对忘年交的亲密关系。
瞿秋白旧居位于山阴路东照里,虽也是上海市文化保护单位,但实际上只有一块牌子,现已是民居杂院。而位于对面山阴路大陆新村的鲁迅故居,一个单元三层楼房,则修缮一新,不但有专人管理,且参观还得买票。
大陆新村系大陆银行1931年投资建造,其一弄9号由日本友人内山完造以其书店职员的名义租下,是鲁迅从1932年4月11日至1936年10月19日去世时的住所。鲁迅在此居住期间,先后编写了《伪自由书》、《南腔北调集》等7本杂文集,翻译了《死魂灵》、《俄罗斯童话》等外国名著,编成了《引玉集》、《凯绥·坷勒惠支版画选集》等重要作品,其中也包括1932年10月写的那首广为人知的《自嘲》诗。
82年过去了,在此牛一之日重读此诗,感慨良多。谨敬录如下。
自嘲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以往,或许是受毛老人的影响,包括我自己在内,许多人特别感兴趣、甚至将其作为座右铭的,是这首诗中“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一联,以为表现了鲁迅鲜明的不妥协的爱憎立场。现在人老了,心境变了,再读此诗,对这一联的感觉好像又有了些不同。似乎这里有一点反话正说的味道,似乎“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与“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表达的竟是类似的情绪,都是自嘲自讽之语。
显然,从诗名看,就是“自嘲”,这才是主题。按理说,鲁迅不会离题万里,在《自嘲》诗中竟去表达自诩、自赞、自我欣赏、自我肯定的意思。这与全诗的其它六句也不协调。因此,在这里,鲁迅究竟是主张、肯定“横眉冷对千夫指”,还是讽刺、揶揄“横眉冷对千夫指”,确实是值得商榷的。
鲁迅在《华盖集·题记》中曾写道:“这运(指华盖运),在和尚是好运:顶有华盖,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了,只好碰钉子。”同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否也是个“华盖”,“要给罩住了,只好碰钉子”呢?
鲁迅的诗文耐读,但也难读难懂。因此鲁迅总是有一种“不被理解的孤独感”。而长期以来鲁迅一直被定义为“不妥协战士”的形象,或许竟是个天大的误会,也未可知。
从鲁迅与瞿秋白的关系上,或许就很能够说明这个问题。
鲁迅与瞿秋白是从1931年5月开始文字之交的。从1932年开始,只要瞿秋白遇险无处存身,总是到鲁迅家里避难。在经济上,鲁迅对瞿秋白的扶助也是不遗余力。瞿秋白住在东照里期间,还与鲁迅合作写了11篇杂文,都是由瞿秋白起草,经鲁迅修改,再用鲁迅的笔名发表,后来鲁迅又把它们收到自己的集子里。鲁迅一生中,除早年曾与二弟周作人一起写作过外,瞿秋白可以说是与他合作写作的唯一之人。
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在回忆中写道:“当时鲁迅几乎每天到日照里(即今东照里)看我们,和秋白谈论政治、时事、文艺等各方面的事情,乐而忘返……秋白一见鲁迅,就立刻改变了不爱说话的性情,两人边说边笑,有时哈哈大笑,冲破了像牢笼似的小亭子间里不自由的空气。”
瞿秋白牺牲后,鲁迅异常悲痛,竟长时间“木然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悲痛得头也抬不起来了”。这一年,鲁迅的身体已经很差,又有许多事要做。但他却放下自己的事,支撑着病体,立即着手选编瞿秋白的译文集《海上述林》,并托名“诸夏怀霜社”(瞿秋白名霜)出版。他亲自抄录部分稿子,校对全部清样,还在内山完造的帮助下,特地送到印制水平更高的日本去印。上卷出版后,鲁迅又亲拟广告:“本卷所收,都是文艺论文,作者既系大家,译者又是名手,信而且达,并世无两……足以益人,足以传世。”
从年龄上看,鲁迅与瞿秋白已属于两代人。但他们不仅没有“代沟”,而且鲁迅还不寻常地送给瞿秋白一副对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究竟他们为什么会建立这样不一般的友谊,为什么瞿秋白会让鲁迅产生“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感叹呢?
或许,这与瞿秋白对鲁迅与众不同的理解有关。
在一般人眼里,鲁迅原则性强,斗争性强,对“敌人”一点也不宽恕,骂人不留情面,近乎刻薄。但在瞿秋白看来,事实却并非如此。
瞿秋白曾指出:陈西滢、章士钊等人的姓名,“在鲁迅的杂感里,简直可以当作普通名词读,就是认作社会上的某种典型”,而并非后来读者说的,是“攻击个人的文章”。在谈及“革命文学”论争期间鲁迅对创造社的批评时,瞿秋白再一次提到鲁迅这种“经过私人问题去照耀社会思想和社会现象的笔调”,甚至是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近乎恨铁不成钢的自虐。对此,鲁迅曾说:“看出我攻击章士钊和陈源一类人,是将他们作为社会上的一种典型这一点来的,也还只有何凝(瞿秋白笔名)一个人。”显然,在长期被众人误读却又无法解释的郁闷之时,仅此一点,就足以使鲁迅产生“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感叹了。
回到《自嘲》一诗,鲁迅是否也有被“误读”的地方呢?鲁迅究竟是在主张、肯定“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还是讽刺、揶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呢?现在也有不少人试图从鲁迅当时的情境中论证应是后者,即同样是鲁迅对自己无可奈何的揶揄、戏谑。
后来,鲁迅在以此诗为日本友人杉本勇乘题写扇面时,将“冷对”改为了“冷看”。虽仅一字之差,但“冷对”与“冷看”的意思差别还是很大的。从这里,或许也多少透露出鲁迅对自己的诗句可能会被曲解的担心。
但反过来,将“横眉冷对千夫指”认定为只是鲁迅对自己的揶揄,就不是曲解?当然也无法肯定。
也许,在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情莫过于真正准确地去理解别人,特别是去理解一个思想深邃丰富的人。因此才有“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的故事,才有管鲍之交的千古佳话,才有“一花开五叶”的流派之分,才有“可与知者言,难与不知者道”的诉说,才有“人生得一知已足矣”的感慨。
鲁迅先生曾评价《红楼梦》说:“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可谁知道曹雪芹的本意究竟是什么,或什么都是,或竟什么都不是呢?
同样,对瞿秋白也是如此。
这个曾经被推举顶替陈独秀的中共早期领导人,这个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他写的《多余的话》,究竟是多余的还不是多余的,究竟是“变节的忏悔”,还是“一生奋斗的诉说”,或只是一种“疏离感的自白”呢?
人的感情往往是复杂多元的,人们对自己思想的表达越是内涵丰富,越可能是不清晰不完整,甚至是充满着矛盾冲突的,并不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非好即坏、非爱即恨、非对即错那样简单。在很大程度上,人心是个完全孤独的封闭世界,是处于不同位置的,他人永远不可能真正完全进入的。奢望别人的理解,或许永远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
在走进人生第六十三个春天的这个早晨,我像往常一样,骑着单车匆匆从大陆新村和东照里之间的山阴路上驰过。在瞧见路两旁相对着的两块标牌的那一刻,我的心底突然渗出一丝凄凉。对这两个伟人的内心世界,多少人曾悉心探求,许多人甚至还因此混了一辈子的饭吃。可这些探求的结果,这种似乎已被普遍认同而近于固化的形象,离真实的他们究竟还有多远呢? □叶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