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雪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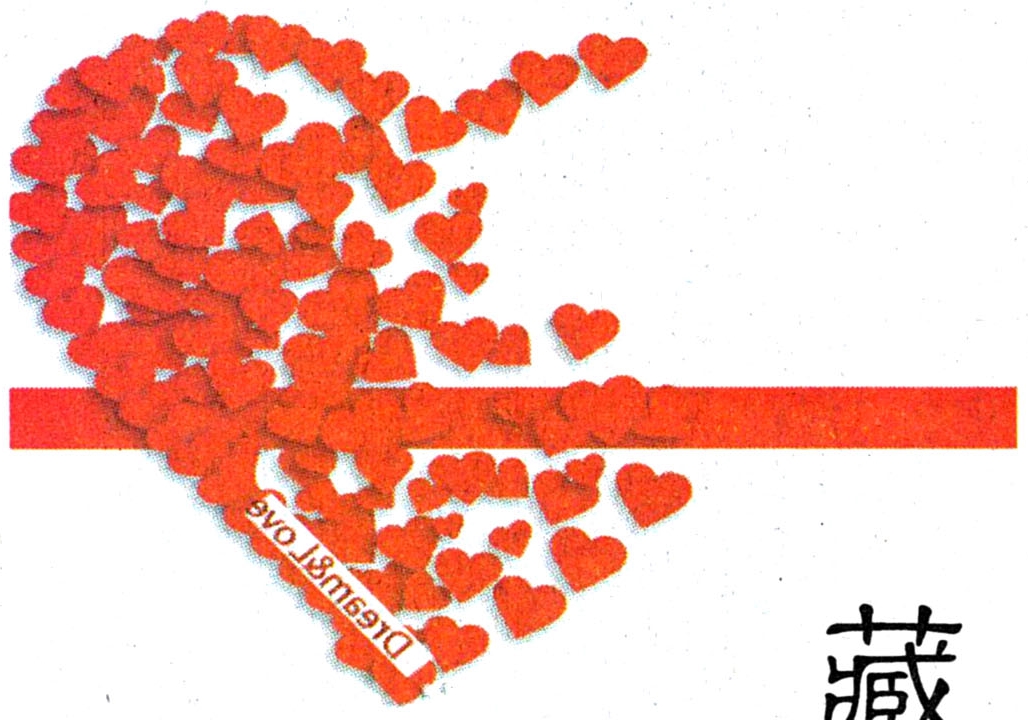
重回乡下的娘家,是这个冬日的下午。进了门,母亲便急着招呼:“上炕,上炕!”我再抱点柴烧炕,一会儿就热了。
长这么大了,就是喜欢冬日里用柴火烧得热腾腾的炕头。
这些柴全是爷爷在世的时候收拾的。每到冬天,爷爷都要上山里砍柴,粗棒细枝,整整齐齐地背到家里。在冬日的严寒中,依偎在爷爷身边,看他用柴火热牛奶、熬茶喝,就连母亲的火炉里取暖用的燃料都是爷爷自制的木炭。有了这些柴火的温暖,整个屋子里暖融融的。那时候,几季的辛苦,满身的疲惫,一切的寒冷,都在爷爷的柴火里消融、飘散。
那年的冬日,我死缠硬磨要跟爷爷去山里打柴,一向疼我的爷爷无奈地带上我这个“累赘”。一进山里,刺骨的寒风迎面而来,像一把把利剑直刺到我嫩嫩的脸颊,山上一片苍凉,偶尔能见一个个啃干草的牛儿。爷爷光着双手举起斧子,很有力且富有节奏地砍着柴,我却像只畏缩着的小鸟钻进一丛灌木丛中不敢仰头,怕这凛冽的寒风。爷爷像位舞者,山间回荡着“嗨嗨……”的号子声。天色越来越暗,风越刮越冷,一会儿天空中就有零零星星的雪花飘散下来。爷爷见我冻得泪汪汪的,就捆起他那沉重的柴棒,拉着我的手。我分明看见爷爷那一道道冻得裂了深口子的手上已渗出了鲜血来。走了一路我哭了一路。爷爷安慰我:“快到家里,有热炕就不冷了!”哎!他哪里知道我是为他而流泪呀!
那年,我12岁。
从那一次起,我坚决反对爷爷上山砍柴。他的绳子、斧子全让我悄悄藏了起来,可生性倔强的他又东翻箱西倒柜找了出来。
后来,家里盖起了小楼。我和哥哥、弟弟相继都工作了,我想这样的条件总该了断爷爷砍柴的念头了。加之,他都近80岁了,哪有力气扛起那沉甸甸的担子呀!可是,每次回家都碰到爷爷佝偻着身子多多少少要往家里背点柴,我气得直嗔怪他:“人家现在都用煤,谁还烧柴火?叫你不要背了,你就不听。”
“煤?没电时就用不成了!”爷爷拉长嗓子喊。
也许,爷爷把砍柴当作他晚年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吧。两年前大雪飘飞的季节,爷爷得了一场重病,在他弥留之际我没见到他。临了,听母亲讲,六个孙子当中爷爷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他嘴里念念不忘:“妞妞的喜酒我喝不上了!”可是,当爷爷去世的噩耗传到我耳中时,我的心情很平静,没有掉一滴眼泪。我想: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爷爷就永远不再砍柴了。
去年夏天,在我出嫁的日子里,瓢泼大雨断断续续下了快半个月了,许多电线杆都被大水冲垮了,被迫停电三天,这个喜事可怎么办?正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父亲提出当年爷爷在老屋里还存放着许多柴。果然,我们曾经住过的老屋房檐底下垒着两座小山似的干裂了的柴垛。停电了,但锅下面的火焰依然很旺,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这时,爷爷那背着沉重柴垛的瘦弱身子,在雪花飘零的天气里,蹒跚而行的情景又浮现在我眼前。爷爷,如果你还活着,那该多好!饱含着老人辛酸的柴垛在我最需要的时候派上了用场。
我心如刀绞,泣不成声。
爷爷已经离我们而去了,但他的柴火一直温暖着我的心,最主要的是爷爷藏在柴垛里深深的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