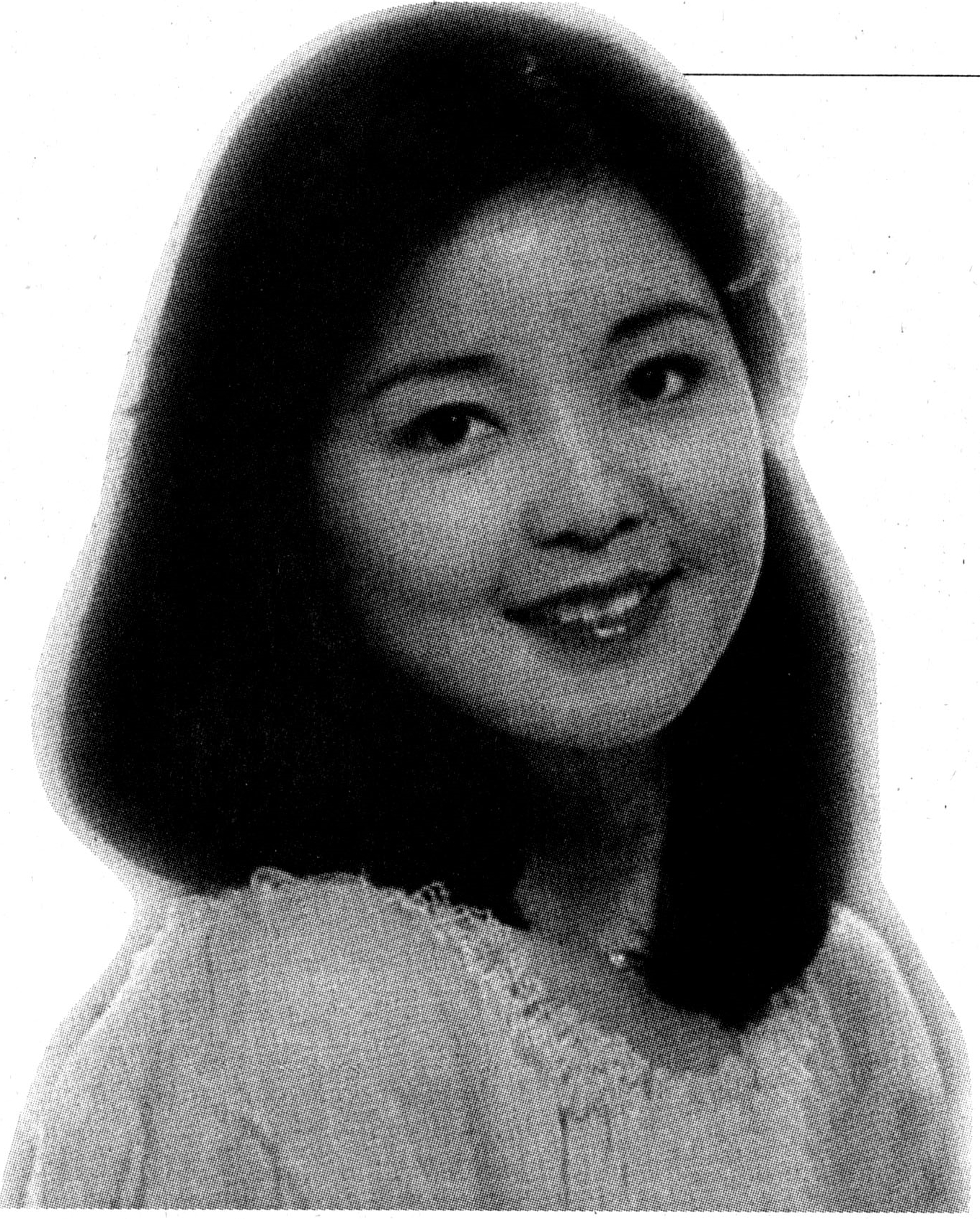较之喜大求全,日本人更关注局部、细节,关注微观世界,关注弱小生命,宁舍森林而看树木。
比之西方美的昂扬、凌厉和工致,日本美显得内敛和朴实;比之中国美的大气、写意和深刻,日本美显得本分与谦和。在具体技法上日本画可谓极尽穷形尽相之能事。其工序之多,用料之繁,费时之久,大概堪称世界之最。东山先生为创作唐招提寺隔扇画,整整耗费了4年时间。
文学世界更是以优美细腻、柔曼婉约为鲜明特点。日本小说一向重细节而轻整体构思,欣赏不了细节,也就欣赏不了日本文学。譬如俳句,短短17个音节简直被日本人摆弄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写尽了心境的涟漪和造化的微妙。如日本“俳圣”松尾芭蕉一首最具代表性的俳句,大意为“古池塘啊,青蛙跳入水里的声音”。著名诗人与谢芜村一首名俳亦有异曲同工之妙:“石老寺钟的裂缝里,酣睡的蝴蝶哟”。而这样的诗句在中国诗词里恐怕不易觅得。
宋词婉约派代表柳永也不过咏到“杨柳岸晓风残月”。最接近俳句的元曲也只到“枯藤老树昏鸦”为止。这也难怪,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开篇第一品便是“雄浑”。从汉高祖的“大风起兮云飞扬”,到曹孟德的“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再到苏东坡的“大江东去”,都是这一风格。而夸张起来,便有了李太白的“燕山雪花大如席”,看得日本人一头雾水,也是他们无论如何也喜欢不来李白的一个原因,实乃审美趣味所使然。
恐怕再不易找出第二个像日本那样对四季更迭那么敏感、对四时风物迷恋得简直到了“同呼吸共命运”地步的民族了。和服上的图案全都是四季代表性的花花草草,并按不同季节换穿不同图案。插花自不用说,就连挂轴也应时轮换,以便在家中坐拥四季。碟盘等餐具也是如此,家家户户都有一两橱餐具排队等在那里换班。甚至和式糕点(“和菓子”)的样式都与时令花瓣相符。不由生叹:真够日本主妇闹腾的了,难怪一结婚许多妇女便不再上班。
和歌俳句里同样显而易见。正如时间是中国诗人最普遍的动机和主题一样,日本诗人也很早就注意到了时间的推移和节序的流转。成书于905年的《古今和歌集》,目录即是按春夏秋冬顺序编排的。吟咏“花鸟风月”等四季景物的“四季歌”在20卷中占6卷,在全集1100首中占340首之多,仅次于“恋歌”。而“恋歌”中的恋情也主要是借助四季风物抒发的。此后各集纷纷效仿。可以说,去掉“四季”,和歌几乎溃不成军。最典型者莫过于俳句中的“季语”了。若无此点季之语(如菜花为春之季语),便不成为俳句。其严格程度大概仅次于中国格律诗的平仄对仗要求。
究其原因,一是由于日本四季分明,雨量充沛,自然景物依时而变。另一点也同日本固有的神道教有关。神道其实就是自然崇拜,认为神在自然之中并孕育万物。天地神祗多达800万,可以说无所不在。因此自古以来日本人就对自然怀有亲近感,与其融为一体。加之日本人的美学追求大多是感性的和情绪化的,于是“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目睹日本无山不绿无水不清,自然植被保护得无微不至,我时常想日本人的环保意识是不是也同这种审美理想有关。 □林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