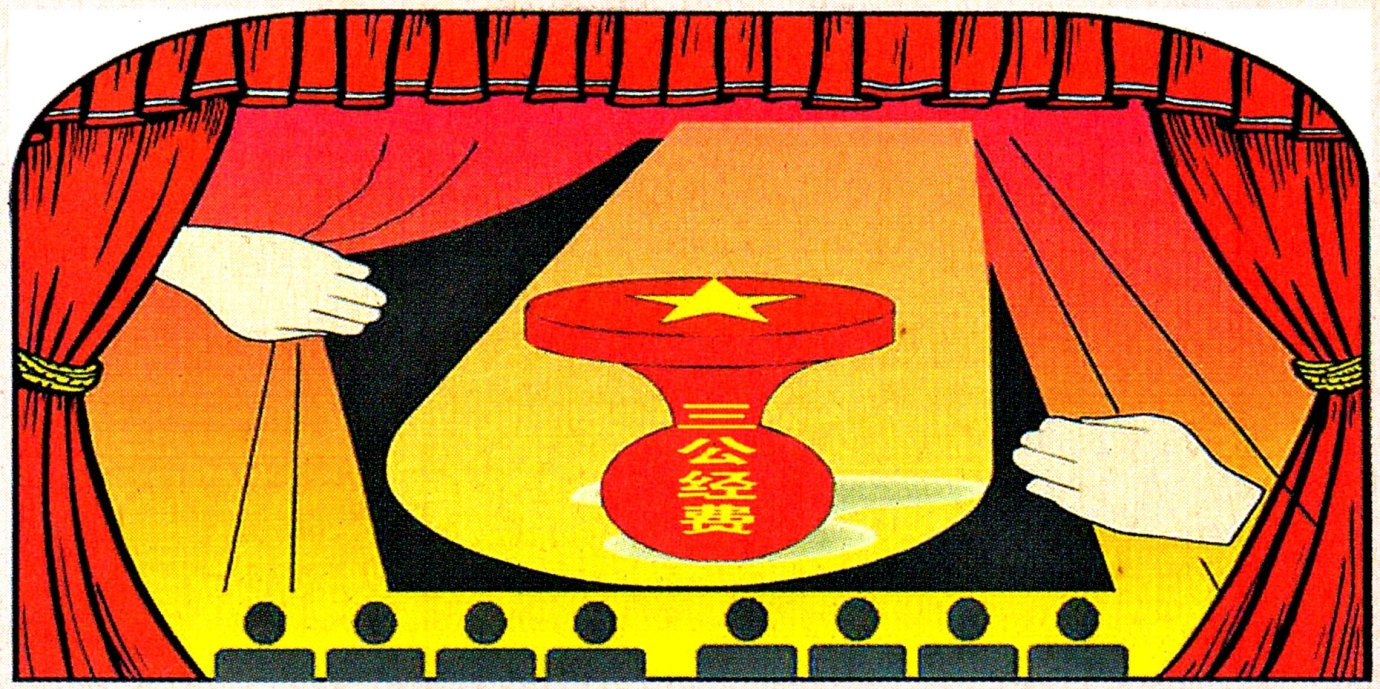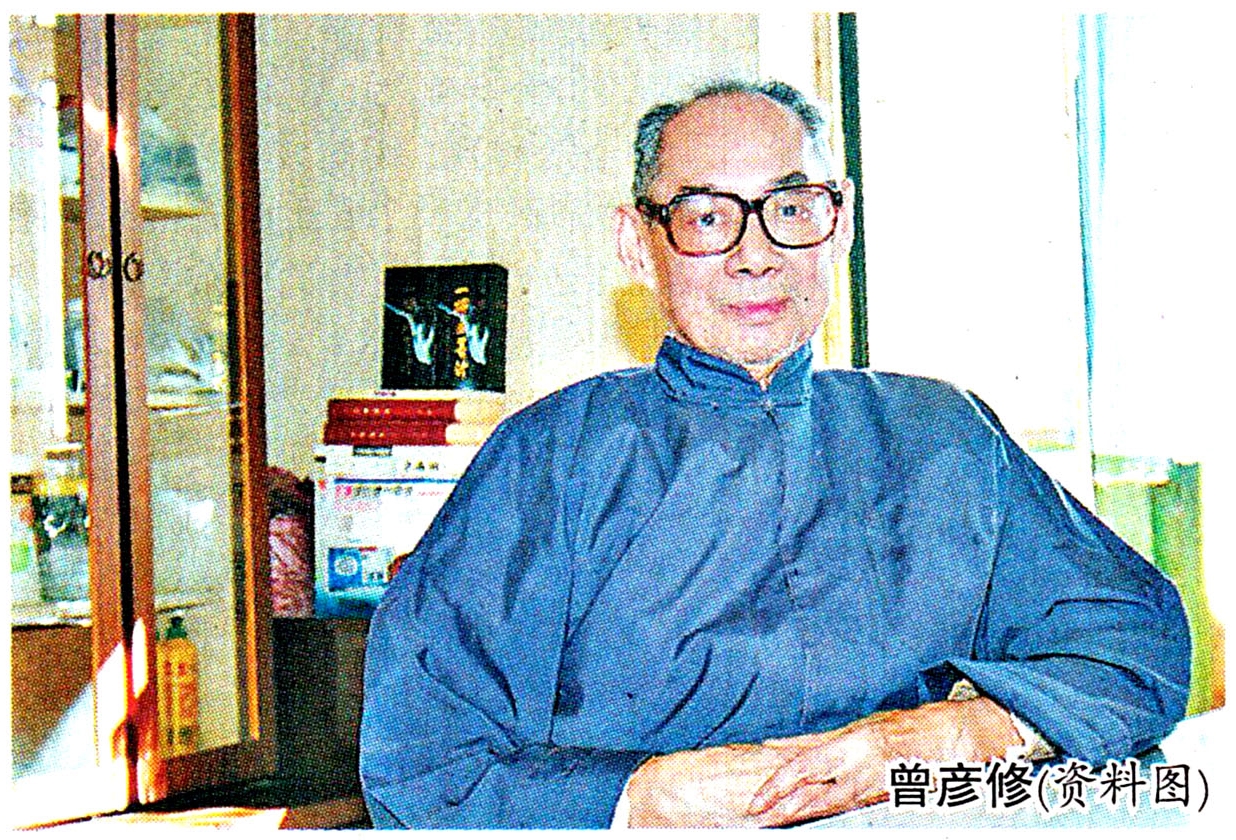
曾彦修(资料图)
曾彦修的《平生六记》记下了他经历的六次政治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土地改革运动、三反运动、肃反运动、反右派斗争和四清运动。这些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头等重大的事件。这本书就是很具体地记下个人在这些运动中的经历,完全无意于展示运动的全貌,可是正如胡适说的“真正的历史都是靠私人记载下来的”,《平生六记》的记载是一部真正的历史。
土地改革运动中,曾彦修率领一个两三百人的工作团到广东云浮县做土改工作。他在书中这样描写了当年流行已久的工作模式:
土改工作队进村后,必须绝对地、长时间地“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建立或重建阶级队伍之后,才能谈得上进入斗争,如反霸、斗争地主等阶段;之后是分田阶段;再之后是建党建政、动员参军等阶段。再之后,又是另派工作队来搞“复查”等等;一个否定一个,一个说前一个“右倾”。已形成宪法,半点不能移动。……工作队动不动就要换三几次。翻烧饼、煮夹生饭,一次一套,统统反右,从不反左,不把农村搞得稀烂才怪。(第3—4页)
三反运动,即所谓“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当时把运动对象称为“老虎”,所以又叫做打老虎运动,《党史》高度评价了这个运动的意义:“‘三反’运动,是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保持党政机关的廉洁,反对贪污腐败的初战。”不过也承认了“在追查贪污犯即‘打老虎’阶段,由于推广‘作出具体计划’,定出必成数、期成数,并根据情况发展追加打虎数字’的经验,要求对于有贪污嫌疑的人‘大胆怀疑,搜集材料,试行探查’,许多地方和部门曾发生过火斗争的偏差。”(第161页)至今还有人写文章称三反运动是一次反腐败的重大举措,予以充分肯定的。
可是事实上呢,这时曾彦修是《南方日报》的社长,他在书中说了他看到的情况,说,这些“老虎”,都是硬逼、硬打出来的,根本上没有什么材料,或者找些事情来附会上去罢了。比这更严重的事,我都体验过,所以我能判断这些全是假的。我一看这些“老虎”,吓了一跳。他们怎么可能会在进城之后,就立刻变成贪污分子呢?这些人,有些不是比我参加革命早么?他们中有哪一个不是经历过多年苦斗,不惜牺牲生命来干革命的呢?有些人还经历过几年艰苦危险的游击战争锻炼的,怎么一进城几天就变成贪污分子呢?……我从根本上不相信会有此等事情。(第14—15页)
1955年,曾彦修是人民出版社的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由反胡风发展而成的肃反运动开始,各单位都按照中共中央的统一布置成立一个“五人小组”领导运动。曾彦修又担任了人民出版社五人小组的组长。可是曾彦修是怎样做的呢?书中说:
我在人民社以第一副社长名义,大约从反胡风后期起即奉命担任单位的“五人领导小组”(单位的最高权力机关)组长,我不得不负起责来,一一把事情弄清。1956年,我已经只能重点对人,而不是对书了。就是说,不务正业了。但我绝不是为了整人而忙,相反地,几乎全是为了脱人于难或脱人于困而忙。(第129页)
在反右派斗争中,曾彦修是出版界排名第一的右派分子;又是第一个上《人民日报》的党内右派分子,1957年7月13日《人民日报》刊出的批判他的文章,引题特别提出“党内也有右派分子”。不过这时候他是人民出版社五人小组的组长,正是他在主持本单位的反右派斗争。他这右派分子是他自己决定要划的。
曾彦修被划为右派分子的经过。倒是很有一点与众不同。书中说:
上面催要“右派”名单了。五人小组急急议了几次很难拟定。倒不是大家要划我的“右派”,而是我不能不自报“右派”,其余四人不大同意。我拟的“右派”名单大约共三个或四个,其中有我。五人小组讨论更困难了,几次定不下来,无一人对我列入“右派”表示赞成。但上面催名单很紧。可王子野、陈原、周保昌、谭吐四人(引者按:他们是五人小组成员)仍久不表态。因为平时关系好,哪里“反革命”要来就来呢!我说,事情摆在这里,上报得用五人小组全体的名义。久无动静是上面在观察我,越拖事情越大,你们也会被拖进去。这里,除陈原同志外都是老“运动员”,亲身经历很多。全国轰轰烈烈,我们这里冷冷清清,又是重点单位,这预示着什么?暴风雨前的暂时沉寂啊!一旦一个“反党集团”下来,整个单位就成粉末了。……经我详说之后,算是说服了五人小组,谭吐说,那就照彦修说的办理罢,不然,未来确是可能更严重。这样,五人小组就算通过了曾起草包括曾某在内的三四个“右派”名单的报告。(第148—150页)
这样的五人小组组长,这样的右派分子,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了。曾彦修就这样成了一名右派分子。可是这一篇《反右记幸》说,这是他的幸事:
像1957年那样九十级地震式的反右派运动,没有被打成“右派”的人固然是大幸,像我这样被提前一点反了右从而免掉了我去发号施令去打他人为“右派”,其实也是大幸。在我尤其是大幸。再不去打他人了,这不是大幸是什么呢?
两难选择,是什么人都碰到过的。可是像在“五人小组组长”和“右派分子”二者之间选择,却是只有曾彦修碰到了。
《平生六记》虽说只是个人经历的回忆录,我看也是一个人的政治运动史,它对历次政治运动的反映,比众口一词的正史更深刻、更生动,在细节上也吏符合事实一些。 □朱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