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徽因(资料图)
母亲去世已经三十二年了。今天,读书界记得她的人已经不多了。老一辈谈起,总说那是三十年代一位多才多艺、美丽的女诗人。但是,对于我来说,她却是一个面容清癯、削瘦的病人,一个忘我的学者,一个用对成年人的平等友谊来代替对孩子的抚爱(有时却是脾气急躁)的母亲。
早年
我的外祖父林长民(宗孟)出身仕宦之家,几个姊妹也都能诗文,善书法。外祖父留学日本,英文也很好,在当时也是一位新派人物。但是他同外祖母的婚姻却是家庭包办的一个不幸的结合。外祖母(林徽因的母亲何雪媛是林长民的第二位夫人。)虽然容貌端正,却是一位没有受过教育的、不识字的旧式妇女,因为出自有钱的商人家庭,所以也不善女红和持家,因而既得不到丈夫,也得不到婆婆的欢心。婚后八年,才生下第一个孩子——一个美丽、聪颖的女儿。这个女儿虽然立即受到全家的珍爱,但外祖母的处境却并未因此改善。外祖父不久又娶了一房夫人(林长民的第三位夫人程桂林),外祖母从此更受冷遇,实际上过着与丈夫分居的孤单生活。母亲从小生活在这样的家庭矛盾之中,常常使她感到困惑和悲伤。
童年的境遇对母亲后来的性格是有影响的。可能是由于这一切,她后来的一生中很少表现出三从四德式的温顺,却不断地在追求人格上的独立和自由。
少女时期,母亲曾经和几位表姐妹一道,在上海和北京的教会女子学校中读过书,并跟着那里的外国教员学会了一口相当流利的英语。一九二〇年,当外祖父在北洋官场中受到排挤而被迫“出国考察”时,决定携带十六岁的母亲同行。关于这次欧洲之旅我所知甚少。只知道他们住在伦敦,同时曾到大陆一些国家游历。母亲还考入了一所伦敦女子学校暂读。
在去英国之前,母亲就已认识了当时刚刚进入“清华学堂”的父亲梁思成。从英国回来,他们的来往更多了。他们之间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珍爱和对造型艺术的趣味方面有着高度的一致性,但是在其他方面也有许多差异。父亲喜欢动手,擅长绘画和木工,又酷爱音乐和体育,他生性幽默,做事却喜欢按部就班,有条不紊;母亲富有文学家式的热情,灵感一来,兴之所至,常常可以不顾其他,有时不免受情绪的支配。
父亲在清华学堂时代就表现出相当出众的美术才能,曾经想致力于雕塑艺术,后来决定出国学建筑。母亲则是在英国时就受到一位女同学的影响,早已向往于这门当时在中国学校中还没有的专业。在这方面,她和父亲可以说早就志趣相投了。一九二三年五月,正当父亲准备赴美留学的前夕,一次车祸使他左腿骨折。这使他的出国推迟了一年,并使他的脊椎受到了影响终生的严重损伤。不久,母亲也考取了半官费留学。
一九二四年,他们一同来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父亲入建筑系,母亲则因该系当时不收女生而改入美术学院,但选修的都是建筑系的课程,后来被该系聘为“辅导员”。
一九二七年,父亲获宾州大学建筑系硕士学立,母亲获美术学院学士学位。此后,他们曾一道在一位著名的美国建筑师的事务所里工作过一段时间。不久,父亲转入哈佛大学研究美术史。母亲则到耶鲁大学戏剧学院随贝克教授学舞台美术。据说,她是中国第一位在国外学习舞台美术的学生,可惜她后来只把这作为业余爱好,没有正式从事过舞台美术活动。
一九二八年八月,祖父在国内为父亲联系好到沈阳东北大学创办建筑系,任教授兼系主任。工作要求他立即到职,同时祖父的肾病也日渐严重。为此,父母中断了欧洲之游,取道西伯利亚赶回了国内。本来,祖父也为父亲联系了在清华大学的工作,但后来却力主父亲去沈阳,他在信上说:“(东北)那边建筑事业将来有大发展的机会,比温柔乡的清华园强多了。但现在总比不上在北京舒服……我想有志气的孩子,总应该往吃苦路上走。”父亲和母亲一道在东北大学建筑系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可惜东北严寒的气候损害了母亲的健康。一九二九年一月,祖父在北平不幸病逝。同年八月,我姐姐在沈阳出生。此后不久,母亲年轻时曾一度患过的肺病复发,不得不回到北京,在香山疗养。
北平
香山的双清别墅也许是母亲诗作的发祥之地。她留下来的最早的几首诗都是那时在这里写成的。清静幽深的山林,同大自然的亲近,初次做母亲的快乐,特别是北平朋友们的真挚友情,常使母亲心里充满了宁静的欣悦和温情,也激起了她写诗的灵感。从一九三一年春天,她开始发表自己的诗作。
母亲写作新诗,开始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过徐志摩的影响和启蒙。她同徐志摩的交往,是过去文坛上许多人都知道,却又讹传很多的一段旧事。在我和姐姐长大后,母亲曾经断断续续地同我们讲过他们的往事。母亲同徐是一九二〇年在伦敦结识的。当时徐是外祖父的年轻朋友,一位二十四岁的已婚者,在美国学过两年经济之后,转到剑桥学文学,而母亲则是一个还未脱离旧式大家庭的十六岁的女中学生。据当年曾同徐志摩一道去过林寓的张奚若伯伯多年以后对我们的说法:“你们的妈妈当时留着两条小辫子,差一点把我和志摩叫做叔叔!”因此,当徐志摩以西方式诗人的热情突然对母亲表示倾心的时候,母亲无论在精神上、思想上、还是生活体验上都处在与他完全不能对等的地位上,因此也就不可能产生相应的感情。母亲后来说过,那时,像她这么一个在旧伦理教育熏陶下长大的姑娘,竟会像有人传说地那样去同一个比自己大八、九岁的已婚男子谈恋爱,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不久,母亲回国,他们便分手了。等到一九二二年徐回到国内时,母亲同父亲的关系已经十分亲密,后来又双双出国留学,和徐志摩更没有了直接联系。一九二九年母亲在北平与他重新相聚时,他正处在那样的心境中,而母亲却满怀美好的僮憬,正迈向新的生活。这时的母亲当然早已不是伦敦时代那个留小辫子的女孩,她在各方面都已成熟。徐志摩此时对母亲的感情显然也越过了浪漫的幻想,变得沉着而深化了。母亲告诉过我们,徐志摩那首著名的小诗《偶然》是写给她的,而另一首《你去》,徐也在信中说明是为她而写的,那是他遇难前不久的事。从这前后两首有代表性的诗中,可以体会出他们感情的脉络,比之一般外面的传说,确要崇高许多。
一九三一年四月,父亲看到日本侵略势力在东北日趋猖狂,便愤然辞去了东北大学建筑系的职务,放弃了刚刚在沈阳安下的家,回到了北平,应聘来到朱启钤先生创办的一个私立学术机构,专门研究中国古建筑的“中国营造学社”,并担任了“法式部”主任,母亲也在“学社”中任“校理”。以此为发端,开始了他们的学术生涯。
当时,这个领域在我国学术界几乎还是一未经开拓的荒原。国外几部关于中国建筑史的书,还是日本学者的作品,而且语焉不详,埋没多年的我国宋代建筑家李诫(明仲)的《营造法式》,虽经朱桂老热心重印,但当父母在美国收到祖父寄去的这部古书时,这两个建筑学生却对其中术语视若“天书”,几乎完全不知所云。遍布祖国各地无数的宫殿、庙宇、塔幢、园林,中国自己还不曾根据近代的科学技术观念对它们进行过研究。它们结构上的奥秘,造型和布局上的美学原则,在世界学术界面前,还是一个未解之谜。西方学者对于欧洲古建筑的透彻研究,对每一处实例的精确记录、测绘,对于父亲和母亲来说,是一种启发和激励。留学时代,父亲就曾写信给祖父,表示要写成一部“中国宫室史”,祖父鼓励他说:“这诚然是一件大事。”可见,父亲进入这个领域,并不是一次偶然的选择。
从一九三一到三七年,母亲作为父亲的同事和学术上的密切合作者,曾多次同父亲和其他同事们一道,在河北、山西、山东、浙江等省的广大地区进行古建筑的野外调查和实测。
三十年代是母亲最好的年华,也是她一生中物质生活最优裕的时期,这使得她有条件充分地表现出自己多方面的爱好和才艺。除了古建筑和文学之外,她还做过装帧设计、服装设计;同父亲一道设计了北京大学的女生宿舍,为王府井“仁立地毯公司”门市部设计过民族形式的店面。她还单独设计了北京大学地质馆,据曹禺同志告诉我,母亲还到南开大学帮助他设计过话剧布景,那时他还是个年轻学生。
母亲不爱做家务事,曾在一封信中抱怨说,这些琐事使她觉得浪费了宝贵的生命,而耽误了本应做的一点对于他人,对于读者更有价值的事情。但实际上,她仍是一位热心的主妇,一个温柔的妈妈。三十年代我家坐落在北平东城北总布胡同,是一座有方砖铺地的四合院,里面有个美丽的垂花门,一株海棠,两株马缨花。中式平房中,几件从旧货店里买来的老式家具,一两尊在野外考察中拾到的残破石雕,还有无数的书,体现了父母的艺术趣味和学术追求。当年,我的姑姑、叔叔、舅舅和姨大多数还是青年学生,他们都爱这位长嫂、长姊,每逢假日,这四合院里就充满了年轻人的高谈阔论,笑语喧声,真是热闹非常。
然而,这样的生活,不久就突然地结束了。
一九三七年六月,她和父亲再次深入五台山考察,骑着骡子在荒凉的山道上颠簸,去寻访一处曾见诸敦煌壁画,却久已湮没无闻的古庙——佛光寺。七月初,他们居然在一个偏僻的山村外面找到它,并确证其大殿仍是建于唐代后期(公元八五七年)的原构,也就是当时所知我国尚存的最古老的木构建筑物(新中国成立后,在同一地区曾发现了另一座很小的庙宇,比佛光寺早七十多年)。这一发现在中国建筑史和他们个人的学术生活中的意义,当然是非同小可的。
可惜这竟是他们战前事业的最后一个高潮。七月中旬,当他们从深山中走出时,等着他们的,却是芦沟桥事变的消息!就这样,他们在日军占领北平前夕,抛下了那安逸的生活、舒适的四合院,带着外婆和我们姐弟,几只皮箱,两个铺盖卷,同一批北大、清华的教授们一道,毅然地奔向了那陌生的西南“大后方”,开始了战时半流亡的生活。
昆明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我们在长沙首次接受了战争的洗礼。九死一生地逃过了日寇对长沙的第一次轰炸。
一九三八年一月份,我们终于到达了昆明。在这数千公里的逃难中,做出最大牺牲的是母亲。
三年的昆明生活,是母亲短短一生中作为健康人的最后一个时期。在这里,她开始尝到了战时大后方知识份子生活的艰辛。父亲年轻时车祸受伤的后遗症时时发作,脊椎痛得常不能坐立。母亲也不得不卷起袖子买菜、做饭、洗衣。
大约是在一九三九年冬,由于敌机对昆明的轰炸愈来愈频繁,我们家从城里又迁到了市郊,先是借住在麦地村一所已没有了尼姑的尼姑庵里,院里还常有虔诚的农妇来对着已改为营造学社办公室的娘娘殿烧香还愿;后来,父亲在龙头村一块借来的地皮上请人用未烧制的土坯砖盖了三间小屋。而这竟是两位建筑师一生中为自己设计建造的唯一一所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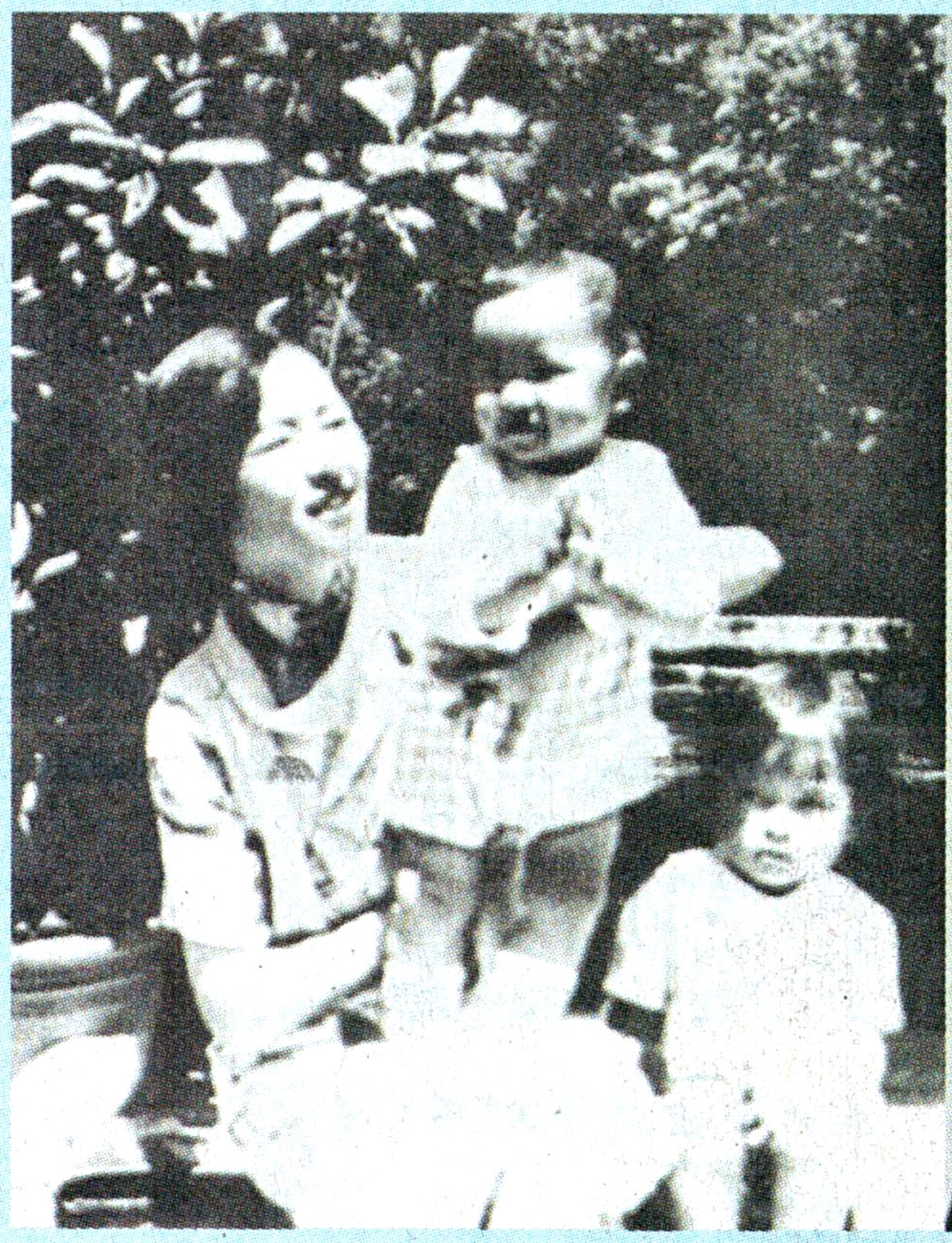
林徽因和她的孩子们(资料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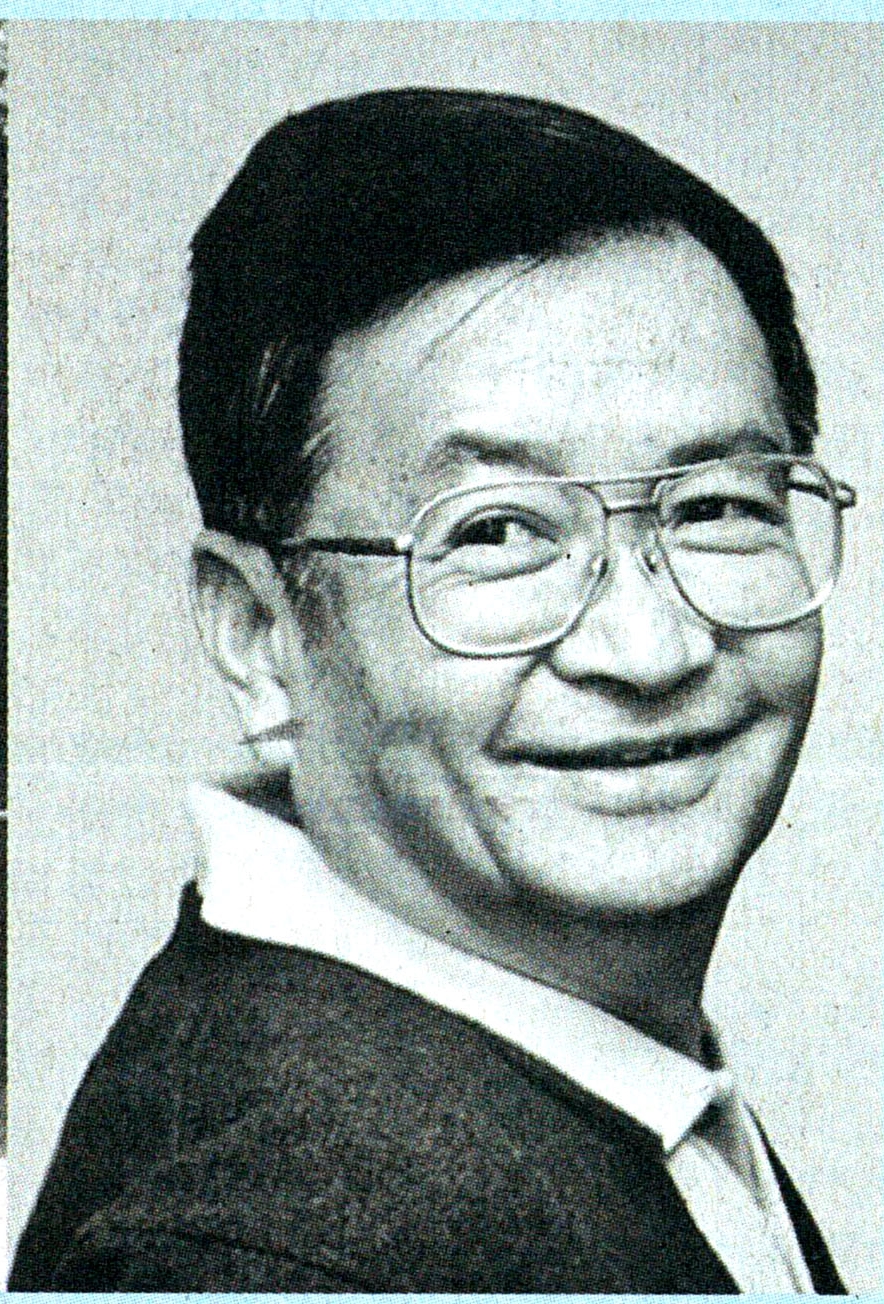
梁从诫(1930—2010)
重回北平
胜利后在北平,母亲的生活有了新的内容。父亲应聘筹建清华大学建筑系,但不久他即到美国去讲学。开办新系的许多工作暂时都落到了母亲这个没有任何名义的病人身上。她几乎就在病床上,为创立建筑系做了大量组织工作,同青年教师们建立了亲密的同事情谊,热心地在学术思想上同他们进行了许多毫无保留的探讨和交流。同时,她也结交了复原后清华、北大的许多文学、外语方面的中青年教师,经常兴致勃勃地同他们在广阔的学术领域中进行讨论。
但是,这几年里,疾病仍在无情地侵蚀着她的生命,肉体正在一步步地辜负着她的精神。她不得不过一种双重的生活:白天,她会见同事、朋友和学生(林洙就是在这段时间内,作为梁林夫妇多年学生助手程应铨的未婚妻,走入他们的世界的),谈工作、谈建筑、谈文学……有时兴高采烈,滔滔不绝,以至自已和别人都忘记了她是个重病人;可是,到了夜里,却又往往整晚不停地咳喘,在床上辗转呻吟,半夜里一次次地吃药、喝水、咳痰……夜深人静,当她这样孤身承受病痛的折磨时,再没有人能帮助她。
一九四七年冬,结核菌侵入了她的一个肾,必须动大手术切除。母亲带着渺茫的希望入了医院。手术虽然成功了,但她整个的健康状况却又恶化了一大步,因为体质太弱,伤口几个月才勉强愈合。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晚上,清华园北面彻夜响起枪炮声。母亲和父亲当时还不知道,这炮击正在预告着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中国人民的生活即将掀开新的一页。
解放军包围北平近两个月,守军龟缩城内,清华园门口张贴了解放军四野十三兵团政治部的布告,要求全体军民对这座最高学府严加保护,不得入内骚扰。同时,从北面开来的民工却源源经过清华校园,把云梯等攻城器材往城郊方向运去。看来,一场攻坚战落在北平城头已难以避免。忧心忡忡的父亲每天站在门口往南眺望,谛听着远处隐隐的炮声,常常自言自语地说:“这下子完了,全都要完了!”然而,就在四八年年底,几位头戴大皮帽子的解放军干部坐着吉普来到我们家,向父亲请教一旦被迫攻城时,哪些文物必须设法保护,要父亲把城里最重要的文物古迹一一标在他们带来的军用地图上……父亲和母亲激动了,“这样的党、这样的军队,值得信赖,值得拥护!”从这件事里,他们朴素地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直到他们各自生命结束,对此始终深信不疑。
解放
解放了。
母亲的病没有起色,但她的精神状态和生活方式,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初期,姐姐参军南下,我进入大学,都不在家。对于母亲那几年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我没有细致地了解。只记得她和父亲突然忙了起来,家里常常来一些新的客人,兴奋地同他们讨论着、筹划着……过去,他们的活动大半限于营造学社和清华建筑系,限于学术圈子,而现在,新政权突然给了他们机会,来参与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实际建设工作,特别是请他们参加并指导北京全市的规划工作。这是新中国成立前做梦也想不到的事。作为建筑师,他们猛然感到实现宏伟抱负,把才能献给祖国、献给人民的时代奇迹般地到来了。对这一切,母亲同父亲一样,兴奋极了。她以主人翁式的激情,恨不能把过去在建筑、文物、美术、教育等等许多领域中积累的知识和多少年的抱负、理想,在一个早晨通通加以实现。只有四十六岁的母亲,病情再重也压不住她那突然迸发出来的工作热情。
母亲有过强烈的解放感。因为新社会确实解放了她,给了她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崇高的社会地位。在旧时代,她虽然也在大学教过书,写过诗,发表过学术文章,也颇有一点名气,但始终只不过是“梁思成太太”,而没有完全独立的社会身份。现在,她被正式聘为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一级教授、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她还当选为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文代会代表……她真正是以林徽因自己的身份来担任社会职务,来为人民服务了。这不能不使她对新的政权、新的社会产生感激之情。“士为知己者用”,她当然要鞠躬尽瘁。
那几年,母亲做的事情很多,我并不全都清楚,但有几件我是多少记得的。
一九五〇年,以父亲为首的一个清华建筑系教师小组,参加了国徽图案的设计工作,母亲是其中一个活跃的成员。为自己的国家设计国徽,这也许是一个美术家所能遇到的最激动人心的课题了。在中国历史上,这也可能是一次空前绝后的机会。她和父亲当时都决心使我们的国徽具有最鲜明的民族特征,不仅要表现革命的内容,还要体现出我们这文明古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一九五〇年六月全国政协讨论国徽图案的大会,母亲曾以设计小组代表的身份列席,亲眼看到全体委员是怎样在毛主席的提议下,起立通过了国徽图案的。为了这个设计,母亲作了很大贡献,在设计过程中,许多新的构思都是她首先提出并勾画成草图的,她也曾多次亲自带着图版,扶病乘车到中南海,向政府领导人汇报、讲解、听取他们的意见……正因为这样,她才会在毛主席宣布国徽图案已经通过时,激动地落了泪。
鞠躬尽瘁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那些年紧张的实际工作中,母亲也没有放松过在古建筑方面的学术研究。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她和父亲以及莫宗江教授一道,在初步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之后,将他们多年来对中国建筑发展史的基本观点,做了一次全面的检讨,并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阶段》这篇长文(载一九五四年第二期《建筑学报》),第一次尝试着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思想,重新回顾从远古直到现代中国建筑发展的整个历程,开始为他们的研究工作探求一个更加科学的理论基础。
在那几年里,母亲还为建筑系研究生开过住宅设计和建筑史方面的专题讲座,每当学生来访,就在床褥之间,“以振奋的心情尽情地为学生讲解,古往今来,对比中外,谑语雄谈,敏思遐想,使初学者思想顿感开扩。学生走后,常气力不支,卧床喘息而不能吐一言”(吴良镛、刘小石:《梁思成文集·序》)。
母亲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所参与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和建造。这里,她和父亲一道,也曾为坚持民族形式问题做过一番艰苦的斗争。母亲在“碑建会”里,不是动口不动手的顾问,而是实干者。
然而,对于母亲来说,这竟是一支未能完成的乐曲。
从一九五四年入秋以后,她的病情开始急剧恶化,完全不能工作了。每天都在床上艰难地咳着、喘着,常常整夜地不能入睡。她的眼睛虽仍然那样深邃,但眼窝却深深地陷了下去,全身瘦得叫人害怕,脸上见不到一点血色。
大约在五五年初,父亲得了重病入院,紧接着母亲也住进了他隔壁的病房。父亲病势稍有好转后,每天都到母亲房中陪伴她,但母亲衰弱得已难于讲话。三月三十一日深夜,母亲忽然用微弱的声音对护士说,她要见一见父亲。护士回答:夜深了,有话明天再谈吧。然而,年仅五十一岁的母亲已经没有力气等待了,就在第二天黎明到来之前,悄然地离开了人间。那最后的几句话,竟没有机会说出。
北京市人民政府把母亲安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决定,把她亲手设计的一方汉白玉花圈刻样移做她的墓碑,墓体则由父亲亲自设计,以最朴实、简洁的造型,体现了他们一生追求的民族形式。
一九五五年,在母亲的追悼会上,她的两个几十年的挚友——哲学教授金岳霖和邓以蜇联名给她写了一副挽联:
一身诗意千寻瀑,
万古人间四月天。 □梁从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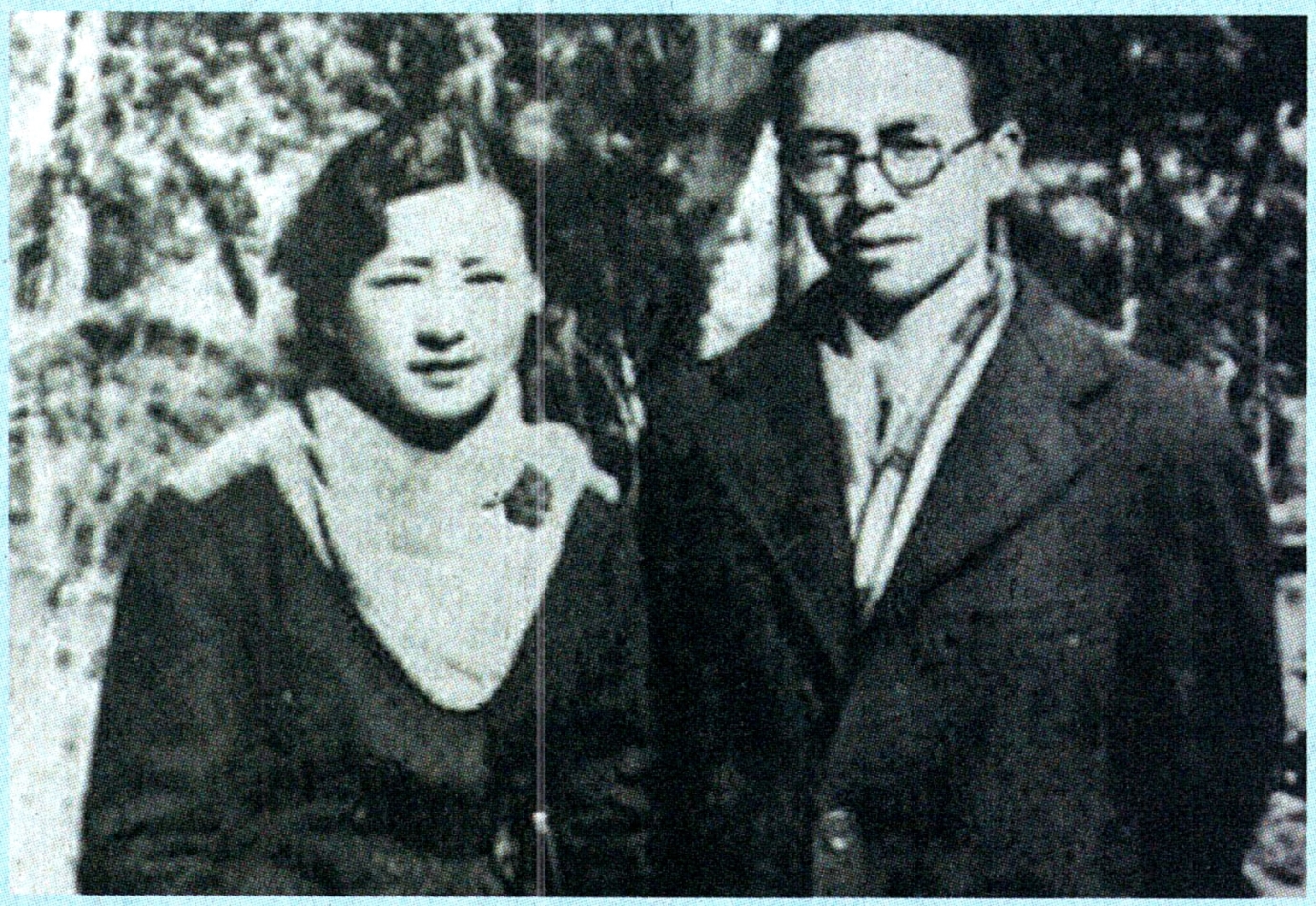
林徽因与梁思成(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