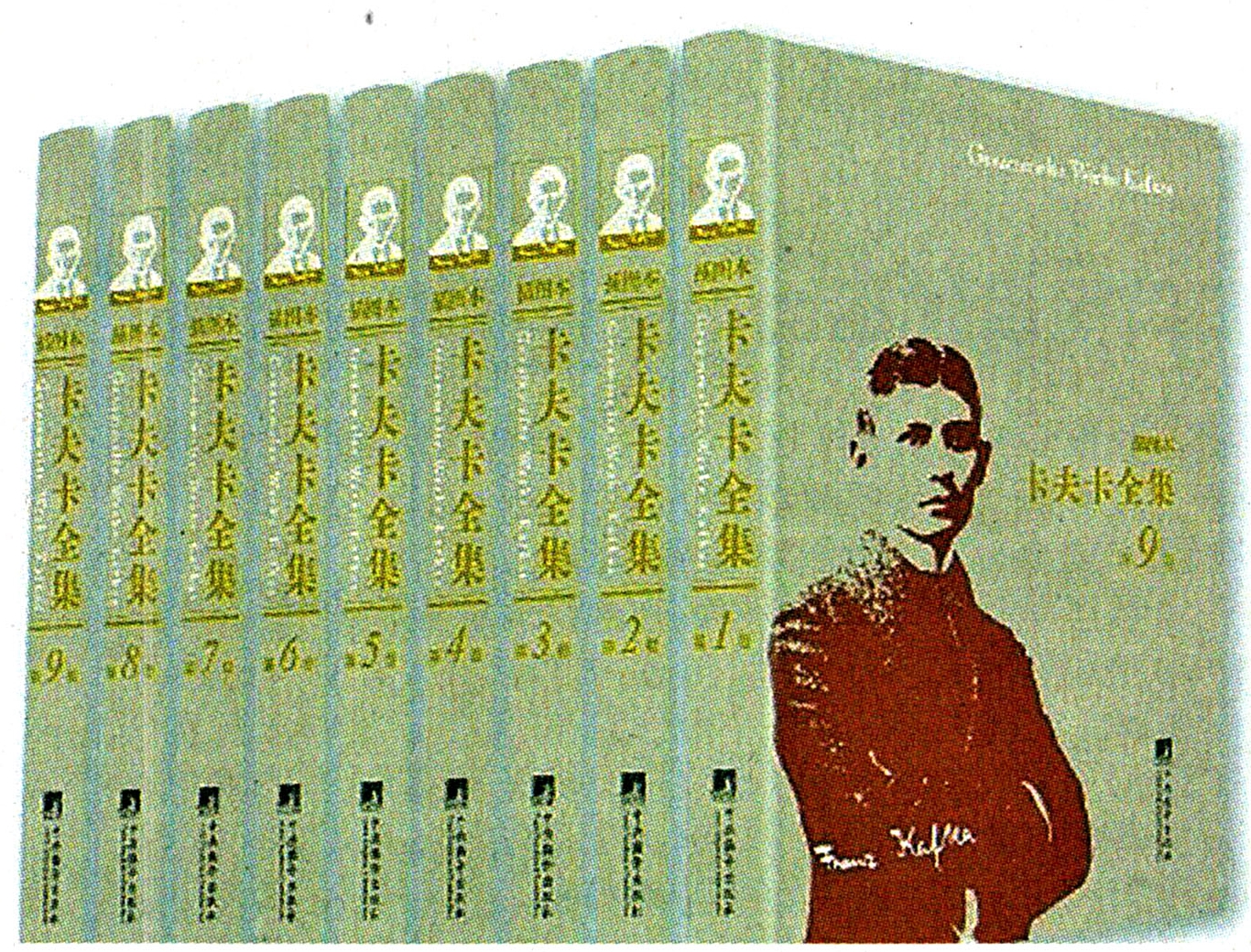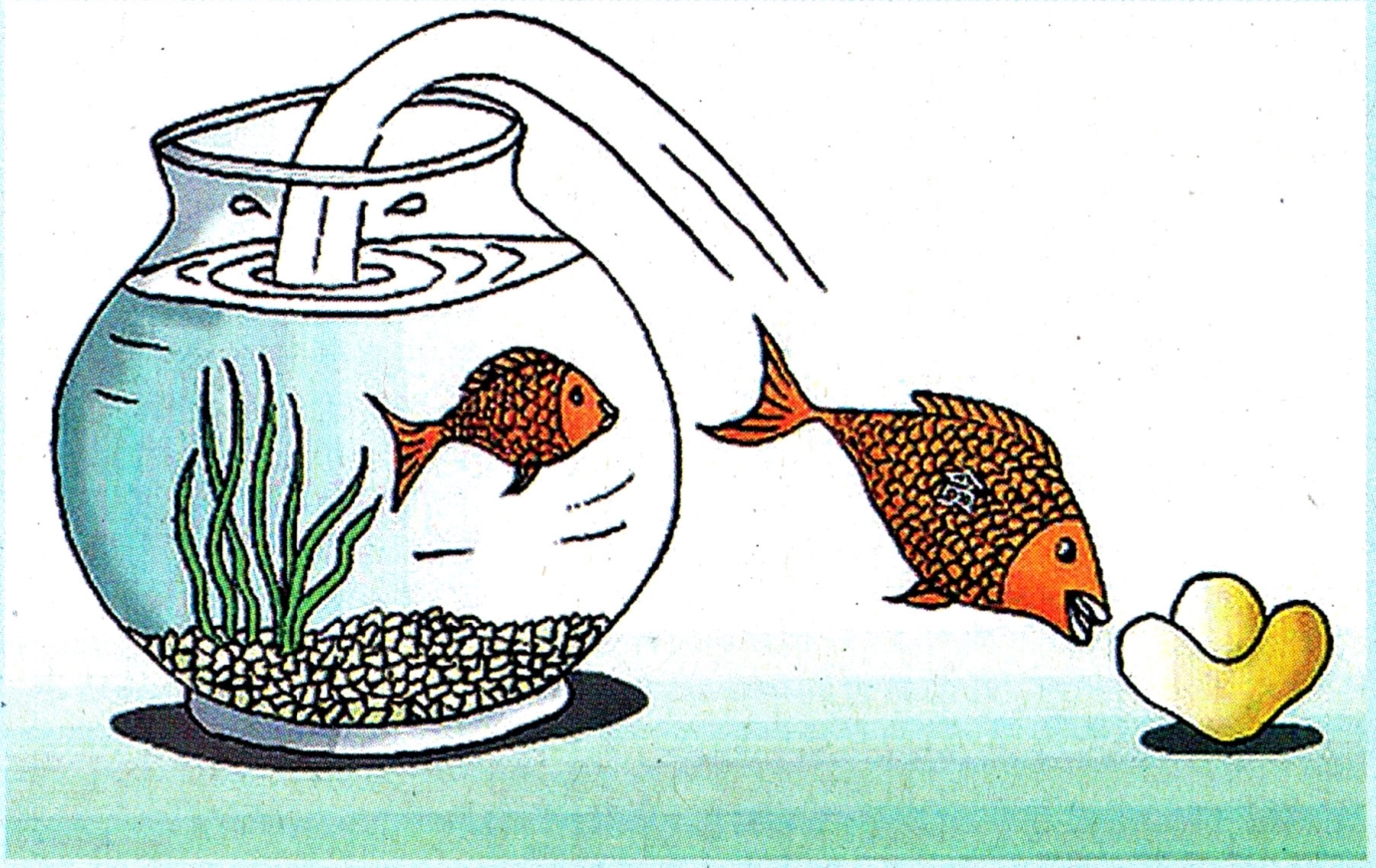编者按
《卡夫卡全集》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全集共9卷,由著名学者、德语翻译家叶廷芳主编,译者有张荣昌、章国锋、赵蓉恒、卢永华、黎奇等,均为德语翻译界有建树的翻译家。此次全集可以看做是之前的河北教育出版社版本的“升级”。
在思想文化领域,每个不同的时代都产生过不同于别的时代的思潮及其代表人物,他们的存在既是时代的见证,又是这个时代精神特征的标志。如果没有了他们,则这个时代的轮廓就会模糊。
卡夫卡也是有资格代表时代,因而有理由载入史册的本世纪杰出人物之一。
卡夫卡的出生地波希米亚王国首府布拉格,历来是欧洲有名的大都市之一,当时约有80万人口,五分之一讲德语。卡夫卡属于犹太血统。这个民族长期没有固定的家园,历来是受歧视的,这给卡夫卡的心灵从小就罩上了阴影。无家可归的漂泊感是他精神结构的重要构成部分,成为他创作内发力的重要来源,因而增加了他作品的思想内涵的丰富性和深邃性。
卡夫卡的大学时代上的是布拉格的德语大学,学的是法律,但他的兴趣是文学,爱读斯宾诺莎、黑贝尔(戏剧学)、达尔文、尼采等人的作品,并开始习作。他的最早一本集子《观察》中的作品约于1902年即已写成。
卡夫卡的成功,首先应归因于他的时代意识,奥匈帝国的专制主义统治与欧洲现代潮流的悖逆,犹太民族的无家可归与受歧视、受压抑的处境,父亲的家长制威权从小对他儿童心理的威胁,社会上法制形式的完整性与法的实质的不存在……这一切都导致他对这个世界的陌生感和异己感,因而无法接受这个世界。于是,现代哲学家们对现代社会从理论上概括出来的“异化”概念,他却用生命做了体验和证实。一种对人类生存的危机感充溢在他的心头,他的内心因此成了一个“庞大的世界”,借助文学手段将它宣泄出来,成了他“巨大的幸福”,否则就要“绽破”。卡夫卡就这样走上了文学的道路。但与其说他想要当作家,毋宁说他为了内心表达。
在《城堡》的另一个稿本的头一章里,主人公K在一家旅馆要求一位女招待帮助他,说他要完成一件紧要任务,为此他必须把其他一切不利于这一任务完成的东西“都要残酷地镇压下去”。
这个紧要任务就是前面提及的,他要把世界“重新审察一遍”。这可以说是卡夫卡的终身使命,是他创作的总宗旨。自从他在文学上初露锋芒(1912年),直到去世,始终都在身体力行。时间对他是最宝贵的,工伤保险公司的那个饭碗成为他最大的苦恼,他曾要求父亲资助他两年,以便暂时离开这个职业,以专心于创作,可惜为商的父亲没有这个眼光,未予答应。他只能利用一切业余时间,为此他恨不得弃绝一切与亲友的往来和社交活动,躲在一个地下室的角落里,除了吃饭,都用来写作。他睡眠很糟糕,失眠还得写作,常忍着头痛。他不愧是个“多情的种子”,先后爱过好几个女子。他也渴望有个家庭,有孩子,为此先后和两位姑娘订过三次婚,但最后都解约了!除了最后一次迫于父亲的反对,前两次都是自己考虑的结果。为什么?笔者研究过他的日记,根本原因还是为了文学。他把写作视为“最大的幸福”,实际上他把最大的爱献给文学了,他和文学结下了“姻缘”,有排他性了。一切有碍于这一“姻缘”的,都要受到“残酷的镇压”。“残酷”,这里是痛苦的代词。和菲莉斯的马拉松式的“结婚准备”扯拉了5年之久,婚约订了又吹,吹了又订,说明他是多么矛盾,这个决心是多么难下,最后还是吹了,是经过多长的精神折磨的结果!不难想像,这个“残酷”的决定,使他付出了健康的代价;他自己最清楚,“肺病是菲莉斯”,是“镇压”婚姻欲望造成的后果。
问题不仅在于他如何地挚爱文学,还在于他对文学要求之高。晚年毁稿之念的原因之一,就是这种要求的反映。这一点他通过晚年的两篇重要小说,即《饥饿艺术家》和《歌女约瑟芬》表达得尤为强烈而清楚:前者主人公为了使自己的艺术达到“最高境界”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后者主人公为了在艺术上“拿到最高处的桂冠”,把身上不利于自己歌唱(即艺术)的一切都“榨干”了,以致一阵风吹来都能把她吹倒。这是卡夫卡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这位现代艺术的探险者,仿佛上天降大任于斯,为了文学,他把“一切生之欢乐”都搭上了!这是一个艺术殉难者的形象,41岁的天年为他作了证。过去我们只知道,出于革命信念有人赴汤蹈火;为了科学实验有人不顾安危;自从有了卡夫卡我们也可以有把握地说:在艺术革新领域也有人为之献身!
卡夫卡也许确实不能像巴尔扎克那样能够“粉碎一切障碍”,但他在实现自己目标的“专线”上可以说是把“一切障碍”给粉碎了!过程当然是残酷的,代价是巨大的:实际上他把生命价值的一半交给了魔鬼,以成全他另一半的成功。也可以说他为了“灵”的完美,作出了“肉”的牺牲。 □叶廷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