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彦修(资料图)
南方日报第一任社长、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出版家、杂文家曾彦修离世数月,其子曾小凉撰文,从家人角度回忆深受人爱戴的老一辈学者。
我出生在北京,因为爸爸的自划右派,1960(也许是1961年)我们全家被迫南迁至上海。过不多久,父母也离异了,留下我们父子二人,父亲的政治生命、工作、婚姻、家庭生活都跌入谷底,可想而知日子有多难过,那时我才6岁左右吧。
但我爸爸可不是那么容易被击倒的。在延安学的手艺这时都用上了:气候进入秋冬,天气日渐寒冷,可是爸爸不怕,把旧毛衣、毛裤拆了,洗净,再买些毛线,在炉子上架上铝锅,用一毛钱一包的染料将毛线染成藏青色,接着教我缠绕毛线团,起针、编织。毛线团缠得周周正正,线是从中间抽出来的。今天的人是很难想象了,当年一大一小两个人的毛衣、毛裤、毛线袜、毛线手套都是一大一小两个男人编织出来的。花色当然不谈了,平针而已,但收针、放针确是操作自如。这门手艺今天虽然用不上了,但是我还是要感谢我亲爱的爸爸。
我从小就喜欢唱歌,但唱得没腔没调的。让我记忆深刻的是,当爸爸高兴时,他就平躺在床上,两条腿收起让我坐在他的膝盖上,教我唱歌,他教了我不少延安时期的老歌,如“追兵来了何奈何,我像小鸟儿回不了窝,回不了窝”、“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黄河大合唱的大部分曲目都是那时学会的)、“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哪里去了”、《渔光曲》、《大刀进行曲》、《松花江上》,太多太多了,都是那个时期(7~10岁间)学会的。爸爸的嗓音并不怎样,可他还是教我怎样用美声发声。直到今天,唱歌还是我最大的爱好。感谢您,我挚爱的爸爸。
那次暴打,是他对我最感后悔的事
接下来的回忆现在想起,还是有点害怕,那就是棍棒教育。当年的孩子挨父母揍那可是家常便饭。从还没有进入小学时,爸爸就教我练习毛笔字,规定了一天要写多少,他每天晚上下班回来要检查的。写得好的就用红笔画圈,以至于在字的某一个局部画圈,再写得好一点的加上一两句表扬,会使一个孩子心花怒放。但我一个小孩儿哪安得下心思写毛笔字呢,所以偷奸耍滑是常有的事。记得有一次已经是大冬天,晚上爸爸还没回来我就睡下了。谁知爸爸进门后看到我敷衍了事的作品,那叫一个气冲脑门啊,把已经在热被窝里呼呼大睡的我提小鸡似的从床上捉起,套上棉毛衫裤,让我把手心伸出来(为了不让我缩回去,还捉住我的手),抓着戒尺就打下来了。接着爸爸亲自给我研墨,之后他去睡了,我抖抖索索地继续写字,写好后唤醒他,再经过他批改后才去睡觉。
当年我的住家应该算是城市边缘。三年“自然灾害”来了,当时家里还养了一两只鸡,这喂鸡、晚上圈鸡的活当然是我的了。鸡食是用带鱼的嘴、肚肠,还有细得像韭菜似的鱼尾搅合在一起煮出来的。我拿去喂鸡,我一个小孩,饿啊,面对这鸡食,唯一的感觉就是香,于是不由分说自己就捞起吃了。邻居看见就告诉了我爸,可能是让家长丢了面子吧,那一顿揍可是把我打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这顿打也是爸爸年老以后对我最后悔的一件事,爸爸说起来就老泪纵横,说那是一个饿急了的小孩,怎么可以那样打呢。我记得好像在哪本刊物上爸爸还专门记述了这事。这就是我的老爸,一个严厉的老爸。
那种讨酒喝的表情让人忍俊不禁
同样因为这“自然灾害”,人们都极度缺少油水,更何况我们这些只知道要吃的孩子。偶尔爸爸不知从哪里买来了绵羊尾,那可是纯粹的脂肪啊。切成小块,放上胡萝卜再加一些咖喱,炖出来的香味绝对不止让人垂涎三尺。这时爸爸会让家里的阿姨(佣工)去把姐姐和小妹接来(那时姐姐和妹妹都跟妈妈一起生活了),一起享用这“天下第一美食”。当时的那种幸福感,今天无论吃什么都无法感受到了
川菜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四川人无论贵贱,个个都是美食家,我老爸也不例外,但他同时还是一个做川菜的好手。1964至1965年近两年里,生活日渐好转,当年在上海时他自己的拿手好菜是回锅肉、鱼香肉丝、白切鸡、蒜泥白肉,后来他还在家里做起了牛肉干、香肠。他做的四川泡菜更是一绝。他喜欢一些西式的东西,会做一道非常经典的俄罗斯菜,还会自己做橘子果酱、菠萝酱,把面包烤一下再涂上点牛油、果酱,是他的最爱。
爸爸还有一个伴随终身的爱好:喜欢喝一点酒,而且是烈性的白酒。听爸爸自己说,上世纪50年代早期,他在广州工作,当时战争刚结束不久,南方有很多援华的苏联军事专家,这些专家都是好酒之徒。每当有重大节日,叶帅(叶剑英当时在南方主持工作)会设宴招待这些专家,爸爸本来就会喝酒,30多岁时正是好酒量,被叶帅招呼来陪酒那是正中下怀。
在上海工作的17年间,他也没断了酒(就是当年下干校回来休假时也还偷偷带些酒去),平时就喝1.1元一斤60多度的烧酒。每每喝时先用杯子倒上少许,用火柴点着,这场景似乎给他带来了极大的乐趣。菜呢,炸花生米是奢侈品,是过年才有的配给,没有的时候就用毛豆代之,把毛豆煮了再晒干那叫一个香啊。我作为老爸的陪酒也在这样的熏陶下慢慢学会了喝酒。
我到北京工作时老爸已经90出头,但还是每顿必酒(主要是晚饭时),但慢慢由高度酒改成了红酒(低度白酒老爸是不喝的,说那根本就不叫酒),又慢慢改成了啤酒,无论什么酒老爸都要冰镇过了才喝,有时还要加上冰块。有一次啤酒喝完没来得及买,晚饭时桌上没酒,老爸居然像小孩一样腼腆地说:“今天还有酒吗?”那种讨酒喝的表情现在想起来还让人忍俊不禁。
2014年夏我爱人和孩子从新加坡回京,一家人晚饭说说话,喝着冰镇啤酒,老爸脸上明显地洋溢着幸福感,笑容灿烂,露出一口洁白的假牙。这就是我的老爸,一个美食家的老爸。
他流着泪说,怕这个家散了
我在上海长大,学习、就业、成家均在上海,1991年有了儿子。当老爸得知他有孙子了,那叫一个高兴,问我想怎么给孩子起名字,我说还没想好呢,他马上回应说由他来起名字中的一个字吧。老爸讲起一个他极其佩服的人,也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王尽美。他说想用“王尽美”中间一个字,再加一个草字头,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意思,老爸问我同意不同意。这还用说,我当然同意啦。名字后面的一个字老爸让我起,当然后来是我母亲起的,那是后话。
现在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照片是不会少的,我的儿子也一样。当爷爷看到孙子的照片后大为惊讶,说这小东西长得太漂亮了,太像我小时候了。这时的老爸一点也不谦虚,眉开眼笑的。巧合的是我老爸属羊,我属羊,这小孙子还是属羊。
我们一家常年生活在上海,儿子10岁时和我爱人去了新加坡。在将去未去时,爸爸有很多顾虑,他劝我要三思而行,他甚至还流着泪对我说:成个家不容易,我怕这个家就此散了。
2012年,当爸爸得知孙子高中毕业后考上新加坡最好的大学,并马上要去当兵两年时,他说现在的孩子都娇生惯养,是应该锻炼锻炼,应该知道纪律是怎么回事。同时又说孙子长大成人了,应该帮助妈妈,为妈妈分担一些担子了。为此他还专门给孙子去了一封信,教育孩子要爱妈妈。这就是我的老爸,一个没有含饴弄孙,却一直在关心着孙子的老爸。
他早就填写了捐献遗体志愿书
因为他常年写作,我们的日常交流不算很多,吃晚饭算是我们的交流时间。他对时事政治是非常关心的,尤其是世界政治和台湾政治。每天晚饭时他都要问我网上又有什么新鲜事,他把当年的萨达姆和卡扎菲归类为独裁者、恶魔和混蛋,对俄罗斯普京的强硬表示赞赏。对美国的奥巴马、女强人希拉里都非常关心,说希拉里作为一个女人快70了还能够当总统吗?她有这个精力吗?说她一旦当了总统对中国来说可不是一个好消息。近一年来对ISIS的残暴做法表示深恶痛绝,后来听我说起ISIS又有新暴行时,老人都不让我说具体内容。
作为一个愿意把自己的全部奉献给社会的老人,早在七年前爸爸就填写了捐献遗体的志愿书,并嘱咐子女要同意。他说:“我老了,全身都是病了,高血压伴随了我一生,现在肾动脉又狭窄、硬化了,我这样的身体将来或许对研究老年病会有些帮助。”作为子女,我们只有尊重他的选择。
老爸走了,走向远方,他去寻找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去了。老爸,姐姐、小凉和许燕、小妹和建新(妹夫)都目送着您。老爸,走好!
□曾小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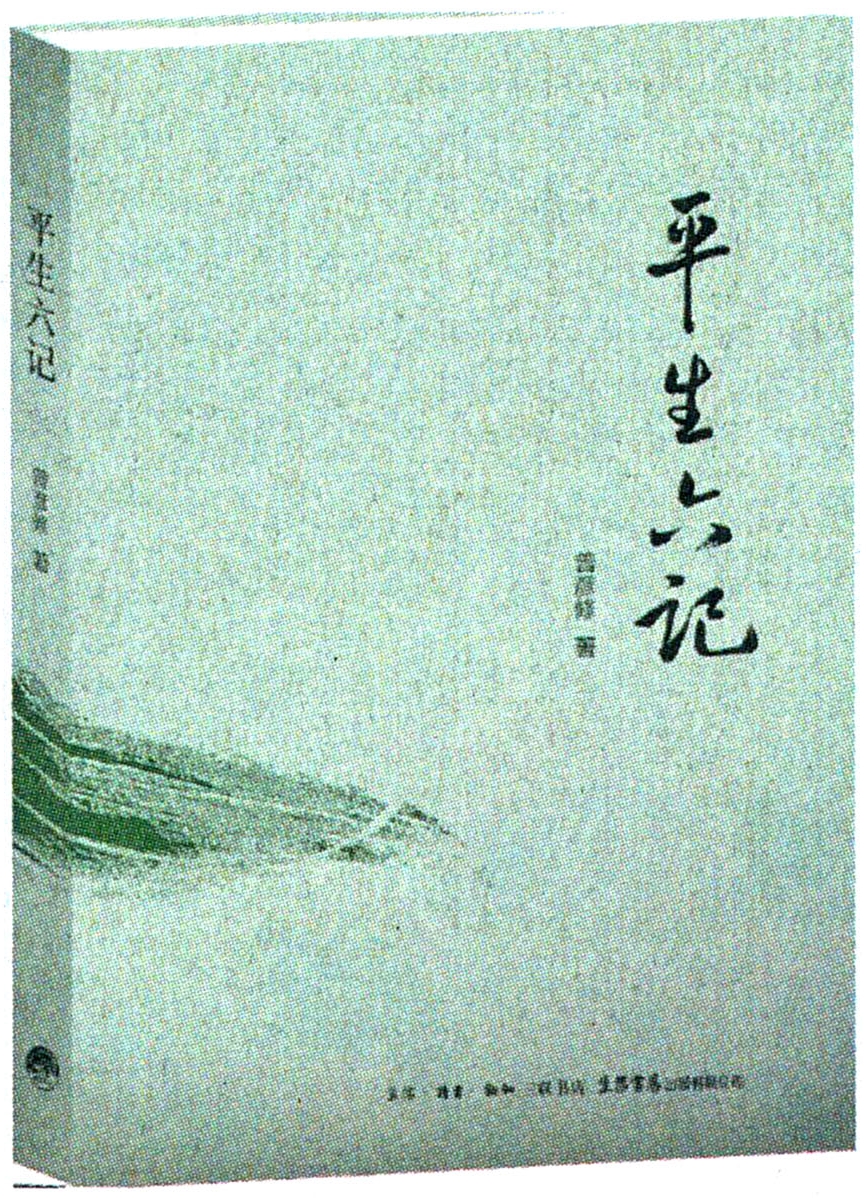
曾彦修著作(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