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与变革》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和赖肖尔合力撰就的有关中国历史的专著。全书贯通古今,包容中国古代传统社会的演变、近代西方势力的渗入后传统社会变革两部分内容。书中着重于从史实的叙述中探讨一些富有启示的理论问题,从比较史学的角度研究中国历史,将同一时期的中国与西方国家互作比较,由此归纳出中国社会发展的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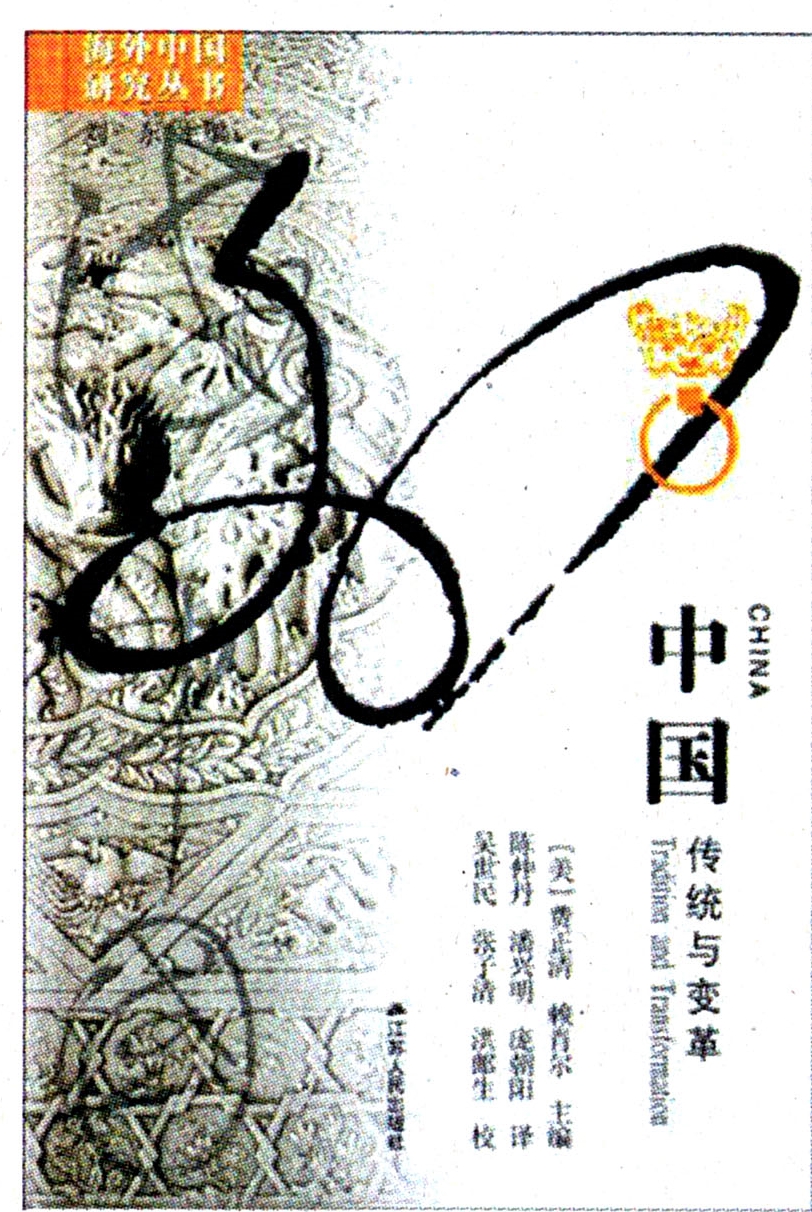
费正清对中国的认识,恰巧在“傲慢”与“偏见”这两种立场之间,没有傲慢,不带偏见。他提出的“冲击——回应”模式,与自己多年对中国的实际感受密不可分。作为来自美国的中国研究者,他眼中的中国和美国一样富有生命力,但在发展上,又与他所见过的欧美世界不同。在他的学术生涯早期,对中国最早的几个通商口岸的研究是他选定的博士论文题目,这个题目可能会成为他解释现代中国诞生的突破口。他也确实是这么做的。1934年到1935年,他接触到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被西方强行开辟的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这几个通商城市的早期档案,在其中发现了自由贸易背后巧取豪夺的历史,又进而在日常生活中见识了和档案记载几乎如出一辙的现象,并对通商城市里中国人的生活与社会阶层问题有所了解。于是,他将问题聚焦在早期的通商口岸上,从贸易与外交的角度去理解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并试图对西方在其中的作用做出评估。这种研究思路,可以视为费正清理论的基础。
然而,只有这样的思路是远远不够的。另外,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思考也并非他计划中的研究题目,他之所以会关注这个宏观的问题,完全缘于他的在华经历,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一些非常偶然的事件。
1933年,在他第二次申请哈佛燕京学社的研究资助失败之后,生计问题成为他必须面对的难题。要在中国继续生活并进行研究,就必须有一笔固定的资金,但显然,他并没有这样一笔可以使用的现成资金。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也许更重要的是,没有了坐享其成的补贴后,威尔玛和我需要在北京开始谋生。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更多地接触到中国人的生活,而这是语言老师所无法提供的。”(《回忆录》第100页)
生活的需要,让他能够深入了解中国的社会,而在充分的了解之后,他的研究获得了意外的灵感。他开始将中国本身而非中国问题作为自己的关注对象,在各个时期写下的文字中,他对中国现实状况的关心甚至超过了对自己研究课题的关注。作为一个美国人,他和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对农村发展、社会各阶层的关系、政府组织及其政策、国共之争等话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生活的缘故,他深入了解了中国,因为了解,他对中国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作为一个美国人,他对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从美国的立场上去理解中国,不自觉地将西方社会的一些标准带入到了他解释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研究中去。因而,他的立场与他选取的评价标准,也就具有了柯文所批评的“西方中心论”的特征。
严格来说,作为中国学研究的外国学者,没有人能够完全放弃自己原本的思维方式与文化立场,绝对客观地去观察中国,费正清的问题也不在此。他所提出的“冲击——回应”学说,设定了一个极度稳定的中国传统的存在,认为促使其发生变化的,是十九世纪以来西方的冲击,而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发生的一切变化,都是对西方冲击的回应。如此概括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必然存在很多漏洞,比如中国是否存在一个整体性的传统,传统是否就稳定到无法出现自身的变革,冲击究竟对中国产生多大影响,冲击是否一定会带来中国的变革,等等。不过,在美国中国学建立初期,这样的理论模式从整体上解释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问题,并将其与西方现代社会联系起来,直至今日,虽然美国中国学研究已经进入全新阶段,但还没有出现在整体解释上能够完全取代这一学说的新框架。
费正清对中国在西方的“冲击”下产生变革作为“回应”的描述,与其说是对中国现代化过程的解释,不如说是从现实出发的一种历史假设,以及对中国未来的一种期望。在中国的生活经历,让他对这个古老的大国产生了虔诚的热爱。正因如此,他才会参与到美国对华政策的讨论,并试图用自己的专业研究去影响政策的制定者,让他们推动中国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在费正清身上,学术也好,政治也好,他的选择总是与中国有关。如果说他有一个确定的志业,那就应该是中国。
因为他深爱中国,所以在讨论美国的对华政策时,他强调政策的选择要把中国的利益作为重要的参考指标,并认为这样才能真正保证美国的国家利益。他说:“最终,我明白了一个重要的道理,如果想从中国方面有所收获,就必须有所付出。这是最简单古老的互惠思想。”(《回忆录》第205页)
在回忆录中,他并未直白地表露自己对中国的爱,但在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这种挚爱。他写到过对二战期间和二战后国民党治下的国民政府的失望,写到过同时被海峡两岸误解的委屈与伤感,也写到过在卡特总统举办的晚宴上没有和邓小平进行中国式的怀旧与聚会觉得遗憾,这一切细节的描述里,都含着一个欲言又止的“爱”字。 □张耐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