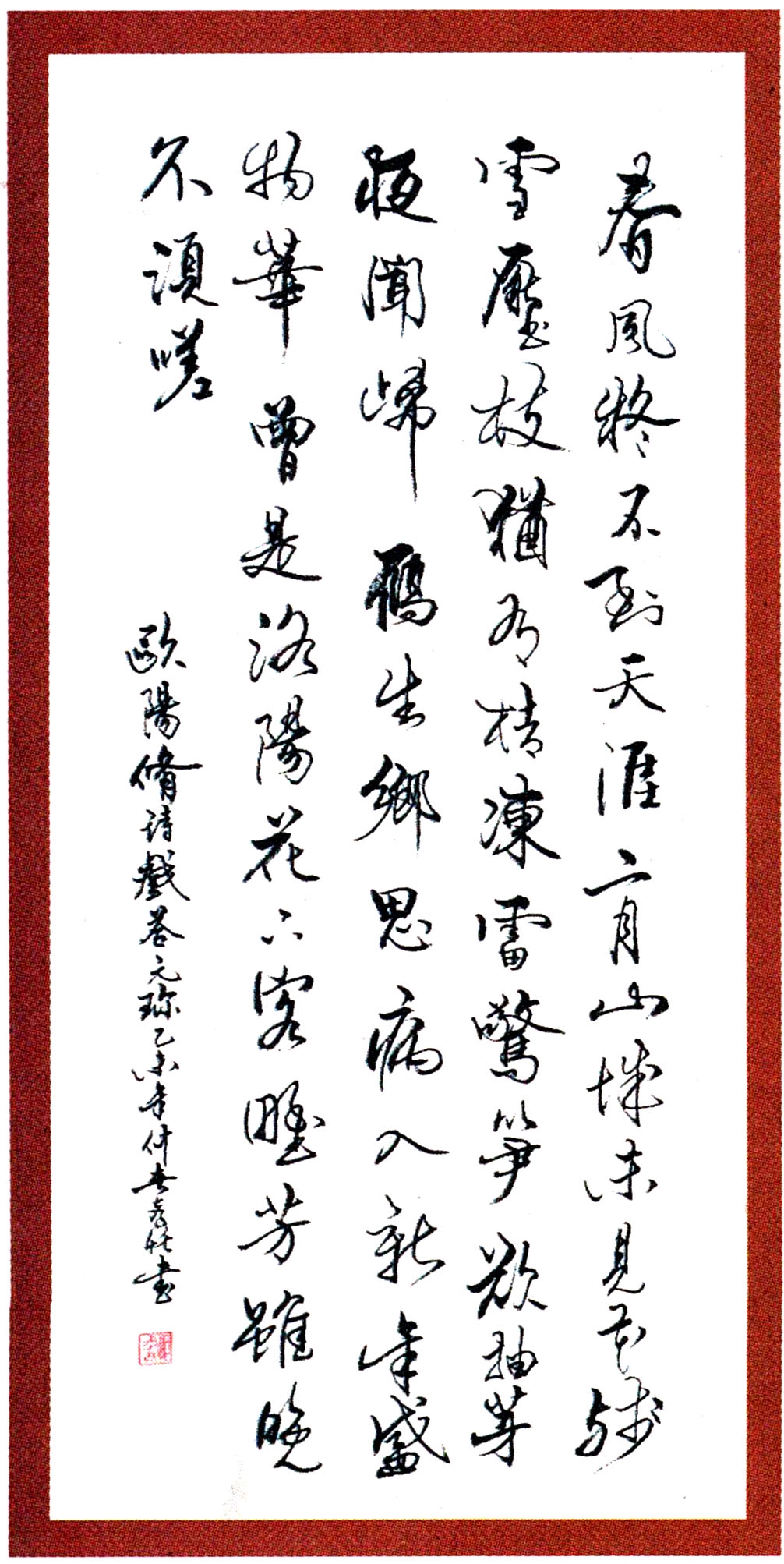□田利祥
如果我是一辆前后驱动的跑车,故乡和母亲便是车之四轮;如果我是一只空中飞翔的小鸟,故乡和母亲便是我的两翼。
母亲是一条浅浅的河流,渴了,我俯下身子嘬上一小口;乏了,我用双手把水搓在脸上,使自己重新振作起来。从童年到成年,面容由稚嫩变为饱经风霜,我经常利用清澈的河水映照一下自己,虽然时光流逝,我依然没有迷失自我。
故乡是母亲的白发,是母亲的泪水。当我第一次离家,要长时间地远行,母亲站在风地里,额前的白发摇曳着,我没敢回头,不忍看到她的泪水模糊着。多少年来,那摇曳的白发,总在我眼前萦绕,不时在向我指点着;那模糊的泪水,一年四季滋润着我,使我从来不曾干枯过。
故乡是我头顶烈日不停地捡起掉落在田间的麦穗,是数九寒天我把棉袄一裹,再在外边系一条腰带、双手抄在袖子里,缩成一团,踏着白雪,冒着凛冽的寒风到学校去上早自习。多年以后,我对我所教的农村学生总要多看一眼,我似乎从他们当中看到了我儿时的影子。
故乡是一群小伙伴,我们曾经和猪牛挤在一方水塘里学游泳,我们也曾口角,偶尔还抱在一起互相撕打。长大成人,各奔前程,见面老远先叫乳名,热烈拥抱,嘘寒问暖。我知道,他们都是我行驶的航标,都是我前进中的助推器。
故乡是我出生的老屋。印象中的老屋是那样巍峨,那门,那窗,那瓦,那屋脊兽,仿佛是一座宫殿,尤其是它总被温暖的阳光笼罩着。
故乡是那长长的街道,早晨太阳从笔直的街道那一头升起,傍晚从另一端落下;我们的祖宅坐北朝南,出得大门,左东右西。每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定位的方法不是老师教的“上北下南左西右东”,我觉得用我们的街道和我们的祖宅定位更加直观、方便,易记易行,方寸不乱。
上哈尔滨,下三亚,往乌鲁木齐,到舟山群岛,无论搭火车,还是乘飞机,无论是去,还是回,坐在交通工具上,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这是离我的故乡更远了,还是更近了呢?哦,原来我始终把自己行动的轨迹放在一个坐标上,原点就是我的故乡。我被我的故乡环抱着,我被我的故乡注视着,不言不语的故乡在我的血液里流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