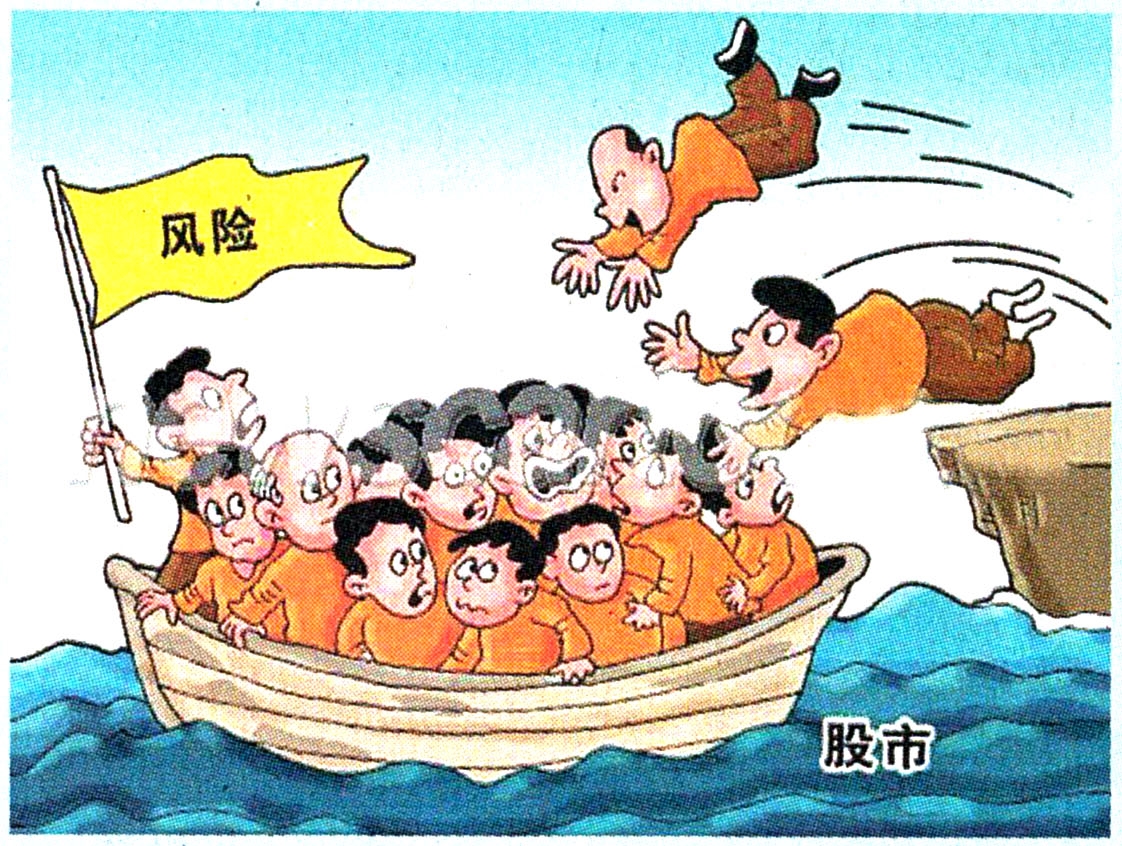在热情勃发的六月,乡党赵凯云捧着他的诗集《豳州书》来了。这让我想起,三四年前他给我赠送诗集《颤栗的时光》时的情景来。那是将近年末的一个日子,黑云飞渡,天空满是阴霾,他来了,一本异形书——《颤栗的时光》就以这种别样的方式出现在了我的眼前。说实话,这是一个诗歌和诗歌创作渐趋式微的年代,只剩下了一些尚在读诗的人,在这样一种现实语境里,赵凯云仍然意气风发、诗意勃勃地经营着诗歌的梦想,无疑是令人惊讶和敬佩的!
如果说,《颤栗的时光》是对已逝青春岁月的深情祭奠,对短暂、炽热、憧憬、迷茫、激情……的青春时光的痴情回望和心理救赎,那么,《豳州书》则是对生养诗人的故乡——彬县——这一方皇天后土的沉重叹息和激情赞叹,是唱给后工业化时代的故乡的一曲赞歌。无论社会怎么发展变革,世界怎么变化突进,唯一不变的是诗人一颗明净、纯洁、善良的心,对故乡过往农耕文明的深切眷恋,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亲人的仰望和钦敬,对故乡在推进工业化过程里产生的问题的困惑以及由此而来的跨越转型发展的探寻和期待,令人回味,令人咀嚼。在故乡,在古豳大地,诗人的双脚大步流星地踏遍了山山水水、沟沟峁峁,掬一捧故乡清冽的河水,嚼一口故乡甜美的野菜,与田间地头耕作的男女闲聊,与留守村居的老人孩子拉家常,与矿山井下的工人师傅们交心问询……件件桩桩,都浸透着他的思考和批判,注视与探寻。农耕文明的厚重和发达,工业经济的高歌猛进,因此而催生的农民工的迁徙,城镇化的建设,留守村庄的空虚,小学校园学生的日渐减少等等现象,使诗人迷茫、彷徨,也促使他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去反思、去叩问、去追寻,在他的笔下没有花前月下、掬水弄月式的浅薄,却实实在在地多了思索、多了拷问、多了人性的厚重、深沉和苍凉,这种超然直视现实之上的献身精神,支撑着他对生命以及人的终极意义的探寻,也保持着他一以贯之的警醒、冷静、坚韧和智慧。
赵凯云是从农家走出去的,他远离山村,远离村庄,在繁华的大城市西安有了他的职业,收获了他的爱情和女人,他本可以安安稳稳地赚钱、工作、享受生活,但是他不甘心,不甘心平庸、不甘心放弃和世界对话,他把善良、宽容、任劳任怨的农民特有的品质带进了城市,在工作间隙,他回望故乡,眺望故乡,以一颗诗心,为故乡的每一步变化和进步鼓劲呐喊。
在煌煌70万言的《豳州书》中,作者深情地叙说,通古达今,穿越历史,穿透烟霞薄雾,在对往事的追忆和现实的歌咏中,完成了对故乡的回望和吟唱。姜嫄、后稷、公刘、苻坚、公孙贺、范仲淹……这些历史人物,在古与今两个时空里风云际会,展现了四千年农业文明的辉煌,也写出了后世子孙对先民祖先的万世敬仰。侍郎湖、程家川、龟蛇山、七星台、隘巷朝烟、履坪春草……每一处山水古迹,每一个历史遗存,都回响着赵凯云留下的足音。他深入故乡故土,不慕虚华,接地气,听乡音,在无限靠近中书写着对故乡的大爱大情。故乡的容颜正在日新月异,尽管发展中的阵痛是明显的,但赵凯云面对故乡,并没有怨怼,也没有失望,而是理性分析,自觉反省,站在发展的高度,在历史的长河里,故乡始终是生长着的,是欣欣向荣的。拂去岁月的尘埃和历史的烟岚,故乡日渐靓丽和清晰,矗立在诗人的心中。
“为什么我的眼里满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艾青的这句诗或许正能揭开青年诗人赵凯云书写《豳州书》的谜底。在诗歌的路途上,赵凯云走出的是自己的一条路。木心说,你爱文学,最终,文学也会爱你的。我欣喜地期待着,赵凯云的《豳州书》赢得属于他的那一份荣光。
□胡忠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