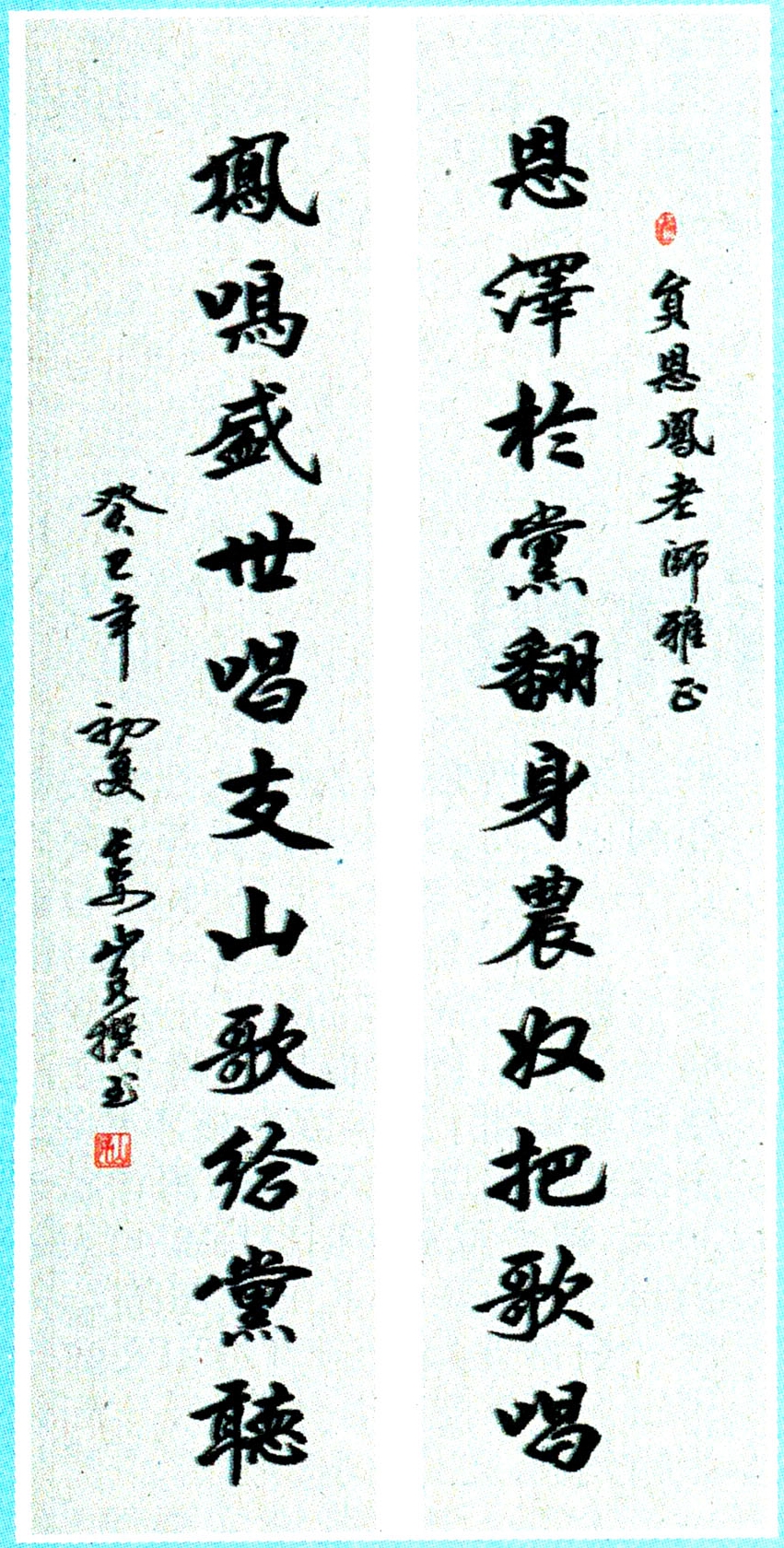□李思纯
意大利有一道著名的甜点叫提拉米苏。
相传,一位美丽的意大利女孩在得知她的爱人即将奔赴战场时,把家里仅有的几样食材——马斯喀邦尼奶酪、意式咖啡、手指饼干和朗姆酒组合起来制成甜点,她把它称作“提拉米苏”,意为“带我走、想起我了吗”,以此送别她的爱人并祝愿他赢得战争的胜利。
动人的传说造就了这一道甜点的辉煌,虽然它只是众多意大利著名甜品中的一份子,但因为它与生俱来的内涵直指情意的珍贵和家庭的温暖,所以一经流传,那充满宠溺、甜美的味道立刻就勾起了所有人内心的温情。
这不禁让人想起去年央视热播的《舌尖上的中国》,一部以时令季节和地域生活特征贯穿饮食文化主线的华夏传统美食记录片,或许因为平常,或许因为乡土,一经热播,立刻风靡全国。记录片以唯美的画面、诗意的解说诠释了日常饮食与人类的劳动、生命的繁衍、自然的发展之间无法分割的关系,让日渐在琐碎生活中变得感官迟钝和心灵麻木的人们陡增了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向往与珍惜。人人都好像刚刚清醒过来:哦,原来我们的饮食还有这样深邃的文化!人人都好像刚刚认识曾经熟视无睹的某个菜肴:哦,原来吃起来还有这般讲究!人们皆因自己地方的美食特色终于昭示天下而快慰酣畅。
我的家乡石泉有一个叫二里的村子,这里曾经有一种草串的五香豆腐干,别具地方特色。草是秦岭山上的蓑草,草丝如发,色青柔韧,编结成细绳,裁成半尺长许,十根二十根一束。豆腐是用二里村甜水井的水、硒土地上的大黄豆石磨细研、柴火熬煮做成,用盐和香料腌好的豆腐经过烟火熏制,待水汽烘干后切成一寸见方的正方形薄片,编好的细草绳从薄片中心穿过,每条七八片上十片不等。穿好的豆腐干色泽金黄透亮,束束齐整,暗青的草丝在绳头结成穗子,如纱帐上的流苏。这样草串的五香豆腐干,粗物中渗透了精巧的女儿心,也因此便别有了一番雅食的味道。每每逢集,兜售豆腐干的农妇早早地提着竹篮蹲守在街口,边叫卖边漫不经心地结草绳、穿串子。价钱也不贵,两块五一束,往往是一束刚穿好便被人买下两束,卖的人换钱和做工着实是两不相误。有出门在外的游子,每每念及家乡,都会托父母和亲朋好友千山万水地遥寄些过去一解乡愁。卖的年代久了,无论老少,再看到街市上草串的豆腐干总会不由自主地眼前一亮,那样久违了的亲切,不亚于与故人的街头邂逅。
然而随着城市的发展,一切品味在提升的同时,因为速度和效益的关系,人们也不经意丢掉了很多好的东西。草串的豆腐干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取而代之的是一包包用塑料袋装好快速加工出来的五香豆腐干。同样黄亮的颜色却不再有人间烟火的滋味,那是一种叫硝的化学品熏出来的结果;同样叫着以一个地方命名的美食,却仿佛和那里又不再有任何关系。没有了慢慢淘洗慢慢研磨的精心,没有了每一片每一串都经手穿起的耐心,没有了散发着淡淡草木香的蓑草、不经了俗世烟火的缭绕——曾经寄予恬淡安详的家的况味又到哪里寻找?
一个小地方的特色饮食文化的流失尚且如此,一个国家的饮食文化又将如何?源远流长的节日文化氛围被商家铺天盖地的商业运作所垄断,被五花八门的速食包装袋所替代。人们往往看着自己正陷入速食商品的怪圈里,离自己的饮食文化越来越远,却无能为力。
好在,我们还能抓住一些别的。譬如,饮食的灵魂,饮食的质感。
饮食的灵魂是劳动者在日复一日的生存中慢慢塑造出来并妥帖安置在一啖一粥中的,它随着制作者的修养、性情而充满灵性与色彩。饮食的质感也会悄悄地潜入我们的秉性,就像好吃清淡的杭州人也有着如水般绵软的性情、好吃辣椒的四川人什么时候都火爆的咋咋呼呼一样。在城市节奏加快和快餐文化充斥每个角落的今天,创造一种饮食文化不易,发扬和传承一种饮食文化的精髓更不易,如何保留我们身边或粗犷或精致的饮食文化渊源,发掘和保留那些缠绕在舌尖之上细微之处的温情?我想,不妨在我们的秉性中先安妥饮食的灵魂,让它更接近于我们正在延续的地方风俗文化,以及一个民族所固有的质朴、温和与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