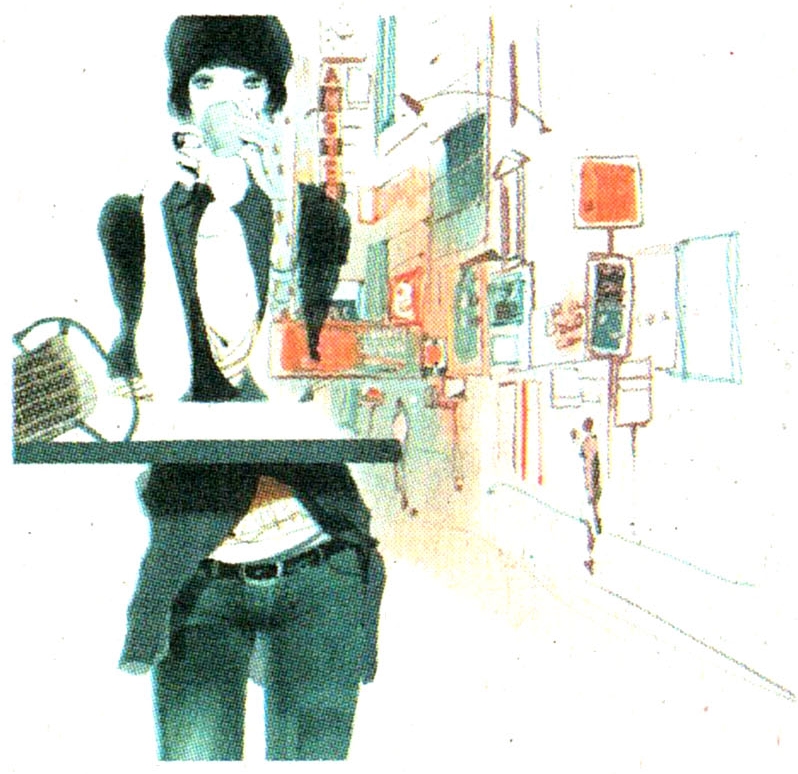□张翟西滨
故事发生在30多年前。
那年,我是一名插队知青,小队有百户人家,四、五百口人,“出工一条龙,干活一窝蜂”是当时大集体劳动的真实缩影。我们小队拥有一排知青院,没有院墙,只有四间简陋的土坯房,男女知青各为两间,最大之便利,每当出工钟声敲响,队上社员必经我们知青点,队长肩扛锄头走在前头并重复吆喝着:“到地里锄草咧!”,凡是队长拿啥农具,我们知青就拿啥,不必多问,一目了然。记得那年开春,日上三竿,左等右候,未闻出工钟声响,不少社员立在路中央朝着铁钟的方向望去,外队社员“一溜烟”出了工,可我们就是难觅队长的身影,莫非家里有事?还是外出了?正纳闷,有的社员猜道:“是不是队长撂挑子不干咧!”一传十,十传百,果不其然被社员言中。
我首次遇到此事,朦朦胧胧,一头雾水。比我早一年插队的知青却不以为然,已经开始收拾行囊准备返城,我也觉得这是不错的选择,小队几位知青齐刷刷返了城。约莫一周同队知青相互打听,好像队上还没有出工的迹象,在家待着吧,周围邻居见面,总会寒暄一句“没回队?”似乎话里有音,内心犹如倒了五味瓶——“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在家又待了两天,我独自归队,但出工的钟声,依旧未敲响。之后,我才弄清:生产队长是队里的“一把手”“土皇帝”,既是地道的“老娘舅”,又是十足的“受气筒”。队长撂挑子,在当时的农村司空见惯,见怪不怪。据说,有的队一年像“走马灯”似的换了几茬队长。
又是一个黎明,“铛——铛——铛——”熟悉的钟声将我从酣睡中惊醒,我揉揉惺忪的眼,侧耳倾听,“嗯”就是我队出工的钟声,我迅速爬起,简单洗漱,到外面一瞧,原来走在队伍最前头的是我们知青点的邻居李老汉,只见他边走边喊:“拉上架子车、带上铁锨,到饲养室拉粪喽!”一声高过一声,声声含糊不清。难道他继任了队长,我纳了闷。李老汉50来岁,中年丧妻,膝下一女,相貌平平,口齿不清,平时,我们总爱和他开玩笑,因腿脚不利落,他几乎常年在队上饲养室干垫圈、起圈和囤积土粪的事。不容多虑,我肩扛锨随大流一起来到队上的饲养室,嗬!土粪堆得像座山,一看就知道好久未清运了,大家攒足了劲,刨的刨、装的装,干得很卖力。春耕时节,麦子泛绿刚露头,这节气,给麦地上土粪就显得尤为重要。
人常说,人哄地皮,地哄肚皮。事后,我得知,缘自饲养室的土粪囤积,他看不过眼,才自告奋勇敲响队上出工的钟声,用社员的话说,有点带“二”。扪心自问,他却让我肃然起敬。随后,在“二队长”的带领下,大伙整整干了多半月,硬是把饲养室的“粪山”给推平了。由此,“二队长”的美名在大队传开了,直至我队选举产生出新的生产队长……
往事如烟,至今回味。在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农民身上,真的,不乏可贵之处和学习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