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川
2015年10月9日凌晨6时20分,杜润生老人走完他102年的人生历程。多年来,他为推动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呕心沥血,是公认的“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他的思考和建议对于中国改革深化亦极具启示。他亲身经历了中国近代史的风云变幻,也参与了众多历史事件。在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过程中,中国农民的屈辱与苦难让杜润生忧乐难忘,他自觉地担任农民的代言人,为农民的权利鼓与呼。
“追溯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历程,无论是在文献的丛林中检索,还是在人们记忆的长河里回望,我们都看到有一个众望所归的名字——杜润生。”2012年7月18日,当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宣读到“杜润生”的名字时,“第五届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颁奖大会的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这一天,是杜润生的百岁(虚岁)华诞。农村发展研究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将“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特别贡献奖”授予这位被称为“农村改革之父”的老人,以表彰他对中国改革的杰出贡献,同时也“向激荡着创造与梦想的改革时代致敬,向伟大的中国农民致敬”!
王岐山打来电话,“祝贺杜老百岁生日快乐。”20多年前,王岐山在杜润生担任主任的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也是“农口”团队的重要一员。
200多名来宾中,许多人都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的见证者与推动者。其中既有原农业部长何康、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石山等杜润生的老同事,也有杜鹰、林毅夫、周其仁、张木生、孙方明等当年“农发组”的成员,他们将“杜老的弟子”作为自己的一种荣誉称号。
杜润生没有出席颁奖会,而是通过视频向与会者问好。这位百岁老人精神健旺,声音洪亮,当他挥手时,掌声与笑声充满了会场。
【一】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传统秩序逐渐动摇,至辛亥革命开始瓦解。生于辛亥革命第三年的杜润生也见证了传统秩序的瓦解过程,晚年他曾回忆道:“我是山西太谷县人,出生在破产富农家庭,家乡有很多人经商。民国初期,我亲眼目睹了晋商的消亡。”
家国多难的特殊历史环境,使得许多知识分子接受了激进主义的思想,期望以社会革命彻底改造中国。杜润生也是其中的一员。在太原国民师范学校读书时他就积极参与学生运动,进入北平师范大学后更成为“一二·九”运动中的学联代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这位大学生脱下长衫,进入太行山根据地,参加抗日游击战争。
此时北方农村经济衰败,基层政权又因国民政府撤退而瓦解,中国共产党以抗日的民族主义为号召,在农村重建政权。与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高举的“民主、自由、抗日”旗帜的感召下,杜润生和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加入了革命的队伍。
抗战胜利后,由于腐败、独裁,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迅速流失,共产党则提出“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富强的新国家”,为新民主主义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旗帜。
国共内战再度爆发。为了动员农民参加革命,中共从1946年开始进行土地改革。先后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共中央华中局秘书长的杜润生参与领导所在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他的一些建议还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要求各地遵照执行。
【三】
直到1952年土地革命完成之前,中共一直强调,新建立的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按照新民主主义撰写的《共同纲领》和《土地改革法》中,都规定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允许土地买卖,农民拥有买卖、雇佣、借贷、贸易等自由。
参加革命的许多知识分子满腔热情地建设着新民主主义社会,他们认为社会主义还是很遥远的事,目前最重要的是发展生产力。毛泽东也说,搞社会主义,是在20年,甚至30年以后,要在社会生产力充分发展以后,要在人民群众都表示同意以后。
1952年秋天,当杜润生进京担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时,就抱着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思想。这个新成立的部门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和领导农民的互助合作运动。不过杜润生和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都认为,当时很多地方刚刚结束土地改革,要从小农经济的现状出发,发挥小农经济的积极性,互助合作运动需加以引导,不能操切从事。
可是,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思想已经发生了变化。进京不久,杜润生与毛泽东的秘书、兼任农工部副部长的陈伯达之间有过一次谈话。陈伯达说,合作化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创造,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需要“组织农业生产大军”。杜润生说,这不成了“劳动营”了?
无意之间,对话者透露了历史的天机,让后来读史者感到惊心动魄。毛泽东就是要以苏联的集体化为榜样,改变私有制,让广大农民成为他可以如意指挥的“生产大军”,建设一个他所设计的美好新社会。
1953年,中国关闭了粮食市场,实行统购统销,农民不能自由买卖粮食。两年后,毛泽东掀起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已经深入社会神经末梢的行政权力发挥了威力,全国96%以上的农民交出自己的私有土地,个体农民的财产合并为不可分割的集体财产,社员不能自由退社,合作社由“干部”进行管理和支配产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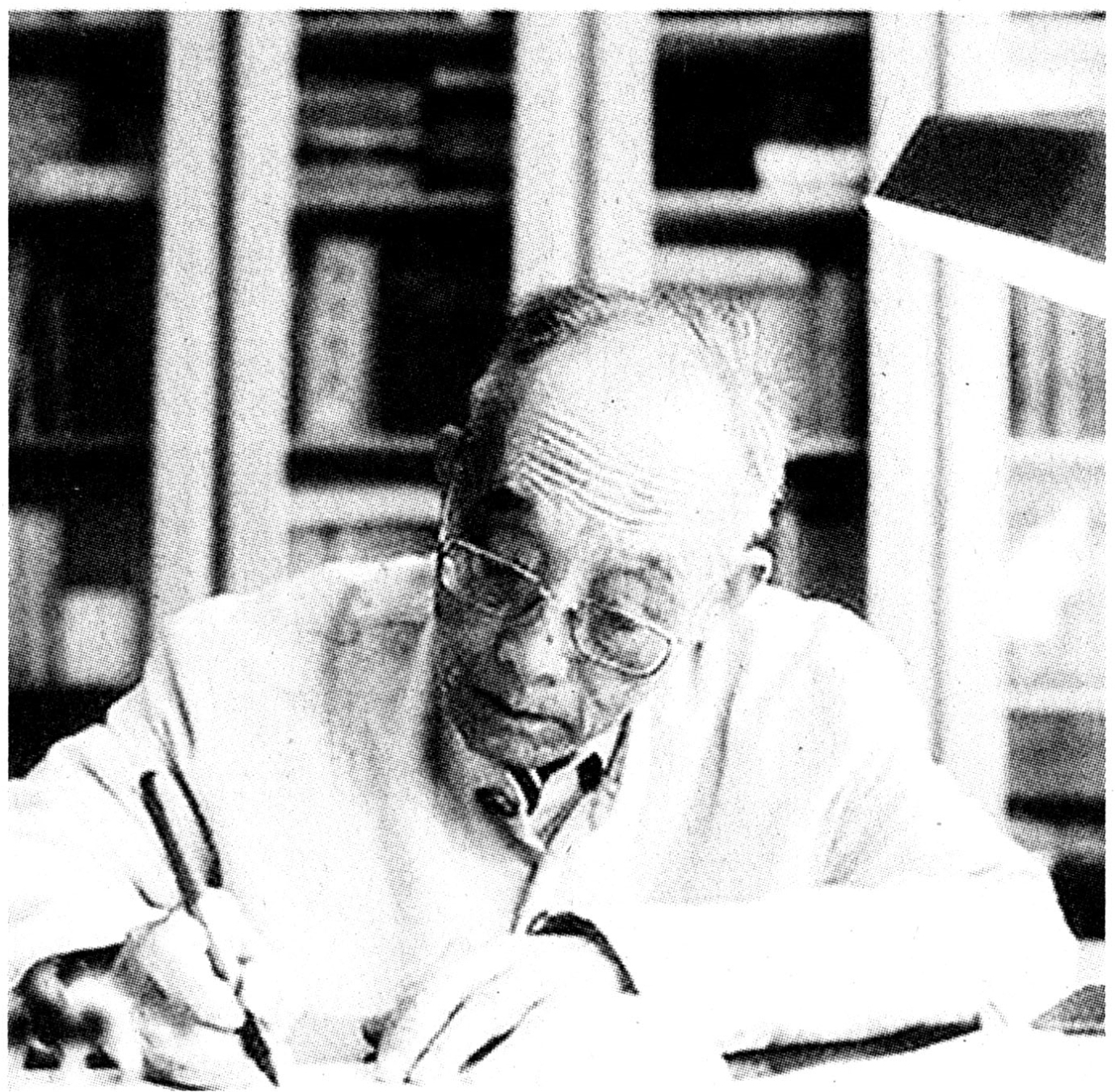
杜润生 (资料图)
【三】
杜润生后被调到中国科学院,但是他依然关心着农民和农村。在实现合作化之后,农村并没有发生预期的变化,1956年粮食反而减产了。这也是中共建政之后的第一次减产,“工农差别”也在扩大。毛泽东不得不亲自站到前台指挥“农业生产大军”。他认为,依靠群众运动,实施所谓“大兵团作战”,就可以提前实现工业化。
于是,数亿农民卷入了一场由个人设计的大同世界的试验——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废除按劳分配,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不但东西是公家的,人也是公家的。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人民公社体制,成为计划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为“大跃进”提供了制度基础。因此,“大跃进”参加人员之广、声势之大,都是史无前例的。在全国性的狂热之中,伟人许诺的天堂似乎就在眼前。
在杜润生看来,“人民公社制度作为一项社会试验,划定一个地方实行,本不应非难。但人民公社一声号令,一下子就卷入6亿人口,付出代价太大了。‘浮夸风’‘共产风’,走向极端,造成大灾难。”狂热退潮,公共食堂被迫解散,但是人民公社制度仍被保留下来。
在过去的1000多年间,曾经是可以自由迁徙、自由择业的农民,现在被死死地捆绑在土地上,即使外出讨饭也要有证明信。苏联集体农庄近似国营农场,但国家承担一部分社会保障费用。可是,中国的农业经营决策来自国家,风险却要农民自己承担,而且农民得不到国家的社会保障。
【四】
为了维系身家性命,中国农民偷偷地扩大自留地,“在那一时期,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自留地的增产效应。农民告诉我:用自留地的办法,保管不愁粮食吃。”当时杜润生不知道,农民还搞了包产到户。这些求生之举屡次遭到政治权力的打压,包产到户更是“三起三落”,无数的人们因此遭受迫害。
1972年的冬天,曾公开肯定包产到户、被杜润生称为“中国农村变革的先驱和开拓者”的邓子恢凄然离世。杜润生则幸运地熬过了“文革”岁月,在1979年重新回到了离开24年的农村工作部门。
此时的中国正处于变革的前夜。就在前一年的深秋,淮河边上的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按下了手印,冒着坐牢的风险搞起了“包产到户”。当时,全国人均占有的粮食只相当于1957年的水平,农民平均年收入只有70多元,有近四分之一的生产队社员年收入在50元以下,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
尽管包产到户能够提高生产力是一个显见的事实,但是党内总有人认为它不符合社会主义公有制格式。对此,杜润生说:“我国建国后在农村推行的农业集体化、人民公社,实践的结果引起人为饥荒。而公有土地家庭承包制在短短几年就解决了人民的吃饭问题,孰优孰劣,不是一目了然吗?为什么总让僵化的教条像梦魔一样纠缠自己的头脑呢?”
身为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杜润生,既熟悉农村工作,也熟知党内规则,既可以沟通田野,也可以说服上层。这些合金般的品格组合使他拥有无与伦比的说服力、感召力和协调力,因此成为上世纪80年代制定中国农村改革政策最有影响的核心人物之一。他创造性地提出“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这一概念,实现了包产到户的合法化。
农民也开始拥有了自己的财产权利。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转移到城市非农产业就业,从这时起,中国农民才挤进了国家现代化的门槛。农村改革的成功,既为全国改革提供了经验,也提供了改革的物质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农村改革是中国改革的真正起点。
【五】
上世纪80年代中期,76岁的杜润生也正式退休,告别了“激荡着创造与梦想的改革时代”。他继续以悲悯的目光关注着农民,观察并思考他们的命运。
2008年,因为对农村改革和发展乃至整个经济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杜润生获得了首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95岁的杜润生在颁奖典礼上说:“家庭联产承包制是农民的发明,我们只是进行了调查研究理论化。”
杜润生曾说道:“我在农村问题上有一条原则:尊重农民,让农民真正解放。”在改革之初,杜润生就提出给予农民“永佃权”。在多数人反对的情况下,他坚持尽可能延长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将使用权物权化。在他看来,中国土地制度最终要“由他物权变为自物权”,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
历史往往并不按着人们的良好愿望发展。公有制下的家庭经营激发出了极大的生产力,可是并没有让农民获得完整的所有权,“承包土地的所有权究竟应该归谁”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城市化进程中,这种妥协的土地制度使得农民无权作为土地产权主体平等地参与土地交易,政府则可以轻易地“低价征地、高价卖地”,于是在十多年间就从农民那里拿走了高达20万亿—30万亿元的土地增值收益。
沉重的现实让晚年的杜润生心事浩茫,忧思深广。他认识到,没有用法律形式把土地承包制作为一种产权制度安排固定下来是一大缺陷,“中国政府惯于用行政系统发布原则性政策指导工作,特别是涉及财产权力的问题,尚待制定法律条文,规范人们的行为,这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宏观调控内容。忽视这点,就无从建立交往中的信用,否则依森林法则,弱肉强食,不会造成良好的预期和有序的市场。现在农村土地中的许多问题,都与此有关。”
此外,因为户籍等制度的阻碍,上亿农民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摆动。城乡收入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拉大,“三农问题”再次凸显。2001年杜润生在一篇文章里痛呼“我们欠农民太多!重新审视‘三农’问题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截至今天,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政府听不到他们的诉求”,杜润生写道,“工人有工会,要允许农民成立农民协会,使农民依靠它行使已经拥有的权利。”
中国现代化历程尽管曲折,但是前进的目标已经越来越明晰:通过改革,建立民主、法治的新秩序。就像杜润生所说:“我们需要一个透明的政府,要在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下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的文明国家。我国人口多、资源少,但我们需要有民主、有自由,要成为世界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