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今年7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宁夏回族自治区考察,在将台堡向红军长征会师纪念碑敬献花篮。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和将台堡会师,标志着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参观三军会师纪念馆时,习近平说,长征永远在路上。这次专程来这里,就是缅怀先烈、不忘初心,走新的长征路。今天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新长征。我们这一代人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剿”,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其间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无人烟的草地、翻过连绵起伏的雪山,行程约二万五千里,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之后,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也先后进行了长征,最后,红军三个方面军于1936年10月胜利会师,结束长征。三支红军会合时虽不足3万人,但他们是经过千锤百炼后保存下来的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宝贵精华。正当抗日烽火即将在全国燃起的时候,三支主力红军在接近抗日前线的陕北会师,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硝烟早已散去,历史不容忘却。红军长征创造了中外历史的奇迹。革命理想高于天,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面对形形色色的敌人决一死战、克敌制胜,这些都是长征精神的内涵。为了继承和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本报计划在“视野”栏目推出四期“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系列专题”,以丰富感人的资料和报道,展示这一改变中国人命运的史诗般征程,讲好长征故事,永存长征记忆。
长征精神既属于历史,也属于当代,更属于未来。80年后的今天,长征精神的每一个音符都蕴含着时代的因子,都具有撼人心魄、发人深思、催人奋进的强大力量,照耀着我们前行的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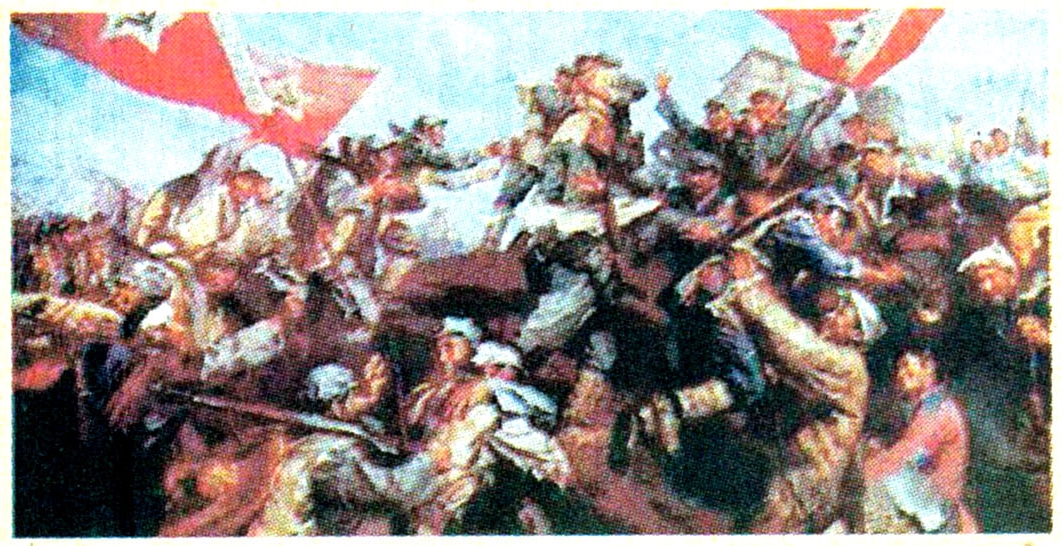
彝海结盟:血脉延续 情义传承
43岁的沈建国住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海河边的一个小区里。尽管盛夏时节酷暑难耐,但在太阳落山后,海河边的晚风却很清凉。沿着河堤,他会一直走到邛海边。
西昌城里的黑彝公务员
邛海湿地是中国最大的城市湿地公园,如今已成为凉山旅游的地标。
这片有些神秘的土地富有多样的自然风光、多元的民族文化、充满特色的美食。
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沈建国是不太起眼的那个——皮肤黝黑,头顶上毛发稀疏,不笑的时候看上去有些严肃。
“我是黑彝。”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神色中有一丝难以被捕捉的自豪。
凉山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黑彝,在解放后民主改革之前,曾意味着身份的高贵。如今,旧时代的阶层早已被打破,对于沈建国来说,“黑彝”二字的意义仅代表着自己作为一个彝族人,血统依然纯正。
81岁的老母亲对此非常看重。正因如此,沈建国的妻子也是一位黑彝。
只是,家里的人丁并不兴旺。早在幼年时代,他就眼睁睁地看着弟弟妹妹因病夭折。他不敢在母亲面前提起这些伤心的往事。老人的眼泪一落下来便止不住。那些忧伤的童年记忆虽然挥之不去,他却宁愿深埋心底,绝口不提。
自从2000年从深山里的西昌卫星发射基地转业到地方,沈建国一直生活在西昌。如今,他是凉山州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行政审批科的科长,轮到值班的日子,他会挂上工作牌,端坐在州政务中心的窗口接待办事的老百姓。
凉山总人口近500万。在这里,除了彝族,还有汉、藏、回、蒙等14个世居民族。如今,不同民族之间的通婚早已不是稀奇事。在凉山的许多黑彝家支中,已有不少人与其他民族“开亲”。
沈建国有两个儿子。对于他们将来的婚姻,他表示,将“尊重孩子自己的选择”。
核桃树下的果基伍哈
从成都出发,沿着G5京昆高速公路行驶330公里,从彝海出口下高速,再沿着G108国道向南行驶,拐进一条岔路开始爬山,路旁的山坡上有一棵茂密的核桃树。据当地百姓讲,树龄已超过百年。
这棵核桃树旁,曾经坐落着果基伍哈的家。80多年前,他的爷爷果基约达也住在那里。
彼时的凉山还处在奴隶社会,等级森严。
从西昌北上通往大渡河,有两条路——一条是经越西的“官道”,另一条是穿过拖乌地区的密林小道。
拖乌地区的深山中,居住着果基、罗洪、倮伍三个家支。果基约达是黑彝,也是果基家赫赫有名的家支首领。
虽然三个家支经常相互“打冤家”,他们却有着共同的仇敌。那时的彝区流行着一句谚语——“石头不能当枕头,汉人不能做朋友。”
得出这样的结论,源于历朝历代对凉山严苛的统治。“不尊重民族习惯,不把彝族当人,用高压的方式管理,导致彝汉之间矛盾很多。”果基伍哈说。
历代统治者把彝区视为畏途,以往汉族的军队想通过彝区几乎不可能。1863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部曾深入此地,前有清军拦截,后有彝人围攻,最终在大渡河畔惨败于清军,折戟安顺场。
国民党统治时期,该地的彝汉矛盾更加突出。各个县里都有国民党的驻军,许多无赖混在驻军中,欺压百姓,无恶不作。
然而果基约达是个另类。多年来,他走南闯北,认识了不少汉人。81年前,他甚至与“不能做朋友”的汉人歃血为盟,结为了兄弟。
果基伍哈虽然出身黑彝族,却从未因此感到身份尊贵。在“文革”浩劫中,虽然家境早已败落,却被划为地主。这顶“帽子”,直到他上小学二年级才摘掉。
有一天,老师带同学们去春游,在彝海畔动情地讲起红军过冕宁的故事。果基伍哈发现,原来当年与汉人结盟的爷爷还有个更加广为人知的名字——小叶丹。
三年级下学期,果基伍哈从彝海乡转学到县城读书。他给自己起了个汉族名字,叫作沈建国。
彝海畔的诺言
“上有天,下有地,我刘伯承与小叶丹今天在海子边结义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
“我果基约达今日与刘司令员结为兄弟,如有三心二意,同此鸡一样死去。”
1935年5月22日,彝海见证了红军长征史上伟大的一幕。
结盟仪式按照彝族的风俗进行。虽然没有酒,毕摩(巫师)将一只大红公鸡的嘴角剖开,将鸡血滴进了盛着彝海湖水的碗中,二人一饮而尽。
81年后,湖水依然清澈,在阳光下泛着粼粼的波光。聆听着沈建国的讲述,那段光荣的历史依然让人热血澎湃。
1935年5月,红军到达泸沽后,为正确宣传和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揭露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号召彝汉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军阀。5月19日,中央红军派出以刘伯承为司令员、聂荣臻为政治委员、萧华为群众工作队长的先遣队,准备借道彝区,抢先渡过大渡河。
刘、聂二人都是四川籍,尤其是刘伯承曾在川军中任职十几年,阅历丰富、作风细致,非常熟悉川西地理风俗人情,对彝区风俗和家支情况比较清楚。
5月20日,先遣队占领冕宁县后,立即释放了被扣押在城内“坐值换班”的彝族家支人质,并向他们宣传民族平等政策,说明此次只是想借道通过。获释的彝族同胞得到红军发给的食物衣物,回家后当了红军民族政策的宣传员。
“在冕宁待了一天后,先遣队到了大桥镇,从那里往东都是果基家的地盘。老百姓告诉刘伯承,借道拖乌地区需要与果基家支的首领交涉。另外,他还需要一个能跟果基家搭得上话的人。”沈建国说,“一位在冕宁开酒馆的汉人陈志喜自告奋勇来当‘中间人’。他与爷爷关系很好,过去爷爷去大桥镇都在陈家吃住。”
5月22日,萧华与红军总部工作团团长冯文彬一道,由陈志喜带路,率领红一军团侦察连组成的工作团开路,进入果基家的领地。
“爷爷虽然自从红军到了凉山后就一直打听消息,了解到这支队伍纪律严明,对老百姓秋毫无犯,然而还是没有放松警惕,便在山上埋伏了人。陈志喜边走边喊话,红军也一直严守着决不开枪的规定。最后,爷爷的四叔先和萧华进行了接触,随后萧华被带到爷爷面前。”
“萧华告诉爷爷,刘伯承表示过,如有必要愿意与他结盟,并向爷爷再次讲了红军的民族政策。爷爷慢慢打消了顾虑,随后把刘伯承请到彝海边见面。过去国民党对彝族不当人看,爷爷从刘伯承身上看到了尊重,觉得这个人也很可信,与他相见恨晚。”
“歃血为盟后,他们互赠了礼物。刘伯承把手枪送给了爷爷,爷爷把自己的骡子送给了刘伯承。”
结盟当日晚上,刘伯承将果基约达叔侄请到红军宿营地大桥镇,开怀畅饮。他把一面写着“中国夷(彝)民红军沽鸡(果基)支队”的红旗赠给了果基约达,并任命他为支队长,并当场写下任命状。
次日,果基约达带路,带红军进入拖乌地区,直到走出家支领地,双方才依依惜别。而后,红军后续部队也沿着“彝海结盟”这条友谊之路,顺利地通过彝区,迅速抢渡大渡河,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圈。
小叶丹一直信守着诺言。红军走后,国民党追究他与红军结盟的罪责,他被迫交出1.2万两白银和120头母羊。但他宁肯倾家荡产,也不愿交出队旗。他将旗帜珍藏在背篼下特制的夹层里,随身携带,还不断叮嘱妻子:“万一我死了,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这面红旗,将来交给红军。”
“1950年,西康省解放后,奶奶依照爷爷的遗嘱,把藏在百褶裙里的‘中国夷(彝)民红军沽鸡(果基)支队’的队旗献给了政府。”
共产党也信守着当初向彝族同胞许下的民族自治的承诺。1952年,凉山成立彝族自治区,1955年,改成自治州。
血脉延续,情义传承
高中毕业后,沈建国和表兄伍龙一起被保送到北京上大学。伍龙去了中国人民大学,他进了中央民族大学。在上学期间,学费、生活费全免。
“国家没有忘记彝海结盟的后人。”他说,这么多年,他一直心怀感恩。
1997年,伍龙毕业后被分配到全国人大工作。沈建国一心想参军。“总有一点父辈的情结在那里。”
然而,最终由于身体原因,沈建国只在部队待了几个月,就来到了现在的单位。
“同事都说,你有小叶丹孙子的身份,应该上个台阶啊。可我觉得,做什么、在什么岗位不重要,我应该像颗螺丝钉一样去发挥作用。”
他说,刘伯承和小叶丹的后人,如今已到第三、第四代,至今还传承着父辈们深厚的感情。
而小叶丹所属的果基家、他的妻子所属的倮伍家,也诞生了诸多的彝族精英。他们中的绝大部分,现在都生活在凉山,并继续为家乡的发展做着贡献。
倮伍家族中,伍精华历任四川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国家民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西藏军区政委、西藏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是家支中从政者的代表。
1983年2月,他作为起草《民族区域自治法》五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直接参与、组织和领导了《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起草工作。
如今,伍精华的孙子伍晋刚已成长为一位研究彝族文化的专家。他说,正因为有了长征途中的“彝海结盟”,才使得封闭的凉山彝区向外界敞开了大门。从此,中国其他民族乃至整个世界的文明,得以进入,并与彝族本土文化形成互补。对于中国革命来说,它是我党民族政策的第一次伟大实践;对于彝族儿女来说,它将古老文明带入了一个崭新的纪元。
行走在凉山大地上,我们发现,另一场战斗正在打响。
作为中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凉山要在2020年以前摘掉48.7万顶贫困帽。在见证了刘伯承和小叶丹兄弟情义的冕宁县,任务更加紧迫——根据凉山州定下的目标,该县将于2017年实现脱贫。
2006年,沈建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爷爷跟着党走,后人更要传承发扬。作为小叶丹的后人,生活中要更加自律自强。我们虽不能做超越爷爷的事,但是绝不能给爷爷脸上抹黑。这一点,子子孙孙都要传承下去。” □吴光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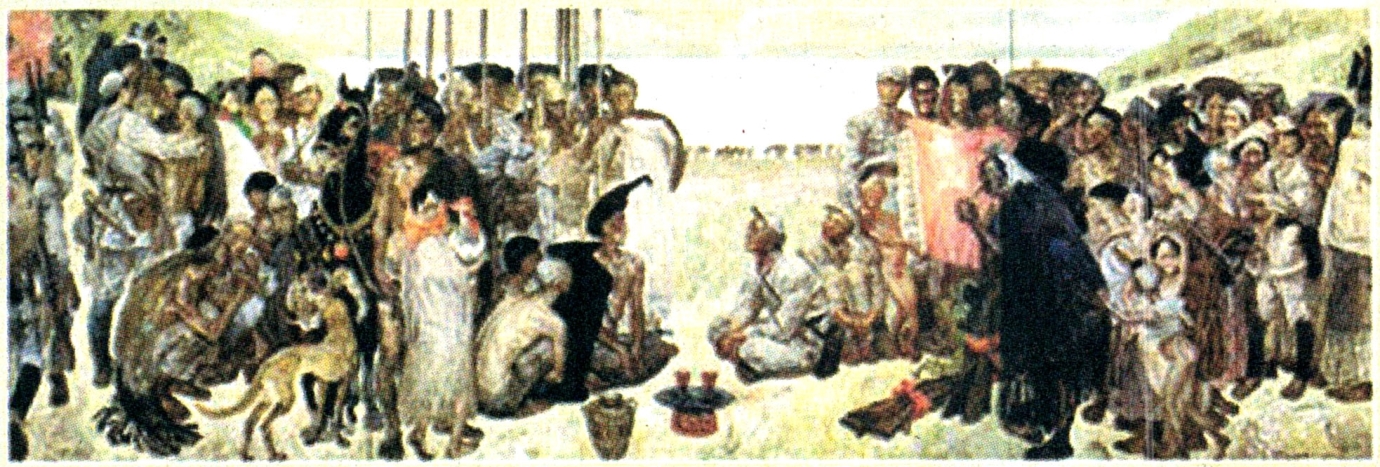
油画:长征诗画(4) 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
长征路上的女红军
在红军长征的队伍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女红军。她们当中既有中央苏区党政军领导的妻子,也有普通的女干部、女士兵。女红军人数最多的要数红四方面军,包括了一支成建制的妇女部队——妇女独立师。人数最少的是红25军,只有周东屏、戴觉敏、曾继兰等7名随军医院的女护士,人称“七仙女”。
在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上,女红军一样要面临频繁的战斗、高强度的行军,一样要经受疾病、饥饿,以及雪山草地等严酷环境的考验。此外,女性生理期痛苦和怀孕、分娩的折磨,又使她们承受了比男红军更多的艰辛。她们用女性特有的柔韧与艰苦的环境和命运进行殊死抗争,用浓浓的情与爱谱写了一个个感天动地的故事。
长征中,为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部队要不停地赶路。女红军如果遇上生理期,尽管腹部绞痛、两腿发抖,但也要捂着肚子一步步往前挪。宿营时,往往三五人挤在一起,躺卧在冰冷潮湿的地上。无奈之下,有的女红军居然练就了站着睡觉的本事。
异常艰辛的长途行军,使许多人因伤病而掉队。当时规定,对实在走不动的伤病员,给8块大洋寄养在当地老百姓家里。为了跟上大部队,女红军们提出一个朴素的口号:不掉队,不带花,不当俘虏,不得八块钱。进入贵州后,中央红军干部休养连战士邓六金患上痢疾,实在走不动路了。上级便拿出8块银元,劝她留下养病。邓六金坚决不同意:哪怕是死,也要死在队伍里!红四方面军妇女运输连连长王泽南更是一位传奇人物。这位裹着小脚参加长征的女红军,过雪山时,唱起自编的歌谣来鼓励战友们:裹脚要用布和棕,包得不紧又不松;到了山顶莫停留,革命道路不能停。最终,她硬是以“三寸金莲”的小脚,一步一步走过雪山草地。
长征途中,女红军的衣食住行更是异常简陋。据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从中央苏区出发时,她的全部家当是一条毯子加上几件必备的换洗衣裳和大约够吃10天的口粮,打成一个背包,腰带上还挂了一个搪瓷缸,走起路来叮当作响。遇上阴雨天会被淋得像落汤鸡,几天不下雨则是满身尘土。
恶劣的自然条件和严重的物资匮乏使正值豆蔻年华的女红军忘记了自己的性别。为在作战时不被敌人认出是女的,她们剪去了长发。风餐露宿,长途行军,根本没条件考虑个人卫生问题。红军个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头上长满了虱子。彭德怀开玩笑:“无虱不成军,没有虱子的不算长征干部!”每当宿营时,无论男女老少、职务高低,都有一项“必修课”——捉虱子。为此,一些女红军干脆剃成光头。
红6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李贞回忆长征时曾感叹:“特别是我们这些女同志吃的苦比男同志更多。日夜兼程行军打仗,女同志头发里都长满虱子,一梳就呼呼地往下掉。有些女同志身怀有孕,挺着大肚子行军打仗。尽管领导和同志们关心、照顾女同志,把干粮让给我们吃,把马让给我们骑,可还是付出比别人更多的气力。”
过草地时,女红军无一例外地领略了自然环境的严酷。辽阔的草地一望无垠,黑色的泥沼被深草覆盖着,人和牲口陷在里面就会被吞没。一天,邓颖超连人带马掉进了沼泽地里,幸亏被后面的同志及时发现,才把她拉上来。当时天降大雨,邓颖超浑身上下都湿透了,原本体弱患病的她又发起高烧。整整七天七夜,邓颖超终于走出茫茫草地,看见一户人家的房子。那房子上下两层,上面住人,下边养牲口。由于身体虚弱、疲劳不堪,邓颖超走路都很困难,根本上不去楼,便一头扑在粪堆上,站不起来了。直到蔡畅和其他几个同志赶来,才把她架到楼上。蔡畅后来告诉邓颖超,当他们看着一身粪便的邓颖超,都忍不住偷偷地哭了,以为她活不成了。
刘伯承元帅的夫人汪荣华曾回忆:“我们身着单衣,在沼泽地里行军,两脚泡在又臭又凉的水里,其艰苦程度是可以想象得到的……粮食越来越少,不几天,我们就把刚进草地时携带的一袋用青稞做成的炒面和一块鸡蛋大的盐巴吃光了。在这渺无人烟的沼泽地里,到哪里去找粮食呀,没办法就吃野菜,有的同志把脸都吃肿了。最后连野菜也不好找到,只好找来一些牛皮,把牛皮上的毛烧掉,用水煮着吃。”
为了生存,树皮、草根、皮带,女红军几乎什么都吃过。一次,杨尚昆的夫人李伯钊错把野烟叶当成萝卜缨,吃下后差点中毒。为把牛皮鞋底制作成“美味佳肴”,她们还编了一首打油诗:牛皮鞋底六寸长,草地中间好干粮;开水煮来别有味,野火烧后分外香。两寸拿来熬野菜,两寸拿来做清汤;一菜一汤好花样,留下两寸战友尝。
漫漫长征路,女红军有的在战斗中牺牲,有的在行军路上倒下,有的因环境条件恶劣而导致生理变化、终生不育,更有像贺子珍、曾玉、陈慧清、廖似光、吴仲廉等在长征途中分娩的母亲,产后不得不忍痛把刚出生的孩子托付给老乡抚养,却从此生死不明……为了革命的胜利,她们牺牲了自己的爱情,牺牲了自己的亲生骨肉,甚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李涛 郭林雄 郑文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