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党和红军如何利用报纸发挥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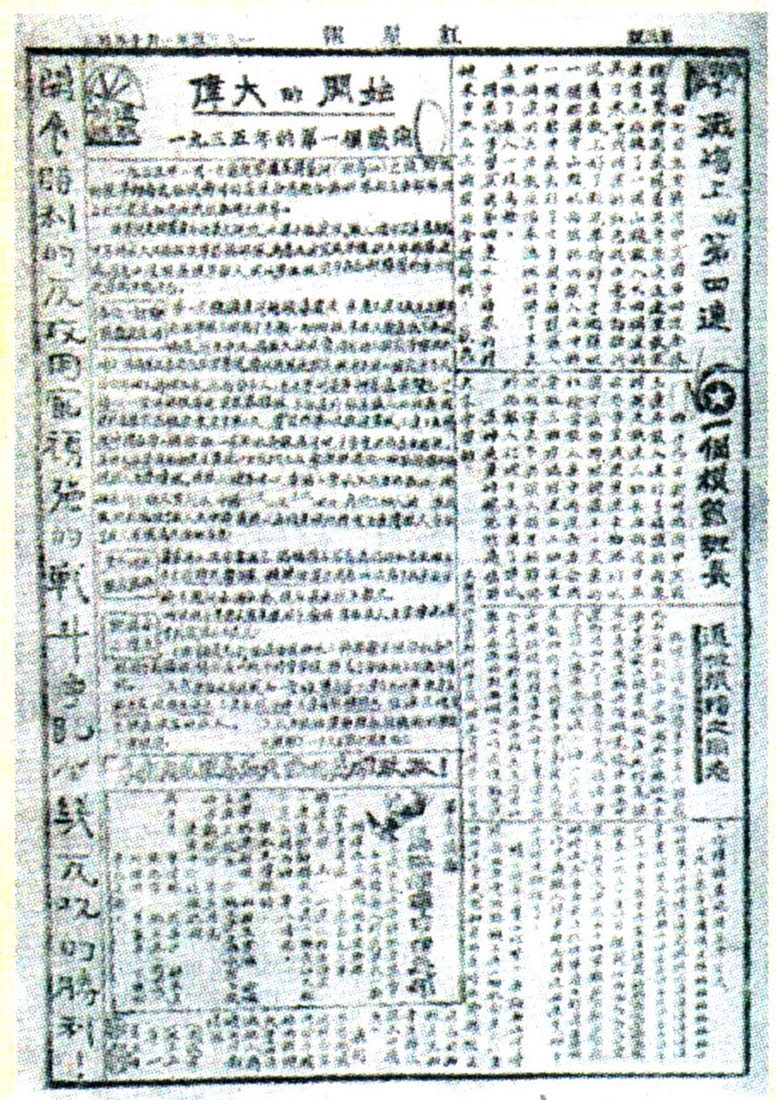
这是《红星报》关于红军强渡乌江英雄事迹的报道(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传播渠道日益多元的今天,传统的新闻载体——报纸,似乎离人们渐行渐远。然而,在80多年前的长征中,对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来说,报刊的作用不亚于枪支弹药,是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同时也是红军了解外界信息的重要手段。
条件艰苦但办报不止
长征开始后,为了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红军常常是连续行军作战,所处环境十分恶劣。但即使这样,他们仍想方设法坚持编印报刊,如红军总政治部的《红星报》、《前进》报,红一军团的《战士》报,红二方面军的《前进》(副刊),红四方面军的《不胜不休》报等,都在长征路上坚持出版。
1931年11月7日,红色中华通讯社(即新华社前身,简称红中社)在江西瑞金成立。红中社最初担负两项任务:对外播发宣传中国共产党、苏区和红军的新闻,编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报;依靠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电讯,编印供领导决策的内部参考消息(《参考消息》前身)。
长征期间,《红色中华》报因条件有限而停止工作,但抄收工作始终在进行,为中央领导了解敌方信息、实施正确决策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红军长征中的报刊多为手刻蜡纸油印。由于物资紧张,红军的印刷设备十分简陋,如《红星报》就是一台油印机、几盒油墨、几筒蜡纸、几块钢板、几支铅笔和一些毛边纸等。报纸最初使用从苏区带来的毛边纸,用完后,大家就因地制宜找“纸”源。长征中曾发行过“叶报”,就是拿树叶当纸进行宣传。
1934年10月20日,《红星报》发行了长征中的第1期油印报纸,其中《突破敌人封锁线,争取反攻敌人的初步胜利》、《当前进攻战斗中的政治工作》等文章,起到了积极的战斗动员作用。1934年11月7日,《红星报》针对个别部队纪律松懈、违反群众纪律的现象,刊登了加强党和军队组织纪律的文章,对加强党的组织纪律,教育党员干部和红军指战员切实保护群众利益起到了重要作用。
巧借国统区报纸确定红军战略转移方向
长征途中通讯十分不便,致使红军主力部队之间的联络经常中断。由于国统区报纸种类多、发行范围广,因此红军每到一地都会派人专门搜集报刊资料。
据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毛泽东等领导同志还有一个习惯,每到一地,顾不得吃饭休息,就研究各个部队发来的电报,还尽可能地找报纸来看。下面部队得到报纸也往中央部队送。他们把这些东西当宝贝一样,看得很仔细,反面文章正面看,从中了解敌我情况。”
有一个众所周知的故事:1935年9月,红军到达哈达铺后,毛泽东凭借缴获的《大公报》,了解到陕北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这一重大消息促使党中央作出了落脚陕北的战略决策。
事实上,不少在长征中掉队的红军,也是在看了《大公报》的有关报道后,知道了大部队的去向,赶上了队伍。1937年2月,周恩来在西安会见《大公报》战地记者范长江时指出:“你在红军长征路上写的文章,我们沿途都看到了,红军干部对你的名字都很熟悉。”
“借船出海”构建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阵地
为打破国民党政府的新闻封锁,真实报道红军长征的实际情况和中国共产党北上抗日的真诚愿望,1935年12月9日,中国共产党在巴黎创办了《救国时报》。这份报纸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直接领导下,积极传播长征信息,着力塑造共产党和红军的抗日形象,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援助,堪称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的“红色阵地”。
比如,1936年12月,杨定华在《救国时报》上发表的《雪山草地行军记》和《从甘肃到山西》两篇长篇长征实录,以亲历者的视角,详细介绍了红军长征中的所见所闻,扩大了红军和长征的影响。
陈云是党内利用海外媒体宣传长征的杰出代表。他曾在巴黎出版的《全民月刊》上,假托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之口,介绍了红军长征的相关情况,收到了良好的反响。
长征中,虽然红军的办报条件简陋,规模也十分有限,但却积累了丰富的开展报刊活动的经验,为党的新闻宣传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肖石忠 王经国 孙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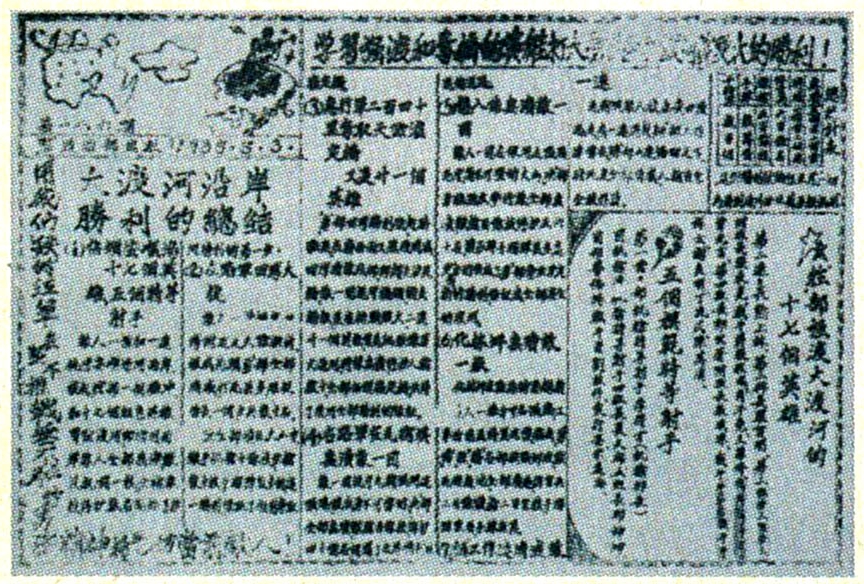
这是报道红军强渡大渡河的《战士》报(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长征中红军军装是什么样子
军装,是供军人穿着的制式服装,是军人身份的重要标志,是部队形象的重要体现。军装不仅是军人生活的必需品,也是重要的装备物资,是构成军队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透过不同时期军装的质地、颜色和款式,不仅可以品味出时代的审美,同时也反映出那个时代军事、经济和技术发展的水平。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军装就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红军初创时期,成分来源复杂,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也有从国民党军队中起义的官兵。因此,红军军装五花八门。
1929年3月,红四军打下闽西重镇长汀后,成立红军临时被服厂,为部队缝制了4000套军装。毛泽东、朱德、陈毅亲自审定了新军装的样式:上衣为中山装式,两个上贴口袋,领口缀红布领章;裤子为普通样式,配绑腿;军帽为八角形,缀红布五星帽徽。不过,这款军装只在红四军范围进行了初步的统一。
红军真正有了统一的服装是在1932年。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随即建立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32年春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看到来自不同部队的学员身着各种样式的服装,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刘伯承认为,红军学校的学员代表红军形象,服装应该统一,不然既影响整体形象,也不利于学校的正规建设。为此,他把设计红军军装的任务交给了学校俱乐部主任赵品三。
设计服装时,赵品三参考借鉴了许多军队的服装。比如,在设计上衣时,起初他仿照苏联红军军服紧袖口套头样式,但这种样式不适合中国南方湿热的气候。后来,他又仿照国民革命军军服式样,将上衣改为前开襟、敞袖口。在颜色选择上,既要与国民党军服区别开来,又考虑到红军经常在山地行军作战,他选用了不容易暴露目标的灰布制作。
经过精心设计,赵品三将新军装设计为:上身中山装,下身西装裤。衣领上缝两块红布领章,象征红旗普照全国。军帽开始采用大八角式列宁帽,但因帽角太大,不适合中国人的脸型,就改为“小八角”,帽中央缝一颗红布五角星,象征工、农、兵、学、商团结一心向革命。
刘伯承对这套军装非常满意,认为既美观又实用,于是就指示给每个学员做一套。穿上新军装的学员显得分外威武、英气。
红军学校有了新军装这个消息很快在各部队传开,并在指战员中引起不小的轰动。很快,中央苏区各部队、各根据地红军纷纷按照这种样式制作军装。
作为我军第一次统一的军装,无论是服饰的设计,还是颜色布料的选择,都突出了中国工农红军的特色,如红布五角星帽徽、红布领章凸显了我军的革命本色,八角野战帽、粗布衣料的设计既与根据地简陋的生产条件相一致,也拉近了与人民群众的距离。
长征期间,红军就是身着这款军装爬雪山、过草地,突破敌人的重重包围,闯过一道道险关。由于部队始终在长途行军、机动作战,无后方依托,大多数官兵只在出发前补充了军装,此后未能更换。中央红军在遵义休整期间,随军转移的被服厂加班加点,为每人补充了一套新军装,此后也未能更换。由于长时间行军作战、风餐露宿,到达陕北时,许多官兵的军装都破旧不堪。
各路红军的军装样式是基本统一的,但也有各自的特点。比如,红二、红六军团长征时,条件异常艰苦,只好让各部队自己沿途解决衣物以适应气候变化。由于在西南地区难以找到灰布,红二、六军团的军装多以当地的黑布制作,以至于三大主力会师后,许多人找红二方面军的人就以黑色军装辨认。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时,各部队军装颜色杂乱,但绝大多数人都戴着一顶象征革命的红五星八角帽,表示对革命的忠诚。 □辛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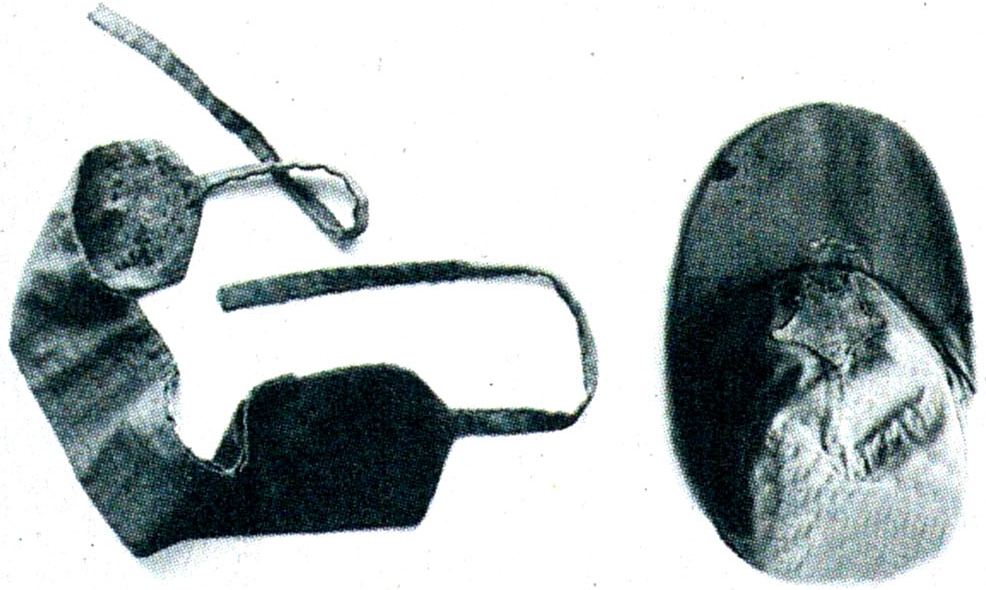
红四方面军的军帽和子弹袋(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二万五千里”是怎样算出来的
一提起长征,人们自然就会想到“二万五千里”,它已成为一个固定词组深深地印烙在人们的脑海中。从某种意义上说,“二万五千里”成为了红军长征的代名词。
那么,“二万五千里”到底是怎样算出来的?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的里程不是在地图上测量出来的,更不是凭空编造的数据,而是有着充分的事实依据的。
“二万五千里”指的是中央红军的行程。1935年10月19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长征胜利结束。当天,时任直属队党总支书记的萧锋在日记里写道,毛泽东对他讲,红军长征“根据红1军团团部汇总,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此后,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等正式文件中,开始使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提法。
从萧锋的日记中可以看出,这个数字是“根据红1军团团部汇总”得出的。但是,由于战争年代的特殊原因,当时的大部分汇总材料未能完整保存下来。现在所能查到的关于红军长征行程的记录,主要来自中央红军红1军团直属队长征行程表及亲历长征的陈伯钧、童小鹏、萧锋等人的长征日记。尽管这些材料是片段的,统计也不完全,但根据红1军团直属队长征行程表就可以确定:红1军团直属队至少走了1.8万里。
此外,在计算红军长征行程时,有几个重要因素不容忽视。
一是长征途中,红军打的是运动战,频繁迂回穿插、重复走路。比如,红4团出草地到班佑后,前进至巴西地区,但隔了一天“又奉命返回班佑,担任警戒任务”。红5军团第37团为保卫党中央、掩护方面军休整,翻过夹金山后,又奉命回翻夹金山,返至盐井坪一带坚守阵地,继续阻击尾随的敌人。
二是红军在行军作战中,还要筹款、做群众工作等,这些都需要走路。比如,萧锋在1934年11月11日写道:“师政谭主任布置在白石渡镇休整几天,要求扩红三百名。我担负扩红和筹款工作,到各连去了解情况,走了六十五里。”筹款、做群众工作是红军的经常性工作,萧锋仅此一次就走了65里,可想而知,这样的行程在整个长征中有多少呢?
三是在长征中,特别是长征初期,红军由于缺少地图,走错路的事经常发生。陈伯钧在1934年12月8日写道:“第38团‘行军方向搞错,以致迷失路途’。”可见,长征中因常走错路而多走的行程,应当也不少。以上诸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增加了红军长征的行程。
长征“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这个“最多的”又是指哪些部队呢?目前现存史料没有提供直接的答案,但经过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走的最多的应是担负侦察、作战、掩护、迂回、穿插等任务最多的基层作战部队。比如,从平查所到八嫖,红3团走了315里,红1军团直属队走了145里,相差一倍多。
可见,这些基层作战部队的行程,要多于领率机关和直属队,这也符合部队行军作战的常理。鉴于此,《红军第一军团在长征中行军和休息的时间统计表》中特别注明:“此表系依军团直属队为准的,如各师另有行军作战等,均不在内,但各师行军作战等时间,均比军团直属队为多”。
红军的长征是在紧张的作战环境中进行的,但走什么样的具体路线,因当时敌情和任务的不同而各不相同。即使相同的出发地和目的地,各部队的途经地点也是千差万别。
在这种情况下,现在重走长征路的人,在大的行军路线上或许能与当年红军基本一致,但却难以到达红军各部队经过的每一个具体地点。而且,80年来,道路也已发生诸多变化,二者已不可能再完全走同一条路。因此,重走长征路的人,用自己所走的里程来计算、验证“二万五千里”,从根本上说都是不科学的。 □王建强 蔡琳琳 李悦
喇嘛走长征——藏族红军干部天宝的故事
红军长征曾经过西南、西北大片少数民族地区,这里的各民族群众接触到红军后,对红军严明的纪律和平等的民族政策产生深刻印象,掀起了一波波参加红军的热潮。据不完全统计,少数民族参加红军的,贵州有1.25万人,四川有5.5万人,甘肃陇南有2000多人,云南扎西有3000多人。一批少数民族红军干部由此诞生。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和政府主席的天宝就是其中之一。
小喇嘛当红军
1935年,红四方面军长征来到阿坝。
“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灭族灭教”……红军到来之前,国民党散布的谣言一时间闹得人心惶惶。不但土司头人和有钱人跑到城里躲避,连普通的藏族群众也有不少人逃到山里。虽说天宝家里穷,三兄弟都还没有结婚,天宝又是个喇嘛,但实在摸不清红军的底细,他还是跟着乡亲们跑到山上去了。
在山上,藏族群众偷偷地观察这支从未见过的被称作“红军”的队伍。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发现红军纪律严明,宁可冒着雨雪风霜挨饿受冻,也不进寺院、不住民房。红军对他们态度友好,尽管言语不通,也总是笑脸相迎,打着手势想同他们交流。红军还把没收土司头人的东西分给穷人。渐渐地,一些胆大的年轻人,也敢和红军接触了,有的甚至参加了红军,天宝认识的一个年轻人还当了队长。天宝也不知道“队长”是多大的官,但知道能管几十号人,今天在这家打土豪,明天给乡亲们分浮财,风光得很。
天宝有点动心了,“他们能当红军,我为什么不能当呢?”没有同父母亲商量,18岁的天宝就报名参了军,当即脱去袈裟,穿上了一套不太合身的半新不旧的军装。天宝的“革命行动”受到红军战士和身边朋友的称赞。
当过喇嘛的天宝懂一点藏文,在参军的年轻人中算个知识分子,因此被任命为副队长,任务是打土豪、分田地,为红军筹集粮草。同年,天宝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红军第一批藏族战士和中共第一批藏族党员之一。
“野菜宣传员”
天宝参加红军后不久调到红四方面军总部工作。1935年8月,他随左路军踏上草地。这是红四方面军第一次过草地。
无边无际的草原,不知道哪里能走,哪里不能走。红军找到一些赶过马帮、走过草地的藏族群众当向导,让上过学、懂汉话的藏族战士当翻译。当时的天宝只懂一点汉话,没有出过远门,当不了向导,只是跟着大家一起走。
部队缺粮,只能挖野菜当饭吃,但草地的许多野菜有毒,红军总部就请藏族同胞帮助把野菜分类绘出图来,印发各部队。当时,总部只有几台油印机,而且缺乏油墨纸张,后来只好采集野菜标本,让天宝和其他几名藏族战士当“野菜宣传员”,拿着各种野菜到各部队告诉大家:这个可以吃,那个不能吃。
筹军粮学文化
不久,天宝调到丹巴藏民独立师政治部任青年部部长。他最重要的工作是为部队筹集粮草。当时,整个丹巴县只有3万多人口,而驻扎在县境内的红军就多达3万余人,此外还有大批骡马也需要饲料。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亲自抓给养问题,派天宝等人直接到寺院里、到土司头人家、到群众中筹集粮草。天宝所在部队第三次过草地前,上级要求每个战士准备15斤粮食。丹巴本来产粮就少,红军几万大军来回过,粮食差不多吃光了,但藏族同胞还是想方设法找粮食。一些寺院把积存多年的粮食和茶叶都拿出来了,连天宝当过小喇嘛的那座小寺院也找出几百斤青稞。
为了北上抗日的需要,天宝所在部队奉命组成一支少数民族革命武装——“番族人民自卫军”。这是一个师的建制,天宝被任命为党代表。这支特殊的部队担负着特殊任务,时而走在前面为大部队开路,时而在后阻击追兵;时而护送伤病员、收容掉队或迷路的战士,时而去找粮食、找牛羊。
天宝当上了领导干部,如果再不认识汉字、不会说汉话,必然影响到工作。他一边行军打仗,一边学文化。天宝的步枪和背包上都写着汉字,后面的人看着他的学,天宝则看着前面的学,会念、会写、记住了,又换一个字。天宝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凡是学过的字和话,大部分能马上记住。不久,他就能向藏胞宣传党和红军的宗旨、民族政策和抗日救国的方针。等走完漫漫长征路,天宝已经完全掌握了汉语。
毛泽东为天宝取名
红军到达陕北后,天宝到中央党校学习。一次,毛泽东在党校讲完课,问天宝:“你叫什么名字?”天宝回答叫桑吉悦希,“桑吉”是佛祖的意思,“悦希”是宝贝的意思,“是活佛给我取的,有点迷信色彩”。
毛泽东笑着说:“了不得,了不得嘛!又是佛爷,又是宝贝!”
毛泽东的兴致很好,想了想,又对天宝说:“长征时我到过你们的家乡,那里的藏胞对长征的胜利是有贡献的。汉族有句古话,叫物华天宝,也就是和你那个‘悦希’差不多。我给你取个名字,就叫天宝吧!”从此以后,“天宝”这个名字就在中央党校和延安传开了。 □尹黎 遇际坤 孙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