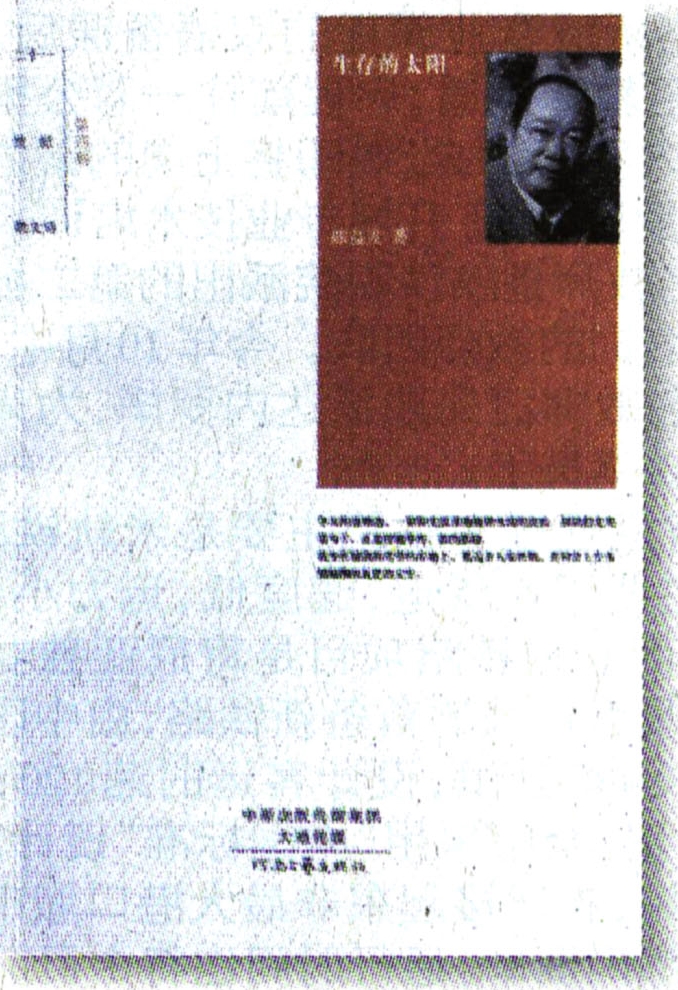
我和陈益发是隔墙而居的邻居,如果两人同时开窗望景,我看到的画面上有他,他看到的风景中也会有我。
但这种如果还没有“变现”过,原因是他还是中铁二十局集团的在岗职工,那是一支以当年的铁道兵为班底的筑路大军,铁路、高速公路通吃,威风八面驰誉四海!
益发说:我在中铁干了二十多年,大部分时间在施工现场。现场多在崇山峻岭,大漠荒原。青藏铁路就是我们曾经参与修建的,我们生活在可可西里,打通了世界最高的风火山隧道。我说:前年我去过青海格尔木,上到昆仑山口。站在莽昆仑的山口上,我看到火车从山顶呼啸而过,壮观啊!可山口太高了,我心慌气短,只待了十几分钟便落荒而逃!
益发平静地说:山口海拔4767米。我们施工的地方比那还高,接近5000米,我在工地上工作了3年多!我目瞪口呆,脑海中蹦出一个名词,“无人区”!那里有人类“生存的太阳”么?
我忽然明白了,益发为何要把他即将付诸出版的散文诗集命名为《生存的太阳》了。
我是好奇,想看看这位经年累月奔走在严酷生存环境中的筑路人是怎样用文字解读“生存的太阳”。
《生存的太阳》是一本散文诗选集。有人说:散文诗是“散文的诗”和“诗的散文”,我认为:不然!
散文诗是散文与诗“嫁接”出来的品种,具有诗与散文的“两栖”特征,散文诗既吸收诗的表现主观心灵和情绪的功能,也吸收了散文自由、随便抒怀状物的功能,并使两者浑然一体,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性。散文诗是抒情散文与抒情诗交叉心汇融合后“优生优育”的文学骄子。虽然不能排除“父母”的遗传基因,但新生儿一旦脱胎而出,儿女就是儿女,父母就是父母。就文学本体而言,没有个性就没有其“生存的太阳”!然而,就创作者而言,不熟悉诗与散文这两种文体,就很难创作出优美的散文诗。我想,这大概也是散文诗与诗和散文的“量化比较”中处于“劣势”的缘故吧?但“量小”却并不代表“质劣”,有时恰恰相反,譬如:一车沙土和一两金子……
落雪的日子,我躲在书房读《生存的太阳》。
全书收录了作者创作的130首散文诗,按内容分成了4章,即:《故土情深》《游走浮云》《生命本真》《自然风情》。
“我们就这样走着。不知不觉,日子,竟被我们走成身后一岭一岭的坡坎。而滩地,一道一道的,也舒展了,我们撂置的心事。”
——《故土情深》
“冬天的池塘边,一抹阳光温柔地梳理水波的流纹。树枝们光秃着身子,正羞涩地孕育,春的新绿。”
——《池塘边的思念》
以上是我从书中信手捻来的句子,是典型的散文诗,以比散文更简约的文字截取生活的场景、状物叙事;以比诗更飘逸的姿态释放作者心灵的感动,一如行云流水,空灵而热烈。而这样的句子,这样的段落在全书中俯首皆是!贯穿全书的是作者对故乡的一石一草一滴泉水,对父老乡亲的一颦一笑一个眼神,对自己生活过工作过游走过经历的山山水水、日日夜夜、风风雨雨的那种刻骨铭心的恋情。这种感情,顾盼之间便会“穿胸而过”,入梦时节也会汩汩作响,从而激起心海层层涟漪,于是那每一滴水——泉水或者泪水,便幻化成了优美的散文诗。
因为,那一切,都是他、一个关中汉子、一位筑路英雄“生存的太阳”,也是诗人陈益发文学生命中的“太阳”!
古人说:“文章不是无情物”。
这话对,但似乎还不硬朗,不如说“文章本是传情物”更贴切。不知妥否?
那么作家的劳动就是“从真情出发”向社会传递真情。桌案上摆放的这本《生存的太阳》即为例证。
作家的真情从哪里来?是从生活的源泉里来么?答案是:是。但又不是“唯一”。理由是:“生活”是客观发生和存在的现实,而写作是写作者受主观意识掌控的个性劳动。当写作者被社会客观现实所感动、刺痛甚至不排除被伤害,情感之火被“引爆”了,情感之水“决堤”了,真情就熊熊燃烧了,奔流而下了!这么说是因为现实中的确有为数不多的“写手”早已变成了麻木不仁、“一刀扎不出血”的稻草人了。但这并不表示这些人写不出东西,能写,并且还能时不时地换些凤冠霞帔似的大奖回来。奇怪吗?不奇怪。须知,“虚情假意”是一种社会需求,稻草人也能唬住野雀儿!
好了,言多有失,就此打住吧。
□徐剑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