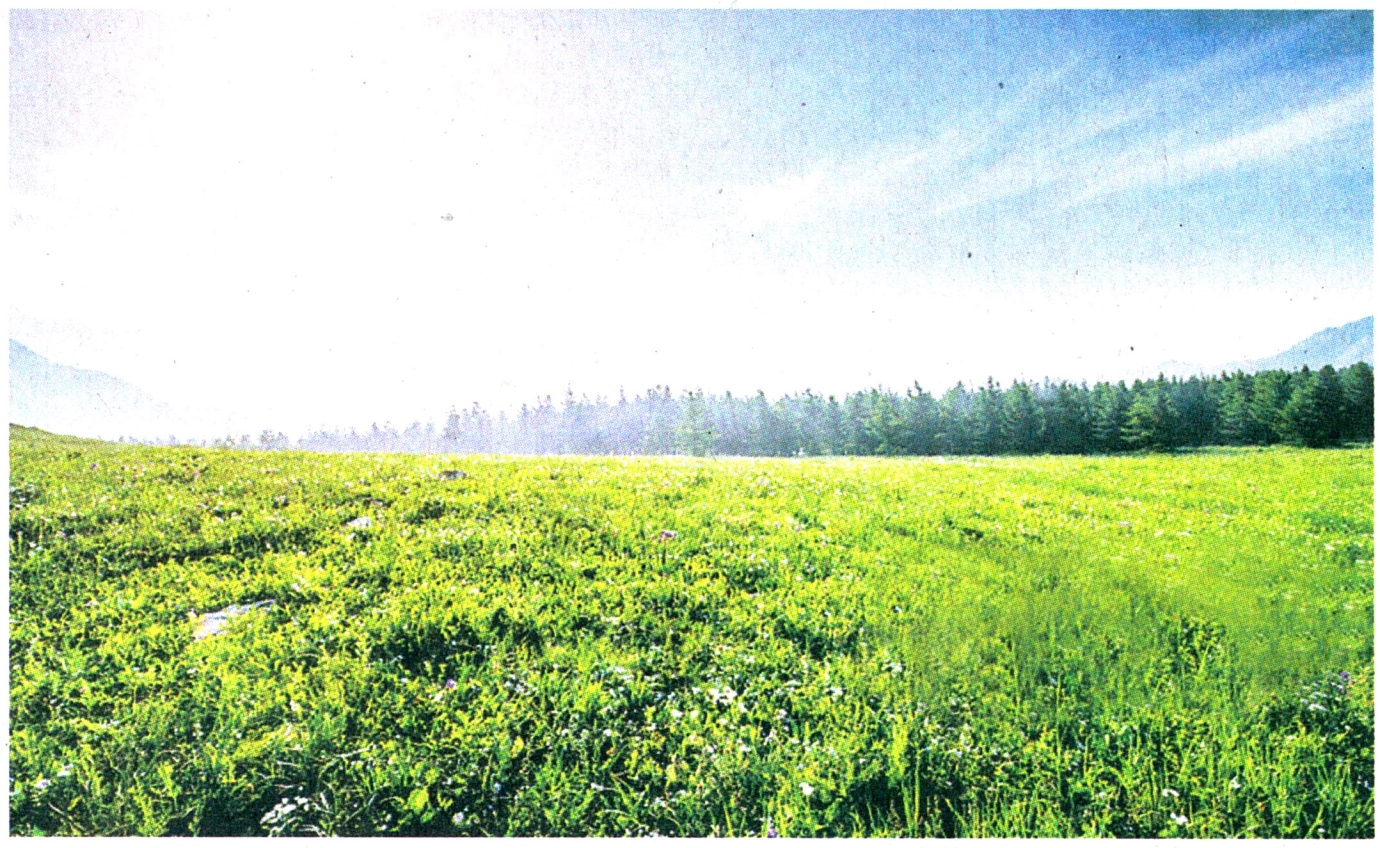□林淼
说起布拉格,头脑中闪现的是夕阳余晖笼罩下童话般的美丽城堡,是墙皮剥落的古老钟楼与精美别致的自鸣钟,是广场角落里喝着咖啡凝望远方的迷离眼神,是街道拐角处不期而遇的邂逅,悠久、唯美、浪漫,无一不是布拉格的代名词。
记忆中这些画面,其实来自于某部电影或电影中的片段。我未到过布拉格,也未曾听身边的朋友聊起过布拉格,甚至没有抱着学习的态度去了解过布拉格。布拉格就这样深藏在记忆的角落里,盖满灰尘,而我却从未想到去触摸它,擦拭它,看清它。直到某一天,我在读余秋雨先生散文集《行者无疆》中,无意间看到它。短短的四千字,仿佛一根火柴,点燃我内心对布拉格的渴求,我急于想知道它的一切,看清它的全貌,而当下也只能通过作家的文字、网上的资讯,试着去了解它、探究它。
余先生笔下的布拉格,不似常人眼中容貌娇艳、衣着华丽、徒有外表的时髦贵妇;更似经过岁月洗礼、命运坎坷,仍能执着于一份恬静与美丽、淡定与从容的绝代佳人。时间的沙漏细数着布拉格无法逃离的过往,岁月的沧桑见证布拉格曾经的辉煌与忧伤。
广场中央胡斯的塑像,向世人述说着布拉格曾经的愚昧与残暴。1415年,布拉格大学校长胡斯,只因发表反对教会剥削普通民众的言论,被教会以“异端”的罪名烧死在广场上。可悲的是,无知的民众非但没有奋起反抗,反而是暴行的参与者和欢呼者。火刑当日,看热闹的市民人山人海,他们中间被尊为“德高望重”的人,还享受到添加柴草的殊荣。愚昧与无知,蒙蔽布拉格人的双眼,但终究没有泯灭正义的灵魂。1419年,暴发了一场以胡斯命名的大起义,为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写下了序篇。既是在近代,耀武扬威的外国坦克也曾轰隆隆驶过布拉格古老的街道,民众的抗议呼声也曾打破古城的宁静。但布拉格相信“是外力总要离开,是文明总要留下,转眼之间,满街的外国坦克变成了外国游客”,这是布拉格人的哲学。
布拉格是一座欧洲历史名城,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在这个城市出生或生活过的名人数不胜数,享誉世界的名人,如音乐家莫扎特、斯美塔那、德沃夏克,作家弗兰茨·卡夫卡、米兰·昆德拉、哈谢克等等。在这耀眼的名单里,作家卡夫卡和剧作家哈维尔起伏跌宕的人生故事,令人难忘。
初识卡夫卡,是通过日本作家村上春树长篇小说《海边的卡夫卡》。当时误认为书中的田村卡夫卡的原型就是捷克作家卡夫卡,后来了解到村上更多是借用了卡夫卡在捷克语中“乌鸦”的意思,暗示小说中主人公是个乌鸦少年,与东京是一个乌鸦遍布的城市相契合。而作家卡夫卡被称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和大师,他的大量作品是在他死后才出版发行,被世人所认识。令我震惊的是,这样一位文学大师,本职竟是一位保险职员。25岁任职,39岁因病辞职,41岁去世。可以说,保险工作与文学创作,伴随着卡夫卡度过短暂的一生。让我们仿佛看到,一个孤独忧郁的年轻人,白天在办公室内处理着事无巨细的保险业务,夜晚栖身在水蓝色小屋的简陋书桌旁,成就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作品,这是怎样一种巨大的精神动力。卡夫卡已经把创作看作一种生存方式,一种生命燃烧的过程。他在日记曾写道“我内心有个庞大的世界,不通过文学途径把它引发出来,我就要撕裂了!”
剧作家哈维尔,是通过余先生《哈维尔不后悔》一文中相识的。在文中,余先生为哈维尔亮出两张耀眼的名片:高水准的剧作家、受国民拥戴的捷克总统。两张名片,两种身份,拎出哪一个都是需要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而在哈维尔身上两种身份同样成就非凡,同样精彩夺目,让人敬佩。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哈维尔创作的“荒诞派”戏剧,活跃在布拉格大小剧场的舞台上。那时,哈维尔已经成为戏剧界、文化圈内的名人了。九十年代,捷克掀起“天鹅绒革命”后,哈维尔就任捷克第一位民选总统。作家当总统,去治理一个国家,听着都叫人替他捏把汗。但能够连任两届,当政十年,足以说明了他的政绩与威望。哈维尔说过:“成功的政治追求正派、理性、负责、诚恳、宽容。”“一个国家的公民在文化教养和举止习惯上的衰退,比大规模经济衰退更让人震惊。”哈维尔执政理念,成就一个平稳、包容、文化的国家。
从卡夫卡到哈维尔,非凡的人物成就了布拉格的传奇。而白色的塔尖、红色的屋顶、古老的大桥、奔腾的河流,又为传奇的布拉格增添了浪漫的情调,披上了五彩的面纱。布拉格,如那在水一方的美丽佳人,正等待我飘洋过海,掀开面纱,目睹她的花容月貌,领略她的绝代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