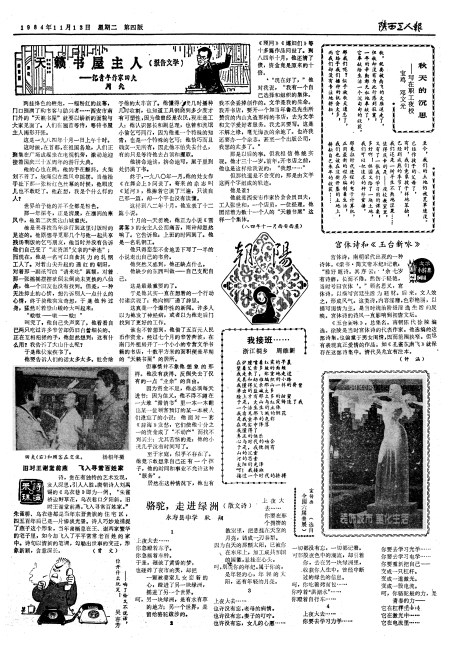
天籁书屋主人(报告文学)
——记青年作家田夫
周失
两挂绛色的鞭炮,一幅粉红的丝幕,门口围满了购书客与助兴者……西安市南门外的“天籁书屋”就要以崭新的面貌与大家见面了。人们在翘首等待,等待书屋主人揭彩开张。
这是一九八四年十月一日上午十时。
这时候,在首都,在祖国各地,人们正聚集在广场或凝坐在电视机旁,激动地迎接着国庆三十五周年的游行大典。
他的心也在跳。他的手在颤抖。火柴划不着了,炮绳似在微风中摇摆。当他抬手扯下那一张粉红色丝幕的时侯,他眼皮儿也不敢眨了。他在想,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世界给予他的并不全都是粉色。
那一年深冬,正是清晨,在凛冽的寒风中,他第二次抵达山城重庆。
他是来寻找当年步行到这里讨饭时的足迹的。他原想寻觅那几个与他一起共享残汤剩饭的乞丐朋友,他当时并没有告诉他们自己受了“走资派”父亲的“牵连”;而现在,他是一名可以自食其力的轧钢工人了。对着山尖升起的通红的朝阳,对着那一副纸写的“请来吃”匾额,对着那一张摇摇摆摆欲倒未倒尚未更换的八仙桌,他一个旧友也没有找到。但是,一种无法抑止的心情,想告诉别人一点什么的心情,终于使他突发奇想,于是他转过身,猛然对着崇山峻岭大叫起来:
“嗷嗷——嗷——嗷!”
叫完了,他自己失声笑了。他看看自己两只吃过许多辛苦却仍旧白哲细长的、正在互相扭搓的手,他忽然想到:这有什么用?我告诉了大山什么呢?
于是他伏案疾书了。
他要告诉人们的话太多太多。社会给予他的太丰富了。他懂得小麦几时播种几时收割,也知道工具钢烧到多少度才有可塑性,因为他曾经是农民,现在是工人;他认识部长和副总理,也曾和流氓小偷乞丐同行,因为他是一个特殊的知青,也是一个特殊的乞丐;他恰巧而且确实一无所有,因此他不怕失去什么,有的只是等待他去占领和攫取。
他拚命地读,拚命地写,屋子里到处扔满了书。
终于,一九八〇年一月,他的处女作《在舞会上》问世了,寄来的杂志叫《延河》,他捧着它读了三遍,只读自己那一篇,却一个字也没有读懂。
这样到八二年十月,他发表了十二篇小说。
十月的一天傍晚,他正为小说《雪雾雾》的女主人公而痛苦,闹钟却忽然响了。它告诉他:上班的时间到了。他是一名轧钢工。
他只得恋恋不舍地丢下写了一半的小说走出自己的书房。
他突然又感到,他还缺点什么。
他缺少的东西叫做——自己支配自己。
这是最最重要的了。
于是他其实一直在想着的一个行动付诸实现了:他向钢厂递了辞呈。
这真是一个爆炸性的新闻。许多人以为他发了神经病,或者以为他走后门找到了更好的工作。
谁也不曾想到,他借了五百元人民币作资金,经过七个月的辛苦奔波,在南门外租房开了一个小小的专营文学书籍的书店,十数平方米的面积便是早期的“天籁书屋”的居所。
但事情并不象他想象的那样。他没有获得、反倒失去了仅有的一点“业余”的自由。
因为资金不足,他必须每天进书;因为信义,他不得不蹲在一大堆“滞销书”里一本一本翻出某一位顾客预订的某一本被人们遗忘了的小说;他面对一套《辞海》发愁,它们使他十分之一的资金成了“不动产”而找不到买主;尤其苦恼的是:他的小说几乎没有时间写了。
至于家庭,似乎不存在了。他竟不敢想象自己还有一个孩子,他的时间和事业不允许这种“服务”。
居然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有《顾问》《孀妇们》等十多篇作品问世了。到八四年十月,他还清了债,资金竟是原来的十倍。
“现在好了,”他对我说,“我有一个自己选择和组织的集体。我不会丢掉创作的。文学是我的生命。我开书店,要开一个如当年鲁迅先生所赞赏的内山丸造那样的书店,去为文学和文学爱好者服务。我尤其要写。这是不解之缘,毫无悔改的余地了。也许我还要办一个杂志,甚至一个出版公司,我想的太多了。”
那是以后的事。但我相信他能实现。他才三十一岁。前年,开书店之前,他也是这样给我说的:“我想……”
但那轨道是不会变的,那是由文学这两个字组成的轨迹。
他是谁?
他就是西安市作家协会会员田夫,工人张世和,一个店员,一位经理。他团结着为数十一个人的“天籁书屋”这样一个集体。
(八四年十一月西安西屋)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