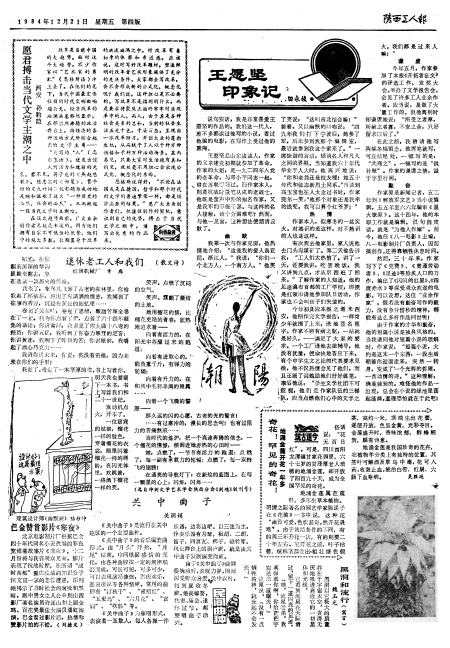
王愿坚印象记
田永桢
说句实话,我是非常喜爱王愿坚的作品的。我们这一代人,差不多都读过他写的小说,看过他编的电影,在写作上受过他的熏陶。
王愿坚是山东诸诚人,作家的父亲建党初期就参加了革命。作家的大姐,是一九二四年入党的老革命,与邓小平同志一起,曾在苏联学习过。而作家本人,则是抗战时投笔从戍的老战士。他既是蜚声中外的知名作家,又是我军的军级干部。与这样的名人接触,该十分困难吧?然而,与他一见面,这种想法便烟消云散了。
幽默
我第一次与作家见面,他热情地介绍:“这是我的爱人翁亚尼,浙江人。”我说:“你们一个北方人,一个南方人。”他笑了笑说:“这叫南北结合嘛!”接着,又以幽默的口吻说:“四九年我们打下宁波后,她参了军,后来参到我那个编辑室,最后就参到我这个家来了。”一席恢谐的言语,顿消名人和凡人之间的界限。当知道我六十年代毕业于人大时,他高兴地说:“你和老翁还是校友哩!她五十年代和张志新烈士同系。”当谈到高玉宝也在人大念过书时,作家莞尔一笑:“他那个对象还是我牵的线呢,我可以算个红爷罗!”
热情
作家本人,似寒冬的一盆炭火。对熟识的是这样,对不熟识的人也是这样。
有次我去他家里,家人说他去门头沟煤矿了。第二天他告诉我:“工人们太热情了。讲了一天,还要我讲,吃罢晚饭,我又讲到九点,才从京西赶了回来。”了解作家的人知道,他的足迹遍布首都的工厂学校,即便是红领巾请他参加队日活动,作家也不会叫孩子们失望的。
今年初夏应本报之邀来西安,他刚作完文学报告,一群青少年就围了上来,请他签名题字。作家不顾有病之躯,一站就是好久,一一满足了大家的要求。一个工厂请他去做辅导,他没有犹豫,便愉快地答应下来。有个中学生文艺社的代表要求见他,他不仅热情会见了他们,而且还题了词勉励他们好好练笔。事后他说:“学生文学社团不可忽视,他们是作家队伍的三梯队,应当点燃他们心中的文学之火。我们都是过来人嘛!”
谦虚
今年五月,作家参加了本报《开拓者征文》的评选工作,发奖大会,举办了文学报告会,会见了许多工人业余作者。应当说,是做了大量工作的。但他离别时却谦虚地说:“所受之者厚,所献之者寡,不安之余,只好留求以后了。”
在此之前,我曾请他写两幅条幅留念。他挥笔就写,可在结尾处,一幅写的是:“共商之”,一幅写的是“供补壁”。作家的谦虚之情,溢于字里行间。
勤奋
作家原是新闻记者,五二年到《解放军文艺》当小说编辑,五五年至六六年编审《星火燎原》。这十四年,他的本职工作就是编辑。说句俏皮话,就是“为他人作嫁”。而今,他任《八一电影》主编,八一电影制片厂负责人,因而搞创作,还得靠牺牲休息时间。
然而,三十年来,作家写下了《党费》、《普通劳动者》、《足迹》等脍炙人口的力作,编出了《闪闪的红星》、《四渡赤水》等深受观众欢迎的电影。可以设想,这位“业余作家”,假若没有勤奋写作的毅力,没有争分惜秒的精神,哪能有这么多好作品问世呢!
由于作家的才华和勤奋,他的短篇小说是独具风格的。当我请问他对短篇小说的理解时,作家说:“短篇小说,大约是这末一个东西:一段生活朝着你迎面走来,突然一转身,变成了一个光辉的哲理,一首动情的诗。”这种理解,确是独到的。难怪他的作品一出现,总会在小说的绿池里荡起涟漪,道理恐怕就在于此吧!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