荧屏背后
——西安电视台散记
郑升旭
一、五个播音员
早晨,莲湖公园幽静的湖畔,不时传来一声声奇怪的吆喝,“啊——啊——啊——”“咿——咿——咿——”声音拖得很长,而且高低有序。是些歌唱家在练声么?走近了看,四五个穿着风衣的年轻人,扬着脖子,个个神情专注。他们就是每天晚上在屏幕上和观众见面的西安电视台播音员们。
为了使观众能得到美的享受,听到悦耳的声音,他们每天一大早来这里练声。公园免收他们的门票,在这一点上,他们享受了“特殊”的待遇。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晚上好!现在介绍本台今天晚上的电视节目……”屏幕上那位身材硕长,眉清目秀的小伙子,就是今天充当练声教练的焦振峰。他今年二十四岁,十九岁参军,一直在某部话剧团工作,算是受过一定专门训练的,发声指导就由他充当。从形象看,他是本台小伙子中最帅的一个,台里的人都称他为“英俊小生”。原来,荧屏上的“图像”,是电视台十分讲究的一个条件。就象钢琴演奏家讲究手指,乒乒球运动员讲究手臂。可惜小伙子俊气得过了头,竟长出两个酒窝来,损了男子气。为此,小伙子苦恼了。他去请教电影演员,说是可以通过练,使两颊的肌肉平衡起来。于是,在吃饭、说话、凡用面部肌肉的时候,他都不忘记控制它们的运动。天长日久,功夫不负有心人,那两个酒窝,竟似乎消失了。
但形象并非播音员必须具备条件的全部,更重要的,是文化修养,这决定你对播出内容的理解。决定你对自己声音神态的处理。一句话,决定你的气质。如果说,形象是一个人的外在美,气质就是一个人的内在美。这里的播音员有一个共同的嗜好,就是爱读书。就拿小焦来说,他星期日除了玩一阵摩托之外,就把精力全部用在读书上,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论文集》,读金山的《美学散步》等等。他说,我不能一辈子满足于做一架说话机器,至少要明白为什么编导要让我这么说,这么做。
播音员的工作有乐也有苦。和小焦一起主持“下周节目预告”的胡晓青向人说,每晚,她坐在电视机前,能亲眼看到自己的节目,就是她最大的幸福。她也是前年电视台招聘时,两千多名应聘者中,有幸被录取的四名之一。她曾为此欢腾过,笑过,但以后也为此痛哭过。她,瓜子脸,中等个儿,在屏幕上显得朴实、娴静。乍看,有二十五六,其实才十九岁,是这里最小的一个。初到电视台,每晚要播音、剪辑,有时还要给电视剧配音,稿子一背十几张,这个节目刚上完,又要上那个节目,累得她常常喘上一阵子气,才能发出声音来。她进台时刚刚高中毕业,穿一双大头鞋,一件军大衣,连修饰尚不懂呢,贪玩的脾性自然也没改,有时还迟到,挨领导的“尅”。为此,她哭了一次又一次,躺在长椅上哭,站在楼顶上哭。哭着哭着,她长大了。台领导常说,小胡现在播出越来越象回事了。
然而,那位仅比晓青大一岁的苏静,就显得老练多了。她不仅图像好,而且神态亲切大方,声音富予感染力。即使在屏幕下,她也满象小胡的大姐姐。现场采访奈良市市长的节目中,她发问得当,插话得体,不卑不亢,庄重有礼,博得中外人士的好评。这是屏幕前后难得的形象统一。另一位男播音员,叫孙石沙。这小伙长得有点虎实,大脑袋圆脸,大眼,阔嘴,用句时髦话说,颇具“刚阳之气”。到了屏幕上,他大方、朴实,也别有一番风度。
这里真正的大姐姐是三十六发的老播音员庞薇。她虽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却是一位典型的“事业型”妇女。白天,她除参加那些需要灵活应对,难度较大的现场播出外,还得帮助四个年轻的伙伴,提高业务水平。她爱人是一名机修工,她有时在外县采访,一连几天回不来,爱人只好用一双男子汉摆弄机器的大手,为孩子们穿衣做饭。每当说到这里,说到爱人对她的支持,说到孩子们对她的爱和她自己对家庭的歉意,她总是眼圈微微泛红。
二、开拍啦
播音员在摄像机前的工作,仅仅是电视台整个工作量的几十分之一。
为了了解拍摄电视的全过程,我随电视台一个采访组一起出发了。算是采访采访者吧。报刊记者采访一般是“单兵作业”,而电视台却得出动一个组,常常是三个人,一名文字记者,一名摄像记者,一名播音员。
有人认为,拍电视就和照像一样,背着机器,走到哪照到哪,象星期天打鸟那样随便。其实不然,单是那二十多斤的摄像机,一只手托上几个小时,就够人受的。
今天的摄像记者叫权明,三十几岁,红红的脸膛,一看就是一个开朗、豪放的人。他紧张地拍着电视,但一闲下来就给我讲解。他告诉我,摄像是基本功,要求机子不能抖动,否则,电视屏幕上看到的画面便会抖动。来电视台前,他在一所高校电教室里搞录像。从那时起,他就开始练习单臂托举。一次托五块砖,开始托十几分钟,以后增加到半小时、一小时,不管严冬酷暑,天天如此。渐渐地,手臂有劲了,功夫体现在了屏幕上,有时连续托举五六个小时,也可以做到不抖,不晃。拍电视原来竞这么难哪!
“其实还有更难的,”他说,“前面那叫笨功夫,构图、焦距、角度……才算巧功夫。”比方搞新闻录像,你得首先考虑每个镜头以谁为主,不断转换角度;其次得一边拍,一边变动焦距,不然该突出的模糊了,该模糊的突出了。举例说吧,拍一个学生点烟抽的特写,他身后的画面要模糊一点。然后再突然将焦点从孩子身上推到模糊的背景上,背景变清晰了,显出了沮丧的老师。这样便具有了特殊效果。
而这一切构思和意图,都要由文字记者安排。文字记者在这整个活动中起着“轴心”的作用。他既是编导,又是“制片人”,又是“场记”。既要安排摄像记者的拍摄计划,还要撰写说明词和台词,指导播音员及其它采访对象的活动。回到电视台以后。还要按照自己的意图,参与剪辑和制作。一个节目拍摄的成功与否,表现了文字记者的构想和处理水平。
和我同行的文字记者叫黄勤,最多三十岁的样子,不爱说话,似乎是腼腆,又似乎是骄傲。然而到了拍摄现场,他马上象换了一个人,跑前跑后,朝气蓬勃,时而嘱咐播音员运用什么语气,什么意态,时而安排摄像师应选什么角度,拍什么细节,“好——”“停——”语气果断,指挥若定,一下子,我对他刮目相看了。我想,西安电视台这样的文字记者有十几个,个个都有较强的战斗力,难怪他们拍的电视节目人们喜闻乐见,满透着新鲜气息呢!
三、“大后方”
技术区走廊里铺着红地毯,既干净,也避免了噪音。这里光线有些暗淡,加之来往走动着匆匆的人影,叫人一下子想起阵地上的“战壕。”如果将屏幕上的播出叫做“前沿阵地”,这里便是真正的“大后方”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在这里完成。拍回的素材仅是半成品,需要在这里剪辑、配音、抠像,制成成品,然后发射出去,才能为全市的电视机接收。
我首先进入剪辑室。这里有一架台桌式的木制器具,一分为二,一半叫剪辑台,上边放一台剪辑机;一半叫控制台,上边放一台控制机。一位三十岁左右的男同志正在指挥剪辑。别人告诉我,他叫周朴,播出部负责人。而另一位女青年坐在控制台前正在具体操作。随着周朴的指挥,我看见,两幅一样的彩色画面出现在两个不同的屏幕上。
所谓剪辑机,实际上就是两台录像机,一台装着素材带,一台装着空白带。机器开动了,前一个机子放,后一个机子录。剪辑员严密注视着两个屏幕,根据需要进行取舍。需要的,录在空白磁带上,准备播出;不需要的,让机器空转过去。今天,他们剪辑的是一部由中央电视台拍摄的西湖风景片。忽然,在西子湖畔出现了我们熟悉的西安电视台播音员苏静姑娘。她面带微笑,用甜润的嗓音向我们介绍西湖的风光。这是怎么回事呢?扭头一看,我才发现,隔着一道玻璃墙,苏静着一身白色播出服,面对麦克风说着话。他们向我介绍说:“那就是我们的演播室。”当节目中间需要插入本台播音员的解说时,录像机便转向隔壁演播室,这就叫“抠像”,意思是把播音员的图像嵌入节目中。
周朴笑着说:“我们是新台,一切都因陋就简,比方那演播室——”
我随他踏上演播室的红地毯,向四周一看,没有吸音壁,没有布景,仅有几盏灯光。甚至连普通照像馆都不如。
“奇怪吗?”他接着告诉我,刚才看到的台桌一类的木制器具,就是他们亲手做的,还有打字幕用的升降机、提示器,也都是“土制”的。
很难令人置信,就是靠这些东西,他们竟然搞成了每周七天的自办节目!而且,按照规定,每天自办新闻节目超过十分钟,编制要求要达到一百人,他们呢,当然不止十分钟,却仅有五十七人,而且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年轻人。
在中心控制机房,六名工作人员以手工代替电脑,以几元钱的电子表代替几十万元钱的铯钟,监视、调节画面。
在发射室里,工作人员一连数小时趴在那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机器,每一秒钟的疏乎都可能造成重大的责任事故……
这里既不可能“露脸”,也不可能“出名”,然而他们却越干越有滋味。甚至很少有星期天。拿播出部长周朴来说,调到电视台两年多,还没有休过一个礼拜天。
呵,这一群年轻人!呵,这就是青春! (林积令题图 周朴摄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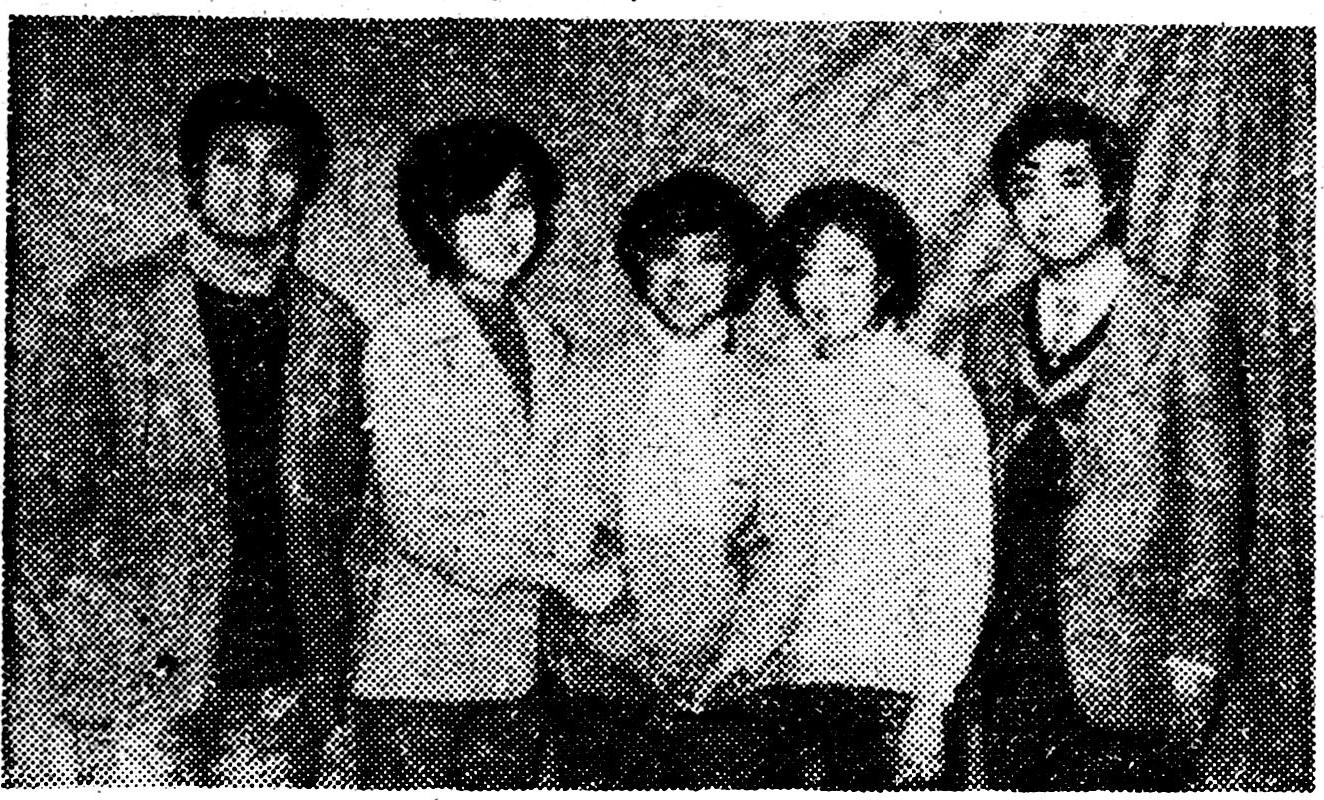
西安电视台播音员。从左至右焦振峰、苏静、庞薇、胡晓青、孙石沙。

西安电视台剪辑人员在工作。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