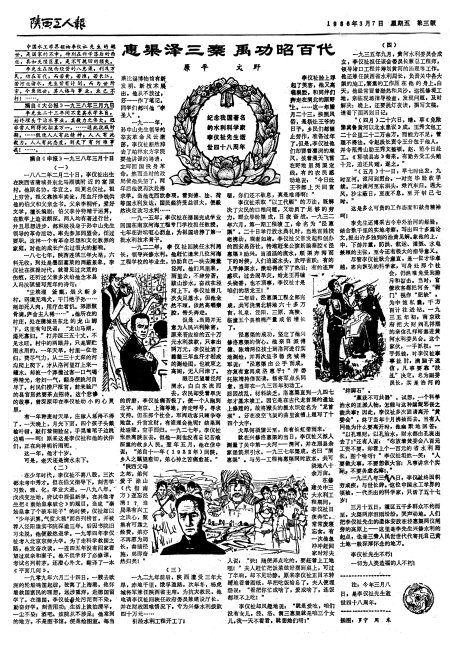惠渠泽三秦禹功昭百代
原平文野
纪念我国著名
的水利科学家
李仪祉先生逝
世四十八周年
中国水工学界领袖李仪祉先生的逝世,是国家的不幸,特别在科学落后的西北,真如天陨巨星,是不可挽回的损失。
李先生在陕西经营的八惠渠,利及万民,功在百代,而若黄,若淮,若长江,若河北诸水,先生皆有计划,而为世所宗。今虽逝世,其人格与事业,业已不朽!……。
摘自《大公报》一九三八年三月九日
李先生二十三年间不变其求学本旨,始终埋头于治水事业,其毅力之伟大,迥非常人所得比拟其万一。……适此抗战时期,……假使人人有此精神,人人有此毅力,人人有此态度,则天下有何难事哉!……。
摘自《申报》一九三八年三月十日
(一)
一八八二年二月二十日,李仪祉出生在陕西省蒲城县东北马湖镇附近的富原村。他原名协,字宜之,后更名仪祉。祖上穷苦,祖父靠推车卖瓮,用血汗挣钱供他的伯父和父亲念书。父亲李桐轩,爱好文学,擅长编剧;伯父李仲特精于运算,在数学上造诣颇深。两人均有著述行世,并且思想进步,都积极投身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活动,率先参加同盟会,任过要职。这样一个有革命思想和文化教养的家庭,对他的成长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一八七七年,陕西连续三年大旱,六料无收,到处是墨面蒿菜的凋蔽景象。李仪祉在孩提时代,就看见过灾荒的伤痕,还听过父亲多次给他念本县人冯汝骐描写荒年的诗句:
“尘埃埋釜甑,烟火断乡村。四境无鸡犬,千门绝子孙……剜却死人肉,用疗生者饥。郊原骸骨满,庐舍主人稀……”。他所在的村庄,处在蒲城县东北的龙山脚下,这里有句民谣:“龙山马湖,渴死寡妇。”打井深三五十丈,不见水旺。村中的两眼井,只是窖贮雨水用的。一年天旱,村里一位老妇,费尽气力,从二三十丈深的河沟爬上爬下,才从洛河里打上来一罐水。却被一个莽撞过客一口气喝得精光,老妇一气,翻身便跳河自尽了。村民们捞尸报官,前来验尸的县官居然要茶点招待。这个悲惨的故事,曾深深印在李仪祉幼小的心灵里。
有一年种麦时天旱,庄稼人记急得不得了,一天晚上,月光下面,四个孩子头戴榆叶帽,敲打着铜脸盆,手晃着苇子边跳边唱一呵!原来这是李仪祉和他的伙伴们,正在向神明祈雨呢。
这一年,他才十岁。
可是,老天还是滴水未下。
(二)
在少年时代,李仪扯不喜八股,三次都未考中秀才。但在伯父指导下,刻苦学习数、理、化,学业大进。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始,府试中提倡新学,在其他考生把《秦始皇拿破仑》的题目,当成“秦始皇拿了个破车轮子”的时候,仪祉却以“少年识算,气度大雅”而名列榜首,并被荐人泾阳崇实书院深造三年。后因书院旧习未脱,他便毅然退学。一九零四年李仪祉考入北京京师大学。为了走科学救国之路,他发奋攻读,一连四五年没有回家看望过双亲和妻子。他不但学好了必修课,考试名列前茅,还潜心外文,翻译了一本《平面几何》。
一九零九年六月二十四日,一艘去欧洲的轮船鸣笛起碇,驶离了上海港,他怀着救国富民的理想,远涉重洋,赴德国留学了。在德国,李仪祉身处污泥而不染,勤奋好学,刻苦用功;生活上淡泊清平,一尘不染;酒吧、妓院从不涉足;他常到的地方,不是图书馆,便是绘图室。每当莱比锡博物馆有薪发明、新技术展出,他从不放过,还一一作了笔记。同学们都叫他“李圣人”。
一九一一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风云激荡,李仪祉断然辞去了柏林东方学院要他讲课的聘请,立即回国投身革命。然而当时的政局使他失望了,两年后他便再次赴德求学。当他在西欧参观,看到德、法、荷等国水利发达,国民经济受益很大,便毅然决定改习水利……
一九一五年,李仪扯在德国完成学业回国在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担任教授,七年在讲坛呕心沥血,为祖国培养了第一批水利技术骨干。
一九二二年,李仪祉回陕任水利局长,领导兴修水利。他赶忙请来几位河海工程学校的毕业生,协助自己一块去测量泾河。他们风里来,雨里去,不辞劳苦,跋山涉水;奋战在泾河上下。李仪祉曾几次失足落水,但他全然不顾,依然高唱秦腔,带头奔走。
但是,当局并无意为人民兴利除害,原来答应给的五十万元水利拨款,只拿出两万元,李仪祉洒了整整三年血汗才制成的测绘图,也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了。
眼巴巴望着泾河渭水,白白东流而去,农民却受着旱灾的折磨,李仪祉痛苦极了,便一个人跑到北平、南京、上海等地,奔走呼号,寻求支持。但在那个社会,军阀政客只顾争夺地盘,升官发财,有谁理会他呢?结果到处碰壁,空手而归。一九二七年,李仪祉怅然离陕东去。但他一刻也没有忘记苦难深重的故乡人民。翌年五月,他在信中说:“弟自十一年(1922年)回陕,乡人之瞩望愈切,弟心神之苦痛愈甚。”“陕西父母之邦,弟何爱于涂山(代指南方)遂忘泾渭!?当局果有兴工之决心,聚集有可靠之经费,弟亦不再愿为局长,畚锸径施,弟即奋然归矣!”
(三)
一九二九年前后,陕西遭受三年大旱,赤地千里,饿孚盈路。次年冬,杨虎城将军兼任陕西省主席。为抗灾救民,他电请李仪祉回陕任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并在财政困难情况下,专为兴修水利拨款四十万元……
引泾水利工程开工了!
李仪祉脸上浮起了笑容,他又高唱秦腔,和同伴们奔走在渭北的原野上。……这一年腊月二十三,按照风俗,是祭灶王爷的日子,乡民们都辍止劳作,准备过年了。但是,李仪祉他们却冒着凛冽的寒风,披着漫天飞雪在野地里测渠定线。有的农民感动地说:“今日灶王爷都上天回富哩,你们还不歇息,真是难得啊!”
李仪祉采取“以工代赈”的方法,既解决了灾民的口粮问题,又动员了足够的劳力。群众早盼渠成,日夜奋战。一九三二年六月,第一期工程竣工,命名为“泾惠渠”。二十日举行放水典礼时,当地百姓扶老携幼,观者如堵。李仪祉父亲发起和创办的西安易俗社,特地赶来公演新编秦腔《泾惠渠》助兴。当滔滔的流水,顺渠奔泻而下的时候,人们追逐水头,欢呼雀跃;有的人手捧渠水,激动得流下了热泪;有的连声感叹:过去闹旱灾,给龙王再磕头烧香,也不顶事,李仪祉才是咱们的活龙王!”
二年后,泾惠渠工程全部完成,共可浇渭北耕地六十多万亩,礼泉、泾阳、三原、高陵、临潼五个县粮棉产量成倍增长了。
径惠渠的成功,坚定了他兴修洛惠渠的信心。他亲自派傅健、陈靖两位技士到洛河进行实地测绘,并再次呈书杨虎城将军说:“泾惠渠由公手而成,亦复有意再成洛惠乎?”并委托陈靖持信面请。杨将军点头同意,当即在一九三四年初动工。后因战乱,材料缺乏,洛惠渠直到一九四七年才基本竣工。因它是在古代龙首渠的遗址上修建的,故将袱头的提水坝定名为“龙首坝”。还在凌空飞架的曲里渡槽上题写了十四个大字:
大旱何须望云至,自有长虹带雨来。
就在兴修洛惠渠的当日,李仪祉又派人测量了关中第一大河——渭河,并在眉县余家堡筑坝引水。一九三七年渠成,名日“渭惠渠”。与另一工程梅惠渠同时放水,共可浇地八十余万亩。
在修建关中三大水利工程期间,李仪祉日夜奔忙,常常废寝忘食。有一次他急冲冲赶回家时对夫人说:“快!随便弄点吃的,要赶着上工地哩!”夫人赶忙把饭菜做好摆到桌上,可过了半晌,却不见动静。原来李仪祉正目不转睛地看着图纸,早把吃饭给忘了。夫人便埋怨说:“看把你忙成啥了,爱成啥了,连饭都顾不上吃!”
李仪祉却风趣地说:“就是爱吆,咱们没有女儿,径、洛、渭三惠渠就是咱三个女儿,我一天不看看,就想她们呀!”
(四)
一九三五年九月,黄河水利委员会成立,李仪祉担任该会委员长兼总工程师,领导堵口工程并筹划黄河的治理等工作。他还兼任陕西省水利局长,负责关中各大渠的施工,繁重的工作压在他的身上。白天,他经常冒着酷热和风沙,巡视修堤工地,亲临现场指导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晚上,还要挑灯夜读,撰写文稿。请看下面两则日记:
“(四月)二十六日,晴。草《免除豫冀鲁黄河以北水患议》成。王秀文包工二十公里二十二万余方,而能力不足,管理不得法。令赵段长责令王分包于他人,并令范秀山助王秀文整顿。赵、范今日赴工。《郓城县志》寄来。有勤务受工头贿十元,追还其贿,逐之。”
“(五月)十一日,早七时出发,九时至河。渡河到贯台,一时完毕验收手续。二时渡河至东坝头,乘汽车归。遇大风,沙尘蔽日,至夜不息。至开封己七时。”
这是多么可贵的工作态度和献身精神呵!
李先生还博采古今中外治河的经验,结合数千里的实地考察,写出四十多篇论文,提出许多独到的治黄见解。象他的上、中、下游并重,防洪、航运、灌溉、水电兼顾的主张,至今还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尽管李仪祉耿介廉直,是一位才华卓越,志向恢弘的科学家,可身处那个社会,仍然难免受到排斥和打击。当时,官僚政客都把河务“衙门”视作“肥缺”,为中饱私囊,千方百计往进钻。一九三五年初,南京政府把大财阀孔祥熙的亲信孔祥榕塞进黄河水利委员会。这个家伙,一手抓权,一手抓钱,对李仪祉事事扯肘,满脑子迷信,凡事要靠“扶乩”决定,名为副委员长,实是治河的“绊脚石”。
“薰莸不可共器”。试想,一个科学治水的正派人物,怎能与这种龌龊邪佞之徒共事?因此,李仪祉多次固请离开“黄委会”,终于当年十月拂袖而去。当有人问他为什么要离开时,他幽默地回答:“以孔理财,以孔治水,财水都由孔流出去了!”还有人说:“你放着黄委会八百元工资不要,却看上个一百元的省水利局长,图个啥呀?”李仪祉坦然一笑:“人要做大事,不要想做大官:凡事讲求个实际,不要务虚名嘛!”
一九三八年三月八日,李仪祉终因积劳成疾,与世长辞。这位中国水工学界的领袖,一代杰出的科学家,只活了五十七岁!
三月十五日,灌区五千多群众不约而至,大渠两岸泪雨纷纷,哭声动地。人们把李仪祉先生的遗体安放在泾惠渠两仪闸旁的高原上——这里是李先生兴修水利的起点,也是三秦人民世世代代寄托自己黄土地一般深厚怀念的地方。
李仪祉先生不朽!
一切为人类造福的人不朽!
注:今年三月八日,是李仪祉先生逝世四十八周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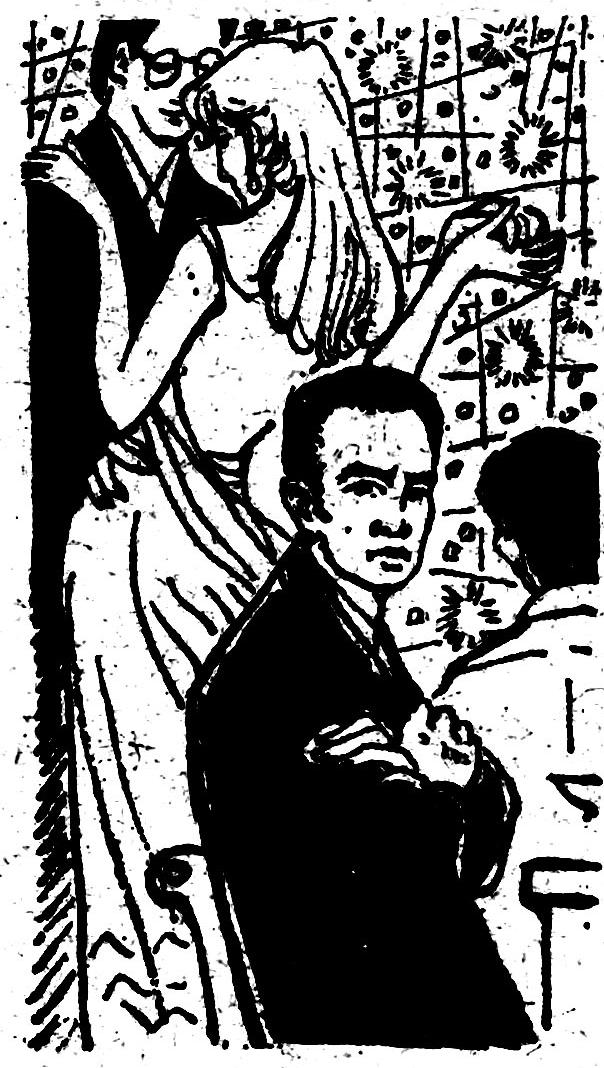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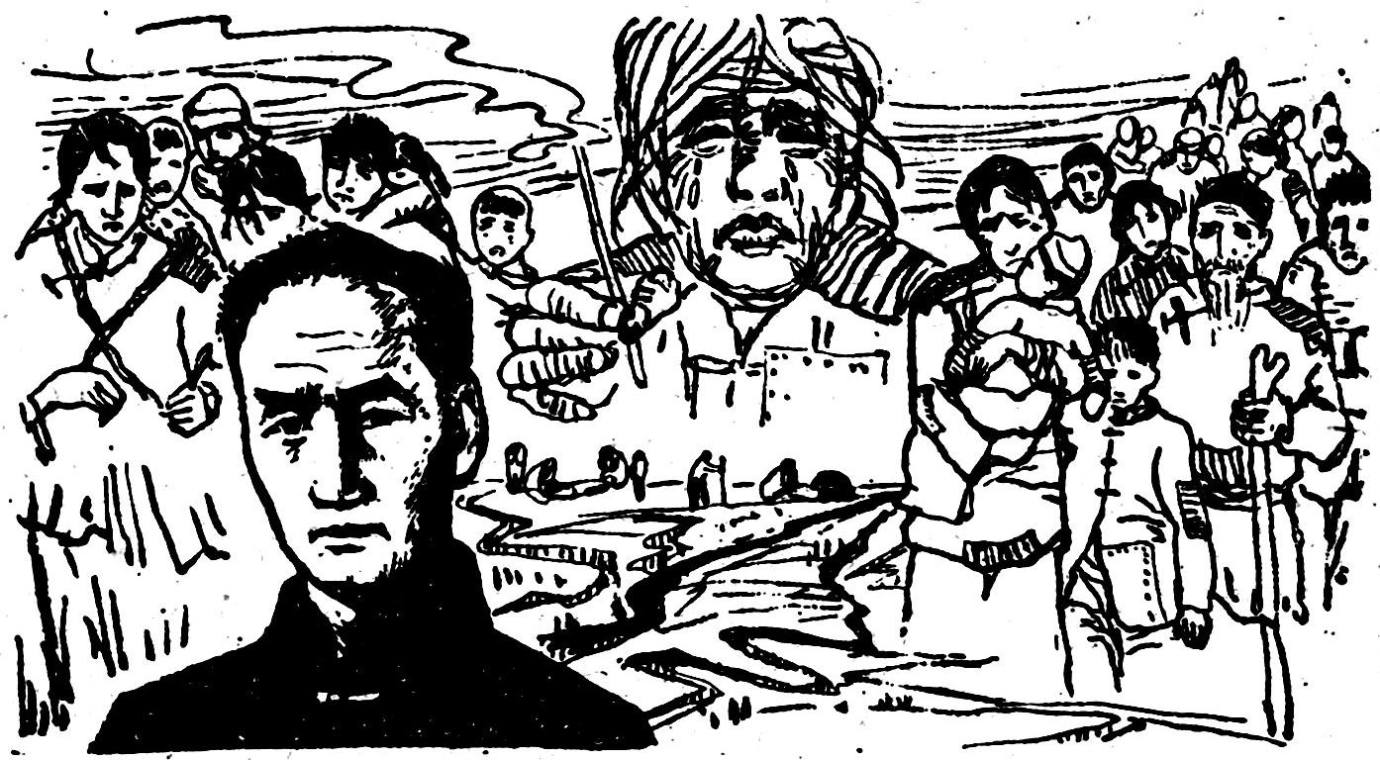
插图:罗宁 周束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