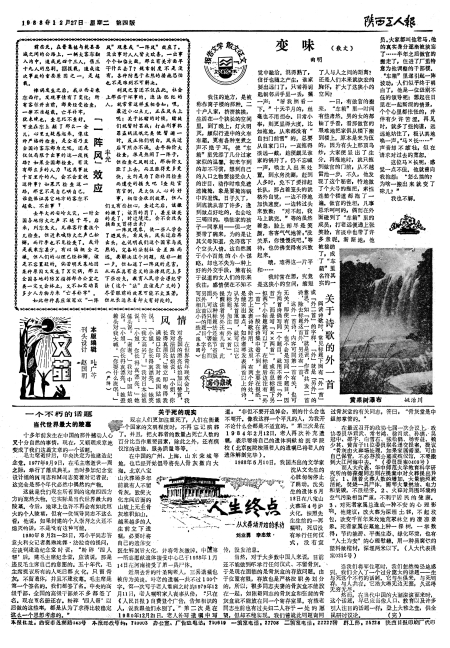人生终点
——从火葬场开始的采访
刘业勇 李忠效
一个不朽的话题
当代世界最大的陵墓
十多年前发生在中国的那件撼动人心又十分自然的事情,现在,又顺理成章地变成了我们这篇文章的一个话题。
毛主席逝世后,中央决定为他建造纪念堂。1977年9月9日,在毛主席逝世一周之际,举行了落成典礼,当时参加纪念堂设计组的W同志和M同志笑着对记者说:这完全是那个年代必然中偶然的产物。
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座四四方方的庞然大物。它实际是当代世界最大的陵墓。今后,地球上也许不再会有如此巨大的个人陵幕,但有一位领导同志不这么看,他说,如果封建的个人崇拜之火还不熄灭的话,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1980年8月21—23日,邓小平同志答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提问,在谈到建造纪念堂时说:“粉碎‘四人帮’后,建毛主席纪念堂,应该说,那是违反毛主席自己的意愿的。五十年代,毛主席提议所有的人死后都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毛主席是第一个签名的。我们都签了名。中央的高级干部、全国的高级干部差不多都签了名。现在签名册还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做的这些事,都是从为了求得比较稳定这么一个思想考虑的。”
关于死的现实
现在人们更加注重死了,人们在衡量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时,不再忘记殡葬了。并且,把火葬者的数量占死亡人数的百分比当作重要因素,除此之外,还有殡仪馆的设施、服务质量等等。
在中国的广州、上海、山东荣城等地,也已经开始倡导将先人骨灰撤向大海。北京八宝山火葬场多年前就有人不留骨灰,致使火化车间后面的山坡上无主骨灰堆积如山。越来越多的人生前立下遗嘱,必要时将自己的遗体交医生解剖后火化,并将骨灰撒掉。中国第一所志愿献遗体接受中心已于1988年1月14日在河南接受了第一具尸体。
近期去世的叶圣陶老人,三易遗嘱也被传为美谈。叶老的遗嘱一共不过130个字。第一次写于老人重病之时的1979年12月11日,老人嘱咐家人丧事从俭,“只在《人民日报》自费登个广告,告知相识的人,说我跟他们永别了。”第二次是在1980年12月21日,老人补写遗嘱中写道:“非但不要开追悼会,别的什么会也不要开。像我这样一个平凡的人,为我开不论什么会都是不适宜的。”第三次是在1984年2月12日,老人再次补充遗嘱,表示要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医学院校(北京医院按照老人的遗嘱已将老人的遗体解剖完毕)。
1988年5月10日,我国杰出的文学家沈从文先生的心脏匆匆停止了跳动。沈先生的遗体5月18日在八宝山火葬场4号炉火化,按照先生生前的一再嘱咐,死后没有举行任何仪式,没有宣传,没发消息。
当然,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目前还不能做到不举行任何仪式、不留骨灰。于是现在面临的是骨灰盒的存放问题。由于位置有限,存放也是严格按职务划分的,所以,很多同志夫妻的骨灰盒不能放在一起,如陈毅同志的骨灰盒和张茜的骨灰盒就不能放在同一个寄存室里。有些老同志生前也有过夫妇二人存于一处的愿望,但却不能实现。我们曾就此问题询问过骨灰堂的有关同志,答曰:“骨灰堂是中组部掌管的。”
在最近召开的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上,政协委员华君武、常书鸿、徐肖斌、孙瑛、吴冠中、邵宇、白雪石、张松鹤、杨宪益、赖少其、黄苗子11位委员联名递交提案,提议“骨灰由火葬场处理,如果家属需要,可由自己保管,不必存放公墓或殡仪馆,不要撒到大江河海中去。”(委员提案0409号)
而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的杨葆焜同志则在提案中对火葬提出异议:1、随着火葬人数的增加,大量能源被消耗,焚烧一具尸体,需要大量燃油、电力和柴碳,不很经济。2、火葬对周围环境的空气污染相当严重,不利于居民的健康。3、对死者家属总造成一种不安的心理影响。他建议:改火葬为深埋土葬,不起坟包,改变千百年来坟地荒冢林立的凄凉景象。死者家属在墓地上种一棵树,一举数得:节约能源、平衡生态、绿化环境,也有“入土为安”的心理慰藉。用一种易腐烂的塑料做棺材,深埋两米以下。(人大代表提案0315号)
当我们将要住笔时,我们忽然惶恐地感到,我们介入了一个过分庞大的话题——生与死这个不朽的话题。它与生俱来,与死同存,与人共在。它浩大得无边无涯,久远得无穷无尽。
然而,在当代中国的大潮滚滚而来时,这个话题,早已应当像人口、教育以及许多引入注目的话题一样,登上大雅之堂,供全民研讨议论。(完)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