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山峡谷尽头
——记秦岭山中的林业工人
叶广芩韩庚
秦岭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山地之一。
这里森林茂密,溪水淙淙,厚厚的苔藓下埋藏着一座座碑石残垣,无尽的藤蔓中缠绕着一个个远年故事……
除却这神奇与悠远,更重要的是这里的人——顶天立地的林业工人。
在绵延500公里的秦岭南坡,珍珠般散落着宁东、宁西、龙草坪、长青、太白、汉西六个林业局。一万多名林业工人,在秦岭腹地,在高山峡谷的尽头辛勤劳作着。雁来雁去,花开花落,他们用咸咸的汗,用滚热的血默默滋润着这片38万公顷的山林,为这片美丽的山地增添了更加绮丽的光彩,谱写了更加悲壮的乐章。
勘察设计队
去年,共青团西安市委在表彰新长征突击队的大会上,九面红旗都被领走了,唯有宁西林业局森林勘察设计队的红旗孤零零放在主席台上。人们注视着那面耀眼的旗,窃窃私语,人呢?
人,在高山峡谷的尽头,太深远了,难以到达省城。这个队在秦岭里转了21年了,专管森林资源调查与线路勘测。谁的脚下都有路,他们没有。他们脚下是丛林草莽,是麂的蹄印,是熊的踪迹,几十名队员钻林子越沟坎跑的路加起来已超过315万公里,可以进行第126次长征了。有人说他们整日钻山林,血都变绿了,掺进了羚羊、山猫的气息,所以队员们个个灵巧机敏,自豪欢快,自然也带着秦岭山中的野性。他们说,站在秦岭梁上撒泡尿,会有一半流入黄河,一半流入长江,这本事也就他们有罢!他们用经纬仪找水平,用三角函数测高度,用角规算出林木直径……都是正儿八经的技术活,内中不乏大学生。这精明强干的一群在年轻队长洪的带领下干得很出色,连年被森工系统评为先进。队长叫洪宗生,但大伙都叫他“洪”,许是昵称吧。
森林勘察设计要先在地图上把高山深谷分成千百个点,谓之“小班”,然后这帮人分成几个组,到每一个点实地勘察,一棵树一棵树查树种、定树龄,做标记,计算蓄积量、郁蔽度、土壤性质、厚度……为采伐、为人工更新做好准备。没人上过的崖他们得攀,没人涉过的涧他们得穿。一双脚把秦岭的山踏遍了,一双眼把秦岭的树数遍了。难怪有人称他们是森林的总体设计师。
在岚皋搞调查的时候,当地老乡把这伙文弱书生模样的人不放在眼里:啥?上老爬岭?2900多米呐,地质队,调查队上去过不少,没一个在上头站得住脚的,你们哪儿凉快哪儿歇着去吧!这伙人一咬牙硬是上去了,在上头一住52天。老乡说,这伙后生简直不是人!
山高林深,什么玩意都有,专往人衣裳里钻的裤裆蜂;粘在枝梢伺机投靠人身的旱蚂蟥;爱钻人腋下、肚脐的草蓖虱;更有蠕动于草间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蛇……哪个都不是善茬。奔波一天,晚上回帐篷还要脱光衣服互相用针挑出钻入皮肤的蓖虱。有一次,队员吴方健在山梁子上让无名小虫咬了,20分钟后浑身肿得失了形,痒得他在地上乱滚,哀求同伴用皮带抽。可谁也下不去手,只能噙着泪看他滚,直到他精疲力尽,再也喊不出声为止。
协助东北搞森林调查时,任百恒小组在大兴安岭老林里迷了路,虽然带着罗盘,但他们自我意识调整不过来,总觉得附近有磁场什么的影响罗盘准确,便凭着感觉走,到半夜都没走出林子。队上人人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四处寻找。他们小组三位弟兄幸好碰见辆拉料车,和木头们一起在大雨中被运进了一个叫碧水的陌生小镇,落难公子似地红口白牙跟饭铺女老板要了碗粥喝,随后就以“老陕”的姿态在小镇影院前的台阶上趷蹴下来等待天色放亮……
于是,在秦岭的清风明月中,在帐篷里的大通铺上,队员们的口头章回小说便在第六章北京亮相,哥们儿大闹行包房后增加了新的一回:“东北栽份,任百恒夜观碧水镇”。
采育队
见过伐树的么?
“顺——山——倒——”,一声猛吼,撼山震岳,回音万千,惊起飞鸟无数。一阵呻吟,一阵轰响,那树带着疾遽的风沉闷地倒下,大地随之一阵战栗。
伐木的汉子巍然而立。
我国人均森林面积仅占世界121位。
我国木材需求量正以每年5%—15%的速度递增。
我国到2010年将出现中龄林断档。
伐木工不愿砍又不得不砍。人们不愿听那揪人心迫的伐木号子又不得不听。尽管这种带有原始的、野性的吼在山的深处已经稀疏。
伐木工人们喜忧参半。
早晨吃罢两个杠子馍上山,干一天,饿一天,水都喝不上,回来狠咥一顿,便钻进被窝里看月亮。山上晴雨无常,淋成落汤鸡是常事,那份单调、枯燥、寂寞就更不用说了。但四面八方要木材,还得干,得好好干。
伐木工王春孝,生长在富饶的兴平县,听说林业局招工,全民所有制,被验上后美得几晚上没睡好。上班了,一人发根木棍,干啥?说是撬杠,集材时撬原木用的。真干起来,才知这可不是玩的,木头撬到坎当央,没劲了,没劲也得硬顶住,只要一松懈,一两搂粗的原木下来,人就“擀了面”,非死即伤。在山里干过20年以上的伐木工,身上都有数不清的伤,死里逃生好几次。
在龙草坪小沟河林场,我们见到伐了一辈子木的何祥云。老何没文化,能喝酒,长一身棱角分明的腱子肉,干起活儿十分利落。现在,当了多年先进的老何坐着,一脸愁苦。他委屈。别的行业超产有奖,他们砍树的超产了要挨罚——龙草坪木材年产量已从5万立方减到1.4万立方,集中力量搞经济林和综合利用了——完不成任务反而有奖,真窝囊。
为了宝贵的绿色资源,打几年前起,林场就多了一群叽叽喳喳的女子——专管栽树、抚育中幼林。采育队名符其实,既采又育。现在,老何看着那谷底冉冉升起的岚雾,托着腮,不言语。育林的女子们也在看雾,指手划脚谈论那架在雾中的线,过几日,电视卫星地面接收站一安好,她们晚上便可以与山外迈动同一个步伐了。
云雾涌来,将老何与女子们统统遮了。
工程队
活人坪梁。
听这名就够了。海拔3000多米,云缠雾绕,山风摧撼,更有什么孙二娘卖人肉包子之类黑店的传说,能活着翻过去实属不易。长青林业局华阳林场工程二队就驻扎在活人坪梁下的大坪。除了他们这里再无人烟,站在工棚门口朝远望,群山都在脚底下拱。
他们的任务是开路,好把木材往山外运。在猴都不住的地方筑路,苦极。伐树挖根,修便道,挖土方,炸山石,推路基,整路面,上头要跑汽车,跑集材拖拉机……七月天,山外热浪翻滚,二队的每个工棚里却都在地当间放着炭火盆。队长魏双安说,都说这是神仙住的地方,哪知我们的难处哩。山高气压低,水80度就开锅,米饭夹生,面条粘牙,洋芋是主菜;木板墙、毛毡顶的工棚里都留着泄水沟,90%的老工人腰腿疼。有一宿,左德友、曾定文三班那几个睡醒了一睁眼,嗬,房顶让风掀了,人在雪里睡着,啥鬼地方!五、六级风在这算是微风习习,冬天雪有一米厚,施工要走七公里。五十米高的绝壁,腰里拴根绳上去,悬在半空抡锤打眼。眼下正施工的右手沟,地质结构复杂,炮眼里直冒水,一天干下来,人人都成了泥猴。
谁能说这活不苦呢?
苦中也有取乐的法子,吃罢晚饭,秦腔自乐班就开戏了,“月光广场”上,围着老老少少一大帮子人,高亢的板胡拉过前奏曲,开山劈路的汉子迎着风大吼一声“窑门外拴战马——”,群山呼应,比那西征的薛平贵更悲凉、更苍劲。
红日自山顶坠落。一条依稀可辨的小路沿坡蜿蜒而上。1935年,程子华、徐海东率领红25军曾沿这条路翻过活人坪梁走向北方。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望着这条隐没在草丛中的路,我们仿佛看到了当年匆匆走过的红军,那些人尽管是一脸疲惫,一身硝烟,但五个角的红星仍在闪烁,至今那么清晰,那么真切。他们的足迹凝聚着向往,凝聚着几代人的追求……筑路工人们沿着红军的印迹在向上攀,行进中,时时可以嗅到并未走远的先辈们的气息。
难怪,他们能锲而不舍地在高山顶上开出一条大路……
青春与热血的奉献
山中有首歌:“有女不嫁伐木场,伐木场里住草房,郎君有朝回家转,捎回一堆破衣裳。”
山里工人顶难找对象。
宁西局森调队的精小伙回到局里个个英气逼人,姑娘们拿眼不住地瞄。真谈婚事,她们就往后缩了,谁也不愿半年守空房,谁也不愿缝洗那堆破衣裳。森调队的小伙们为此不忿,与那些长年坐办公室的小白脸相比,他们什么也不差!于是个个变得高傲冷峻,羚牛似的,越发往山高头没人的地方钻。队长洪宗生问我们,能不能登个集体征婚广告,当然这是下策,首要的还是记者转告诸位读者姑娘,让她们想着秦岭山中有一群把青春献给森工事业的后生们。
他们不仅仅献出青春。
我们到达白杨坪采育五队时这里正被一层厚重的悲哀笼罩着。前天,他们的同伴马孬娃施工时被塌下的山石击中头部,离大伙而去了。马孬娃17岁干林业,35岁便为林业献身。在这位普通伐木工的宿舍里,他擀的面晾在案上,洗净的衣裳还没来得及迭,锋利的弯把锯立在床头……他似乎还活跃在同伴们中间,可却永远地走了,与悠悠的绿草,与亘古长存的山融为一体。他同房的工友赵文卓把一口烟丝毫不剩地吞进肺里,慢慢地说,把木头运出山不容易,这是个玩命的活儿,要流血
我们又想起宁西局那89公里进山路,修路时整整牺牲了89名筑路工,崎岖的山路每一公里都是用鲜血铺就的。山间那一座座不起眼的墓碑,记载了一个个悲壮的故事,埋葬了一个个不息的魂灵,也激励着一个个后人。
山野静寂,残月清冷,深谷制凉,唯有清明节留下的纸花在松枝间摇曳……
秦岭默默。
(题图赵世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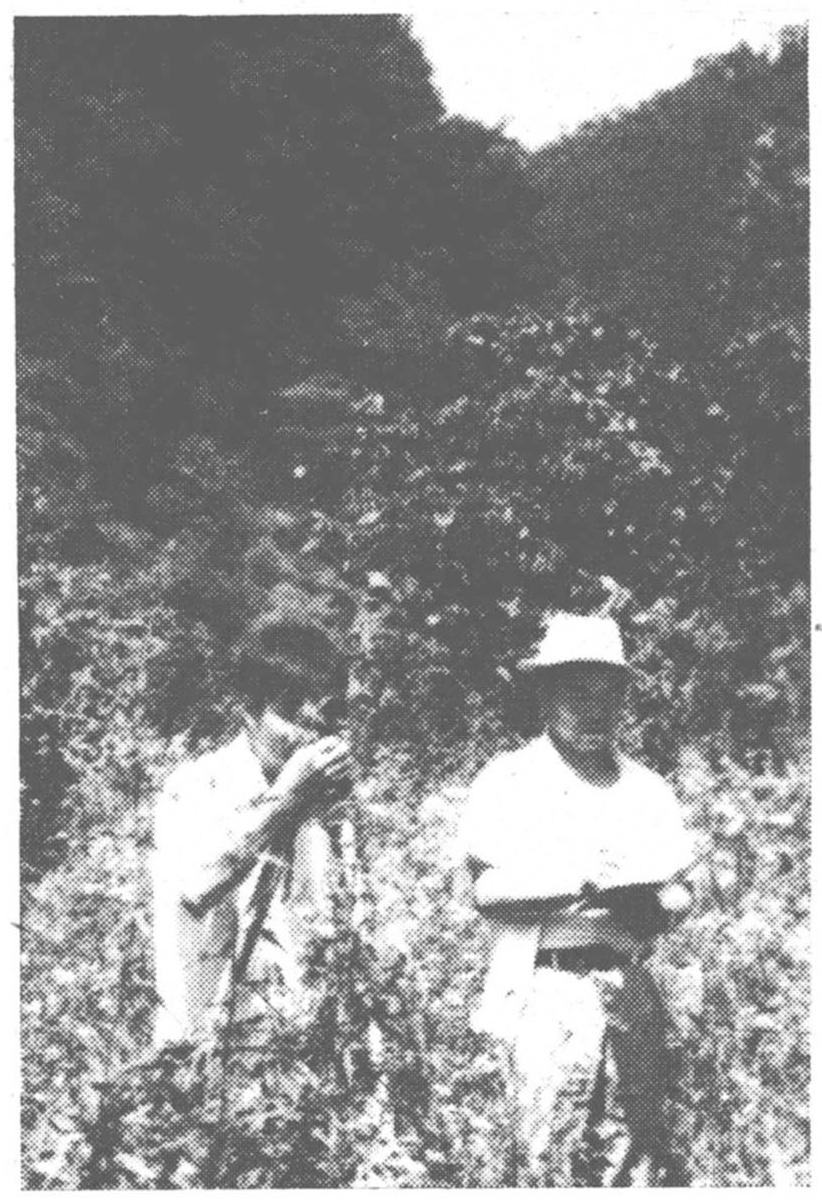
宁西局森林勘察设计队的小伙子们在谷地搞测量。 关华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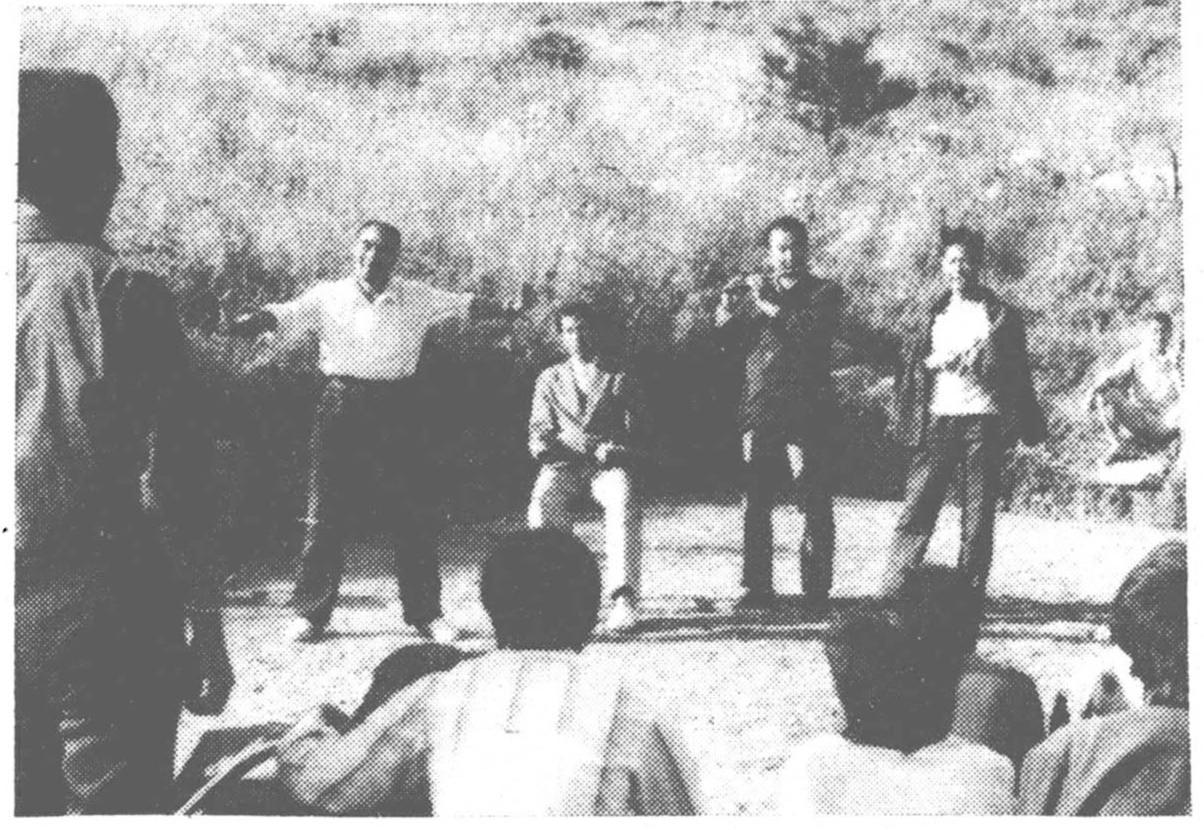
下了班,长青局建筑队的自乐班在高海拔的大坪吼开了秦腔。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