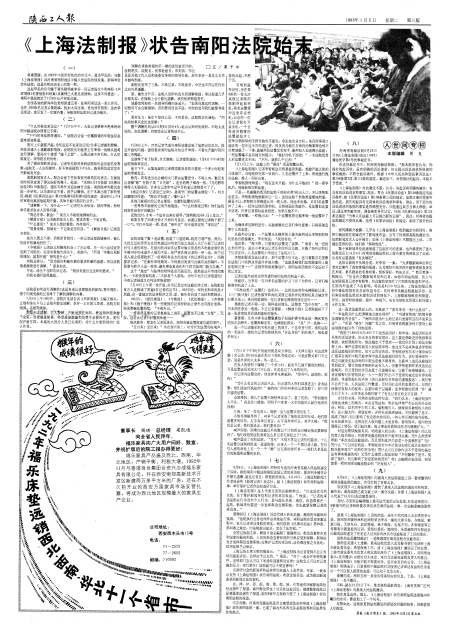《上海法制报》状告南阳法院始末
文/寒于水
(一)
毋庸置疑,在1992年中国形形色色的官司中,最为罕见的,当数
《上海法制报》诉河南省南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的侵权案。新闻单位
状告法院,这是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一例。
这起罕见的官司缘于著名歌唱家李谷一诉记者汤生午和南阳《声屏周报》名誉侵害纠纷案(其案情已大量见诸报端,这里不再赘述)。南阳中级法院定于7月8日公开审理此案。
全国各地的新闻单位竞相派遣记者,赴南阳采访这一名人官司。也许,300余名记者云集宛城,犹如大兵压境。谁也没有想到,这次采访活动,竟引发了一宗案外案,导致南阳法院自己成为被告。
(二)
“什么时候发采访证?”7月7日中午,大批记者络绎不绝来到南阳中级法院办理登记手续。
“下午5时来法院等通知。”法院办公室一位戴眼镜的年轻法官态度冷漠地答道。
明天上午就要开庭,为何迟迟不发采访证呢?许多记者感到费解。消息灵通人士透露最新情报:法院院长刘建秀正在率领一批精兵强将进行调解,要汤生午接受“城下之盟”,以图此案不审而结。什么时候发证,须等院长的吩咐。
为了确保领到采访证,记者争先恐后来到法院临时会议室枯坐等候,法院无一人出面接待。好不容易捱到下午5点,跑来两位法官宣布开新闻发布会。
该院新闻发言人、院办公室主任张春安用最简洁的语言,在极短的时间里宣读了事先拟好的稿子。他说:“本院6月3日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通知韦唯作为追加被告出庭,现经院审判委员会进一步研究,认为原决定不妥,现予以撤销。由于本案出现了新的情况,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32条第3项和第4项的规定,原定8日上午8时审理此案因故延期开庭,具体开庭日期另行公告。”
“请解释一下,为什么……”记者们大为惊讶,顿时哗然,纷纷举手要求发言人回答问题。
“我还有事,散会!”发言人不耐烦地拂袖而去。
《解放日报》记者跑到发言人前,要求再看一下发言稿。
“什么意思?”发言人耷拉着脸,冷冷地问。
“准备发稿,想核对一下记录是否有误。”《解放日报》记者直言相告。
发言人置之不理,仍然昂首前往,一些记者还想跟随核对,被几位法官粗暴地挡住了。
《今晚报》记者赵志明瞅准机会上了办公楼,在一间小会议室里见到了刘院长,其旁坐着被告汤生午。老赵问:“所谓‘本案出现新的情况,延期开庭’指的是什么?”
刘院长答曰:“因为原告和被告都有要求和解的意愿,所以法院准备继续进行调解。”原来如此。
可是,汤生午当即告诉记者:“我没有提出过这样的要求。”
刘院长顿时显得尴尬。
(三)
法院是如何进行调解的?这是各地记者都想抢的新闻。费尽周折,善于问根究源的记者终于了解到调解的内幕。
7月5日上午10时许,法院打电话告诉《声屏周报》主编王根礼,让他和汤生午马上去郑州参加调解,李谷一正在那儿等着。法院方面强调:不能带律师。
到郑州去调解,让人费解。开庭地点在南阳,往返郑州需奔波
千余里,冒着盛夏酷暑,经受旅途颠簸和花费不必要的开支,更何况开庭在即,本案的大部分人员已在南阳,为什么非要到郑州?没人作答。
调解在省政府招待所一楼的会议室里开始。法院院长、副院长、民事庭庭长、审判员、书记员及其他工作人员和地委宣传部的领导在座。原告李谷一及其丈夫肖卓能均到场。
副院长宣布了三条:不准记录,不准录音,今后也不许以任何形式向外界透露。
原、被告分开后,法院人员即向汤点明调解前提:承认报道几乎全部失实;在报纸上公开赔礼道歉,承担经济赔偿责任。
地委宣传部的一名领导明确向汤表示:“如果同意这样调解,一切费用可由公家报销,否则费用自负不说,对你的使用我们就要考虑了!”
面对压力,汤生午坚持己见,不肯妥协。法院院长告诫他:“判决的结果只会比这更惨!”
整个调解时间从5日到8日历时4天,地点从郑州到南阳,车轮大战似的。如此调解,自然使众记者纳闷不已。
(四)
7月8日上午,27名记者代表向南阳地委反映了法院出尔反尔、推迟开庭的问题,强烈要求南阳法院尽快公开审理,不要在开庭时间问题上再拖延。
交涉终于有了结果。当天傍晚,记者接到通知:7月9日下午4时到法院领取采访证。
是日下午,云集宛城的记者都顶着炎炎烈日提前一个多小时赶到法院等候发证。
然而,所有进出办公楼的大门都由法警把守,不准入内,数百名记者被“晾”在院子里“日光浴”,连坐的椅子都没一张。7月的骄阳烤得人头昏眼花,许多女记者和年过半百的老记者都受不了了。
《南京日报》记者见已过5时,恳请守门的法警去催促一下,对方却瞪眼训斥道:“院长早知道了,嚷什么?”
其他几家报社的记者去催促,也遭到法警的训斥。
一些等得不耐烦的记者开始抱怨:“什么时候发证啊?你们法院到底有没有时间概念?”
直到此时,才有一个法官出来打招呼:“请稍候2分钟,马上发证。”
结果又等了20多分钟才开始叫号发证。如愿以偿的记者终于舒了一口气,可打开信封一看,竟是“旁听证”而不是原定的“采访证”。
(五)
法院调集了数十名法警,组成了三道防线,防范可谓严密。然而,大批无证的男男女女仍然通过岗哨堂而皇之地进入大厅占据了记者们对号入座的席位,在庭内的20余名法警对触目皆是的不准参加旁听的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视而不见,却严密注视记者的一举一动。每个记者入座之前都收到了一份南阳有关方面发的《告记者同志书》,明确要求记者:“在案件审理期间,不得擅自发表与此案有关的稿件,不要参与和介入这一纷争,避免事态复杂化和干扰司法部门独立办案。”
这个“规定”与法律的相悖是显而易见的。既然是公开审理的案件,一不涉及国家机密,二不涉及个人隐私,为何不允许记者报道呢?不准记者报道又有何法律依据呢?
7月10日上午第一次开庭。在书记员宣布法庭纪律之前,法院新闻发言人连续读了两遍《告记者同志书》。8时33分,审判长和审判员才到庭。在一套规定的法律程序之后,原、被告各自读了诉状和答辩状。
10时许,《新民晚报》、《今晚报》、《武汉晚报》、《齐鲁晚报》和《扬子晚报》等一些晚报的记者纷纷起立欲外出向报社发稿,结果都被法警挡驾:“不准外出。”
一位重庆某报的记者离座去上厕所飞,法警也不让她“方便”,无奈,这位女记者只好憋到休庭……
每次庭审,都发生记者因录音、照相而被法警驱逐出庭的事件。
“交出来!交出来!”坐在旁听席上,时常听到法警的吆喝声,彼伏此起,不绝于耳。
韦唯到庭作证时,坐在第6排的一位长沙某报记者欧阳劲刚举起照相机,两名法警便冲过来夺走相机;北京的一位女记者刚打开录音机,一个长得虎背熊腰的法警就抢步上前伸出钢钳似的手抓住她的手提包,夺走她的录音机;来自河南周口地区的一位年过半百的老记者,仅仅因为被告方律师的精彩辩论情不自禁地鼓了一下掌,就被两位法警反剪双手,像押犯人似地撵出法庭;一些法警毫不忌讳地互相提示:“拣好的机子没收!”一名法院负责人对法警直言不讳:“不行,就抓几个记者!”
7月11日上午,法庭上的“插曲”更是频繁出现。
《上海法制报》记者李智刚这天特意提前到庭,想趁开庭之前拍几张照片。当他刚拍完第一张照片,几名法警扑了上来,将他强行拖出法庭,推入一间办公室。
李智刚据理辩道:“现在还未开庭,为什么不能拍?”经一番争执后,他被获准回到法庭。
可是,一名摄像的秃顶的法院干部站在第7排出入口,不让李智刚走进去。李智刚请他挪挪步让一让,这位法院干部依然蛮横地挡道,硬是不让。李智刚只得绕道从另一端入座。他还未坐稳,又有3名法警冲了上来,一把夺过他的照相机,又将他强拉到庭外。见法警如此蛮不讲理,许多记者都站起来指责,为李打抱不平。
“谁再嚷,一样拖出去!”一个法警提着电棍率领一批法警冲了上来。
为确保采访顺利进行,头脑清醒的记者们审时度势,只得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
在庭外办公室,一个法警头头模样的人极为麻利地从李智刚的相机里抽出胶卷曝光。李对他说:“我没有拍。”
他回答:“我不管,只要我们法警说了就算。”接着,他一把抢走李的背包,逼迫小李拿出记者证和旁听证交换。在撕了旁听证和扣了记者证后,几名法警将小李推出了法院大门。
李智刚要求交还记者证。那个法警非但不还,还当着数百名围聚在法院门口的群众得意洋洋地大嚷:“这就是被我们法院驱逐的上海法制报记者……”直到李智刚离豫返沪,南阳法院仍然拒不交还扣下的记者证。
记者在庭外拍照也常常遭到南阳法院的粗暴干涉。
休庭后,当李谷一在10多名法警的护卫下步下台阶时,记者们端着照相机迎了上去。
“不准拍照!”法警们一边吼叫,一边挥动皮带和电棒驱赶记者。《三门峡日报》记者孙振军和湖北某报记者洪洋的照相机差点被皮带打落在地上;来自洞庭湖的一位记者被电棒捅得哇哇直叫……
勇敢的记者不顾一切,照样抢拍镜头。法警竟“急中生智”,用书本挡住李谷一的脸,不让记者摄影。《解放日报》记者陈斌拍下了这一张珍贵的具有讽刺意味的镜头。
紧接着,又有10多名法警像裹饺子似地护着韦唯走进一辆米黄色的伏尔加轿车。法警挥舞皮带、电棒驱赶群众,“杀”开一条路……
没一个记者能拍到韦唯在庭上的照片。于是奇货可居,南阳法院的一名法官,趁机向记者兜售他利用“合法身份”拍的照片,每张索价30元!
(六)
7月11日下午3时开的庭仍然是双方辩论。《天津日报》刘志武等数十名记者,2时45分就在烈日下排队等候进场,可是法警关着门不让进,说是外面的人太多,等一会儿。
在灸人的骄阳下曝晒了一个多小时,庭里早已展开激烈的辩论,可是法警还是关闭大门不让进,又说是过了入场的时间。
有记者向法警交涉,他竟挥着电棒威胁:“你再叫,就捅你,抓你!”
“为什么有证的记者进不去,而无票的人你们却放进去?身为法警,你们是如何执法的?”被挡在门外的40多位记者发怒了,异口同声谴责法警。
众怒难犯,那几个法警不敢轻举妄动了,耍了花招:“管钥匙的人不在。”真是信口雌黄,明明手中拿着一大串钥匙的人就在他身后抽烟!
片刻,来了一位负责人,观察一会与法警耳语后走了。
不能再消极等待了。40多个记者采取了集体抗议的行动,他们排成整齐的队伍,左手高举记者证,右手高举旁听证,齐声大喊:“我们是记者,我们要进去,我们要采访!”
喊声似雷,围聚在法庭以外的数以千计的群众目睹此情此景都惊讶了,他们没想到法院竟将这么多记者无理拒之于门外。
喊声震动了南阳法院,“里头”不得不答应记者们的要求。十几名法警分成两排组成一道道防线,由来人一个一个领记者人庭,在对号入座的席位上又一个一个“揪”出无票的旁听者——他们大多是法官的家属和法警的亲朋。
(七)
8月8日,《上海法制报》用特快专递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了诉状,指控南阳中级法院侵犯该报记者的采访权,要求判令被告公开赔礼道歉、返还记者证,赔偿经济损失。8月18日,上海法制新闻工作者协会和《新闻记者》杂志社,就《上海法制报》状告南阳法院一事,举行保护记者合法权益研讨会。
《上海法制报》法人代表吉安国总编辑指出:“打这场官司的目的,在于维护新闻单位和记者的采访权益。”他说:“记者的采访是职业行为而非个人行为,是与报社名誉、地位、权益联系在一起的。新闻单位要进一步发挥舆论监督职能,首先就要保障记者的采访权。”
受聘担任《上海法制报》诉讼代理人的朱洪超、鲍培伦高级律师强调:“法院执行公务也同样必须依法行事。南阳法院在受理李案过程中,发生记者采访受阻的事实,我们依照《民事诉讼法》第29条、第20条之规定,向法院提出起诉,完全于法有据。”
全国记协副主席、解放日报总编辑丁锡满指出:舆论监督符合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人民的舆论监督权理所当然应受到保障,新闻应充分发挥舆论监督职能,应维护记者的采访权,这些都应使之合法化,即用法律予以保证。
上海记协主席王维明确表示:“上海法制报为记者受到不公正对待而提起诉讼,此举应予以支持。”他说:“对于一起公开审理的案件,宣传部门怎么可以下发通知逃避舆论监督?法院怎么可以对记者施加压力,实行禁令?法院就可以不受监督吗?”
出席研讨会的新闻界和法律界的权威人士及学者、专家,一致表示支持《上海法制报》状告南阳法院,希望这场诉讼,成为推动新闻改革的新闻立法的契机。
京、津、沪、苏、浙、鲁、鄂、皖、陕、川等地有26家新闻单位对此事作了报道。海外舆论界也十分关注这起诉讼,港澳数家报纸以显著版面迅速作了报道,美国8家华文报纸刊登了《上海法制报》状告南阳法院的报道。
不言而喻,河南省高级法院是否立案受理及如何审理《上海法制报》状告南阳法院一案,已成了海内外各界尤其是舆论界和司法界关注的热点。
(八)
河南省高级法院8月26日才向《上海法制报》发出(1992)豫法民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
在这份裁定书中,河南省高级法院称:“经本院审查认为,你报社的起诉状,虽有明确的诉讼请求,但无提出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根据,不符合起诉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第3项、第112条的规定,裁定如下:对你报社的起诉,本院不予受理。”
《上海法制报》对此裁定不服,认为:其起诉有明确的被告,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的起诉条件。按《民事诉讼法》第108条第三项的规定,法院立案时需要审查的是:原告的起诉有无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至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是否确凿充分,只能通过双方当事人辩驳、举证,通过审判庭审理、调查核实再作认定。何况《民事诉讼法》第125条还规定“当事人在法庭上可以提出新的证据”。因此,河南省高级法院裁定不受理此案,违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剥夺了原告的诉权。
据传播媒介披露,几乎在《上海法制报》收到裁定书的同时,南阳中级法院在宛城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公布了河南省高院的裁定书。法院新闻发言人公开扬言:如果《上海法制报》不服提出上诉,二审裁定受理的话,他们将“奉陪到底”。
数十家新闻单位迅速报道了这起官司的进展。也许感受到了强大的舆论压力,9月4日,河南省高级法院向上海市委宣传部发出了公函,认为有必要通报“有关情况”。
这份公函的开头部分说,对李谷一一案,“大多数新闻单位和记者对此案作了真实客观的报道,认为南阳中院首次开庭审理涉及著名艺术家、著名歌星的名誉权案,组织得好,判决公正。”然后笔锋一转指出:“但也有少数新闻单位和记者,如你市的法制报、民主与法制画报及记者李智刚等,对此案的审理作了片面性的报道和评论,在国内外造成了不良影响。特别是8月中旬以来,上海法制报以南阳中级法院侵害其合法权益为由,向河南省高级法院提起诉讼,在河南省高级法院尚未接到诉状的情况下,上海数家报纸竞相报道、评论,搞得纷纷扬扬,海外一些报刊、电台也借机在所谓人权问题上大作文章。”
这一段话是颇具匠心的。在陈述了“原告李谷一为什么胜诉”,“一审法院为什么把调解地点放在郑州”,“当地宣传部门的领导参加调解是否合法”,“南阳中院为什么给记者只发旁听证而不发采访证”,“所谓‘禁令’问题”等之后,河南省高院就为何不受理上海法制报的起诉作了详细说明:
“我院于1992年8月19日下午收到起诉状,经审查,该起诉状虽有具体的诉讼请求,但无充分的事实理由,这主要是指缺乏所依据事实根据。故经我院研究,依法裁定不予受理……我们估计到上海法制报要上诉,案件还要经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故这里不必具体叙述李智刚违反法庭规则的事实。但可以肯定的说,李智刚没有向本社领导如实汇报其在南阳中院开庭审理中违反法庭规则的行为。该社领导仅听一面之词就决定起诉南阳中院也是极不慎重的。在庭审上违反法庭规则受到批评、警告的除李智刚外还有几人,但像李智刚那样多次违反法庭规则,而且受到批评后态度十分蛮横狂妄,以致于胶卷被曝光、记者证被暂时扣留的仅此一人……我们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是有事实根据的,考虑到报社的声誉(因只是轻信李智刚的虚假叙述),我们暂不公布于众。人民法院工作繁重,无时间打这样的笔墨官司。但我们保留后发制人的权利,必要时将予以揭露,使李智刚的所谓‘奇’遇大白于天下。正好李还为我们留下了有关记者证的文字证据。”
在信的末尾,河南省高院这样写道:“我们认为:上海法制报作为政法战线上的喉舌,本应宣传法制,维护法律尊严和公民的合法权益;相反,却利用手中的工具,偏袒被告人,继续损害被侵权人的权利,还小题大作,借题发挥,弄得社会沸沸扬扬。不但颠倒了是非,混淆了视听,而且影响了安定团结的局面。一些心怀叵测的海外报纸、电台如获至宝,也借此在人权问题上大发责难,影响很坏。现向你部通报以上情况,望引起注意,防止事态沿着错误的方向继续扩大。”
对这封看似振振有词、咄咄逼人的公函,《上海法制报》的几位负责人阅后指出:河南省高级法院没有开庭审理此案,凭什么指责李智刚“多次违反法庭规则,而且受到批评后态度十分蛮横狂妄”呢?凭什么“可以肯定的说,李智刚没有向本社领导如实汇报其在南阳中院开庭审理中”的所作所为呢?凭什么可以自称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是有事实根据的呢?又凭什么指责上海法制报“不但颠倒了是非,混淆了视听,而且影响了安定团结的局面”呢?总编辑吉安国说,他很想看一看河南省高级法院如何“后发制人”。
(九)
9月8日,《上海法制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要求撤销河南省高级法院的裁定。官司打到了首都北京。
国庆前夕,《上海法制报》接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通知书和传票,被告知:最高法院已成立就上诉一案合议庭,并要《上海法制报》法人代表于10月5日赴京接受询问。
其时,吉安国总编辑随上海司法代表团出访美国。在美逗留期间,8家报刊的记者纷纷要求采访状告南阳法院一事,吉总编委婉地谢绝了。
获悉《上海法制报》上诉的消息,汤生午的代理人北京律师李大进、洛阳律师窦柏林和赴南阳采访李谷一案的天津日报、今晚报、解放日报、天津电台、武汉晚报、扬子晚报、电视月刊、齐鲁晚报等记者都表示愿意提供证词。受报社委托,鲍培伦、朱洪超律师专程赴京向最高法院递交了有关证人证词并再次向合议庭陈述了上诉的理由。
是维持还是撤销裁定?一道难题摆在最高法院合议庭面前。
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最高法院负责人及其秘书曾打电话给上海市政法委员会,希望做做工作,请《上海法制报》撤诉以了结此事。上海市政法委有关负责人将此意见转告了《上海法制报》,并明智地表示:是否撤诉,由报社自主决定。来自北京最高法院负责人的意见,《上海法制报》当然不能不郑重对待。是非曲直自有公论。《上海法制报》明确表示:只要南阳中级法院对其侵害记者采访权益的行为表示一个可以使人接受的态度,可以化干戈为玉帛。
遗憾的是,南阳方面一直没有传来相应的信息。于是,《上海法制报》一直不撤诉。
不料,就在12月2日下午,笔者接到最新消息:上海有关部门已代《上海法制报》向最高人民法院撤诉。
倘若真是这样,那么,《上海法制报》状告南阳法院这场海内外瞩目的官司,算是划上了一个句号。
尽管如此,这场涉及到法制建设的深层次问题的纷争,仍然值得人们深思。
原载《南方周末》报:1992年12月4日第五版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