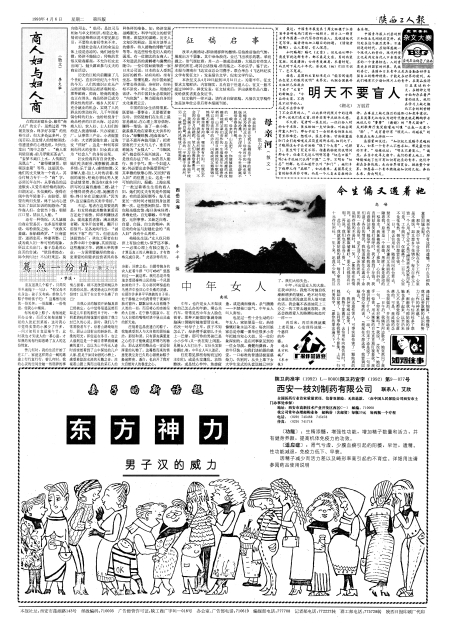
商人妇与妇人商
(散文) 李文举
在我国封建社会,嫁作“商人妇”的女子,虽然过着“终朝美饭食,终岁好衣裳”的优裕生活,但大多命运多舛,空闺苦闷,思念情人的情绪困扰,怕遭遗弃的心理危机,时时生发出“闺中之怨”:“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妾梦不离江上水,人传郎在凤凰山”、“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等等。这是因为,她们的丈夫做为一个商人,其全付精力专于一个“商”字,必须长年在外,从事商品的远途贩卖,又受市场价格的制约,归期无定,失信爽约,使得在闺中的年轻妻子,由盼望、期望而终归失望,终于从内心迸发出了如泣如诉的闺怨诗:“莫作商人妇,金钗当卜钱,朝朝江口望,错认几人船。”
还有一种情况,大凡城镇的商业贸易区,也多是笙歌彻绕,烟粉菌集之地,“夜夜买菱藕,春船载绮罗。”巨商富贾,迷酒恋花,停妻再娶,已成为商人妇一种可怕的现象,所以丈夫出门,妻子总是用心良苦的告诫:“欲别牵郎衣,郎今到何处?不怕归来迟,莫向临邛去。”临邛,是汉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相识、相恋之地。情切切意绵绵诉说不要见新忘旧,不要给夫妻间带来不幸。
封建社会商人妇的命运总体上说是悲凉的。她们地位卑微,经济不能独立,传统的世俗又轻商鄙商,不允许妇女走出闺门,抛头露面参与丈夫的商业活动。
历史的巨轮向前翻滚了几个世纪,直至20世纪九十年代的今天,人们的意识正在从产品经济观向商品经济观转变,那种鄙商、抑商、轻商的观念也正在消失。商品经济已成为群众性的经济,城乡人民有了充分就业的机会,实现了人民群众的劳动权利。几千年围着锅台转的妇女,也纷纷投身于商品经济的汪洋大海。过去的商人妇、农人妇、士人妇们纷纷进入流通领域,兴办家庭工厂,从事第三产业,小者提篮小卖,大者跨国做生意,过海发“洋财”。这是一种何等深刻而伟大的变革!妇女真正成为“社会人”的身份出现。
妇女经商具有自身优势,她们吃苦耐劳,观察敏锐,温柔多情,乐于助人,感情细微,又善解人意,加上入时的衣着、俏丽的装扮,经商办事比男人更会成绩斐然。鲁迅在《故乡》中所写的豆腐西施杨二嫂,就十分懂得消费者心理。她擦着白粉,终日坐在豆腐店里,“因为伊,这豆腐店的买卖非常好。”
不过,笔者在这里要说的是,妇女经商就其整体素质而言还处于弱势。即求利赚钱者众,提高素质者寡;满足现状者稠,竞争开创者稀。翻开日前报刊,见各地均刊出,“诚招天下客”的广告,但前去洽谈投资办厂,承包工程者在妇女界中却十分廖廖。其原因是,这些施展才华、鸿图大举的事业,一方面需要雄厚的资金,更重要的则要求投资者具有各种各样的准备。如,经济发展战略眼光,科学与民主的经营管理,深层次的谋略,历史人文知识的积淀,及至言谈举止的修养,待人接物的博雅气度等等,而这些恰恰是妇人商的弱项。有一位湖北的女商人,不知道武昌的黄鹤楼与襄樊的隆中;一位中国姑娘领着一家日本公司说,日本的女人受到良好的教育,站有站相,坐有坐态,很懂礼貌,而中国姑娘尽管长得美丽,身材好,但坐相不讲究,举止失态,用她的话讲,今后中国妇女必须搞好“内包装”,努力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云云。
中国的妇女生活得很累,既要搞一番事业,又要做贤妻良母。世俗使她们在生活上最容易满足,在心理上常存依附。赚得一笔钱,盖了一座小楼,就羡慕其他在家靠丈夫供养的妇女,“绿鬟皓腕,饱食浓妆”,于是不愿再奔波用脑了,把希望寄托于丈夫与儿子,谁若再称她为“女强人”、“巾帼风采”,她会很不高兴地说:“这是没有办法了呀,如若男人能行,孩子争气,我一个妇道人家,何必要出走争强受罪呢?”其卑微的依靠心理,又回到“商人妇”的位置上去。这是一种可怕的回归。报载,上海出现了一批过着寄生生活的商人妇,她们的丈夫有的是外国阔老,有的是国际倒爷,每月或更长一些时间才能回到身边团聚一次。这些悠闲阶层,常年包租高级宾馆,每日美味佳肴,养尊处优,百无聊赖,年华虚度,无所事事,又缺乏自尊、自爱、自强、自立的精神,其后来的命运与封建社会的“商人妇”没有什么两样。
柏杨先生说:“女人仅只经济上有独立能力,似乎还不够。……必须心理上有独立能力,才算是真正的人格独立。才有资格完成自我。”此话讲得有理。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