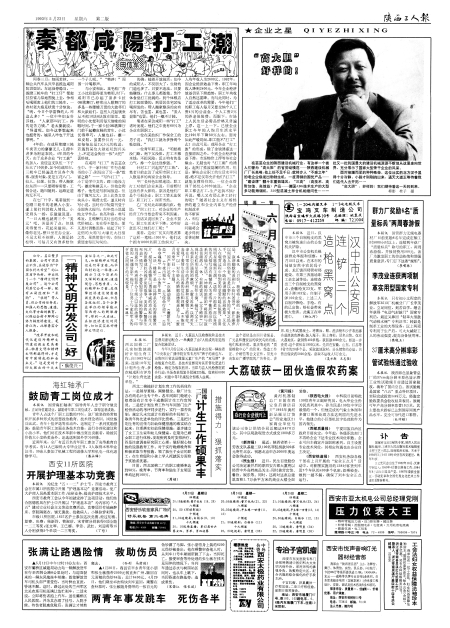
本版导读
秦都咸阳打工潮
阳春三月,细雨若丝。一辆公共汽车从兴平县抵达咸阳防洪渠站,车还没停稳当,一拨蹬三轮车的“打工仔”便忽拉拉雀儿似地围拢上去,争相吆喝顾客上他们的三轮车。一农村老大娘见状竟十分惊诧:“哟,今日个学雷锋的人,咋这么多?”一位中年妇女告诉她:“人家那叫打工,挣的是苦力钱。”老太婆就说:“怪道呢。如今这事想起来也挺奇的,城里人咋也干开这事咧。”
4年前,在咸阳靠蹬三轮车卖苦力的寥寥无几,且蹬车者多为附近农民。4年后的今天,由于众多企业“打工族”的加入,竟使这支队伍一下子壮大了10倍多。如今的咸阳市,三轮车已经遍及市区各个角落,服务对象,更是五花八门,拉人、拉煤、拉货,帮人搬家拉东西……只要顾客需要,工钱合适,随叫随到,远路近道均无不可。
在七厂什字,笔者碰到一位蹬三轮车的老熟人小安,遂上前打问其收入情况。小安眉头一扬,乐滋滋说道:“一日大概也就两三个‘美元’吧。苦是苦了点,但钱来得便当,花起来滋润。不像你老兄,整日坐在办公室,不见太阳不招晒,人倒是轻松咧,可每月又有谁多给你一个子儿呢。”“精辟!”周围一片喝彩声。
与小安相比,某毛纺厂青工小沈则显得更为精明。时下,咸阳市已办起了诸多卡拉OK歌舞厅,经常出入歌舞厅的多是一些腰缠万贯的大款爷们和大款姐们,这些人花起钱来从不把10块8块放在眼里。聪明的小沈便利用每天傍晚的闲暇时间,于一家卡拉OK歌舞厅门前干起擦皮鞋的营生。小沈长得乖巧,人缘也好,擦一双皮鞋,虽要价只有一元,却每每总是2元5元的收进,若遇到某位大款姐玩到兴头上,不定还会掏出一张“大把”丢给他。
在咸阳“打工”的芸芸众生中,于一家针织厂作行办秘书的小丁,则闯出了另一条“致富之路”——“写作打工”。小丁是学中文的,蹬三轮没力气,擦皮鞋嫌丢人,但他会爬格子。他先是写新闻报道,但由于撞坷太大,加上此类文章块头小,稿费太低,遂又转向写小说,虽时有中短篇刊登于全国各大报刊,但毕竟小说属纯文学作品,曲高和寡,难写难发,且稿酬与其付出的劳动代价相比,实在得不偿失,便又及时调整思路,搞起了时下走俏的大特写大曝光大扫描之类。果然箭箭中的,很快口袋便变得沉甸甸的。
的确,随着开放搞活,如今的咸阳人,不仅胆大了,生财的门道也多了。只要不违法,只要能赚钱,什么事儿都敢做。到个体食堂打工洗碗的,到个体粮店打工卸面袋的,到居民住宅区吆喝理发的,帮人搬家修房的应有尽有。苦也罢,累也罢,“丢人显眼”也罢,他们一概不计较。
笔者在采访咸阳一些“打工”者时发现,他们之中竟有60%为企业在职职工。
一位在某纺织厂作保全工的男子说:“我打工就为多挣两个吸烟钱。”
一位青年职工说:“咱经商没门路,南下又没胆,打工不摊本钱,不担风险,反正咱有的是力气,挣一个总比没挣强。”
针对工厂兴起的“打工热”,笔者日前走访了咸阳市职工打工人数最多的两家企业领导。
甲厂长神色坦然地说,职工打工对他们企业来说,目前暂时还没有多大影响。原因是他们厂是个亏损企业,职工工资无法保证,职工打工,理所当然。
乙厂长对此却深感内疚,他说:“职工打工,对企业的生产经营工作当然会带来不利因素。
但话又说回来了,企业不景气,职工生活水平下降,又咋好意思不让他们打工呢?”
接着,这位厂长又向笔者算了这样一笔帐:1991年,他们这个拥有8000名职工纺织大厂,人均年收入为2600元。1992年,因企业经济效益下滑,职工年均收入降到2400元。今年企业经济效益仍呈下滑趋势,职工年均收入自然还要降。而与此同时,为了适应改革的需要,今年他们厂的职工每人每月又要交纳个人工资4%的公益金,个人工资2%的养老保险费,而眼下,市场上人民生活必需品价格又普遍上浮,这一上一下,已使企业职工今年的人均月生活水平比1991年下降30%左右。面对如此严峻局面,职工能不“打工”么?由此可见,咸阳企业“打工族”的形成,除了金钱诱惑这一直接原因之外,个别企业经济效益下滑,市场物价上浮等等社会缘由,无疑也对“打工潮”的涌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解决企业职工的生活水平问题,绝不是仅靠允许他们“打工”就能支撑得住的。一位企业管理干部忧心忡忡地说:“企业职工都去打工,生产还搞不搞?再说,哪儿又有那么多工好打的呢?”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企业内部生产经营机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相信这一社会问题将会逐步得到妥善地解决。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 
